⬆️请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编者按:
此文乃是洪亮老师博士论文《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的摘要。该论文以发展史重构法,展现了图爱森在巴特《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文本形成史中所扮演的多面角色,首次全面评估了这位坚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爱好者”对早期辩证神学的理论贡献。
此文推送的意义不仅在于向汉语学界介绍洪亮博士颇有新意的博士论文和相关研究成果,更在于向汉语学界推介历史发生法或者发展史重构法这一在德语学界常见的研究方法。在我国的西学研究中,这样的研究方法依然是甚为罕见的。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在古希腊哲学界,以Werner Jaeger和陈康为代表的发展史进路开始得到重视。随着我国西学研究的进深发展,对历史发生法或发展史重构法的逐渐重视和应用或将成为其中的奠基性角色。
比对先哲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或者海德格尔关于“后思”[Nachdenken]的说法),若对一位思想家思想和文本的历史生成缺乏细致深入的了解,那就还没有真正做到对一位思想家思想的“照着讲”,遑论在中国学界自身的语境中“接着讲”。
本文原发表于《基督教文化学刊》2019年第41期“返本开新”巴特专刊。推送时已获期刊和作者本人授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文化学刊》编辑部和洪亮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面向终末的生命:
——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15-1923)

(Eduard Thurneysen,1888-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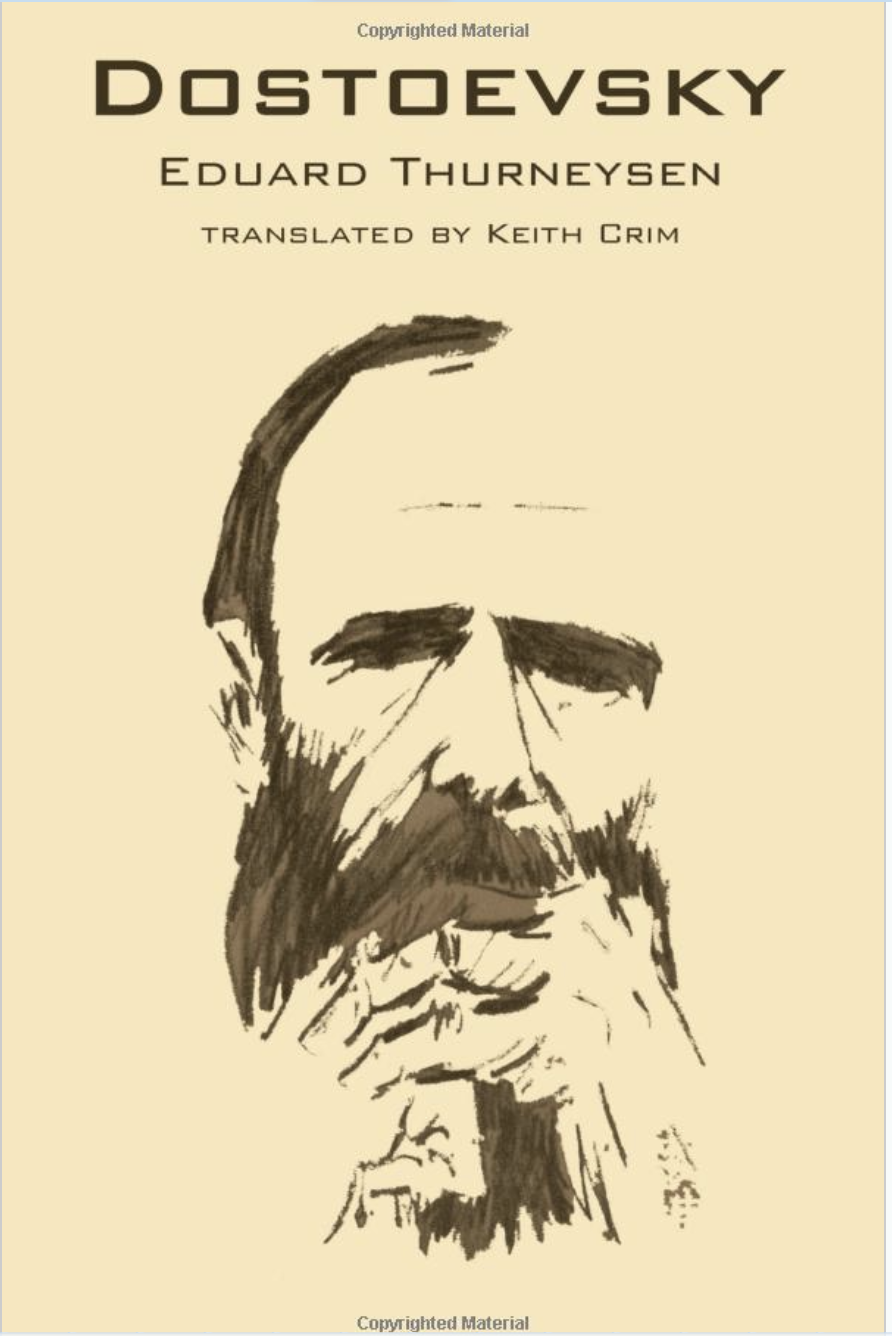

第四章首先分析了巴特与图爱森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九封通信;在此基础上,本章考察了图爱森在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如何继续深化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处理的文本是图爱森的报刊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社会主义》以及论文《迈向文化》,在前一文本中,图爱森强调,这位俄国作家政治观点保守性的根源是其对上帝这一彼岸视角的坚持,他关注的不是尘世内部具体的政治变革,而是具有终末气质与激进性的“真正革命”[16]。后一文本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图爱森认为,尽管这位俄国作家宣告了上帝的审判之言,但这种面向终结的旨趣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化和文化工作的理解是虚无主义式的,恰恰相反,他正是从“真正的终末论”[17]出发关心危机中的文化重建;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存在滥用终末论视角的可能性,尤其是当他唯独把斯拉夫民族视为被拣选的民族,把其他欧洲民族国家看作上帝的审判对象之时,图爱森把这种泛斯拉夫主义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终末论的激化”[18]。本章的第三部分重构了巴特和图爱森与哲学家福斯特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的一次论战。福斯特抨击图爱森和巴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诠释,认为两者曲解了这位俄国作家,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精华是“灵魂引导”[19]意义上的道德教化,不是消解教化意义的彼岸性。巴特与图爱森坚持,真正的德育超越一切此岸教化的手段与设计,指向生命的彼岸救赎;与成人相比,未经教化的儿童反而更能感受生命与彼岸之间的联系;福斯特对十九世纪“教育理念与文化理念”[20]不加反思的推崇是“对基督教的背叛”[21]。
本章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巴特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完成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涉及文本为巴特的授课讲稿《加尔文神学》,论文《当前伦理学问题》,《教会与启示》以及《论“实在性悖论”的悖论》,在这些文本中,“宗教大法官”占据了显著的核心地位。对此时的巴特而言,“宗教大法官”的意义包含三个侧面:首先,他借助神权政治取代了彼岸上帝的意志,损害了人类的自由;其次,他篡改基督的事业,试图以人手捏造出更好的版本;最后,他也代表了前启蒙时代压制人类自由与自治的宗教权威。[22]
第五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概括性地复述第一至第四章内容的基础上,勾勒了巴特和图爱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从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三年的变化过程,指出两者没有如巴特所言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受到“影响”,他们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探求的是其终末论旨趣在生命神学语境中的落实。这是巴特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的一封信[23]中承认自己十年之前误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因所在。第二部分指出,巴特和图爱森强烈的终末论导向一方面使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解读摆脱了“保守主义革命”阵营[24]突出俄国与德国民族利益的诠释进路,另一方面也造成其内在的单调性;但回归到如何理解辩证神学的终末论问题上,这两位神学家从透视主义角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性诠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即生命透过上帝主权这个彼岸焦点所展现出的“深层视野”[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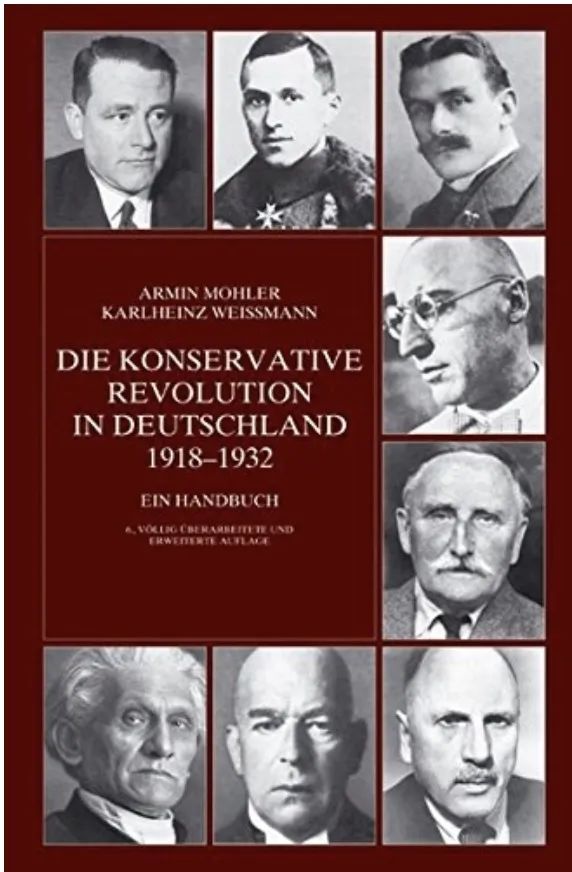
这篇博士论文的贡献有四个方面。首先,它借助巴特档案馆的材料,全面梳理了巴特和图爱森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三年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通信,尤其是两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的通信,展现了图爱森的“双重身份”(即《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初稿的审校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在《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文本形成史中的重大意义;其次,它表明《罗马书释义(第二版)》前言中关于巴特与图爱森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论断是后设视角下的虚构叙事,并不符合两位神学家的书信交流所记录的历史真实,巴特与图爱森并非“被动接受”这位俄国作家的影响,而是把“面向终末的生命”这一解读视角投射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世界,并将其剥离出俄国文化语境,以此来表述并打磨自己在终末论问题上的自我理解;再次,它揭示了图爱森在辩证神学发轫期的重要理论贡献,即透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把这一针对终末论的自我理解概念化为透视主义,从而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竞争性的文化思想语境中解读《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提供了新的可能。最后,就广义辩证神学研究而言,它修正了二十世纪欧陆神学史写作中把《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终末论视为“灾难理论”[26]的解读传统,揭示了早期巴特与图爱森终末论思维所隐含的神学人类学旨趣:终末不仅揭示此岸生命的有限与必死,更意味着它在彼岸上帝之“信实”中的奠基与“成像”,后者涉及的是意义的赋予,而非意义的倒空。
参考文献 :
[1] Barth, K. Römerbrief (Zweite Fassung) 1922. Hrsg. von C. v. d. Kooi/K.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0
[2] Liang, H.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Die Dostojewski-Rezeption im frühen Werk von 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1915-1923).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6.
[3] Mohler, Armin.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Stuttgart:Friedrich Vorwerk, 1950.
[4] Nietzsche, F. Nachlass 1885-1887,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Bd. 12. Hrsg. von C. Colli und M. Montinari. München: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5] Thurneysen, E. Dostojewski.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1921.
________. “Das Römerbriefmanuskript habe ich gelesen”: Eduard Thurneysens gesammelte Briefe und Kommentare aus der Entstehungszeit von Karl Barths Römerbrief II (1920-1921).Hg. von Katja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5.
注释:
[1]K.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1922, hrsg. von C. v. d. Kooi/K.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0), S. 7.
[2]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Die Dostojewski-Rezeption im frühen Werk von Karl Barth und Eduard Thurneysen (1915-1923)(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6).
[3]A. a. O., S. 52-61.
[4]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S. 683.
[5]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78-82.
[6]A. a. O., S. 85-118. 2015年,Katja Tolstaja 博士编辑出版这些书信: E. Thurneysen, “Das Römerbriefmanuskript habe ich gelesen”: Eduard Thurneysens gesammelte Briefe und Kommentare aus der Entstehungszeit von Karl Barths Römerbrief II (1920-1921),hg. von Katja Tolstaja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5).
[7] 这篇演讲图爱森发表于1921年4月25日,但演讲底稿已经遗失。
[8]E. Thurneysen, Dostojewski(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1921).
[9] 在写作《罗马书释义(第二版)》(1922)期间,巴特对图爱森提出的修改建议大都直接采纳。比如巴特在诠释《罗马书》第十四至十五章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罗马书的结尾处(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局处那样)只会被重新放置在生活(也包括基督徒的生活和基督徒的团契生活!)所包含的无法看透的困境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再次从头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关于上帝的谈论把我们逼入的困境。”这一段的原文为: “Nur aufs Neue werden wir am Ausgang des Römerbriefs (wie etwa auch am Ausgang der Romane Dostojewskis) vor die undurchdringliche Problematik des Lebens (auch des christlichen und des christlichen Gemeindelebens!) gestellt, auf dass wir keinen Ausgang finden, sondern erst recht wieder von vorne anfangen, nur immer neu die Bedrängnis sehen sollen, in die uns unser Gespräch über Gott gedrängt hat.” K.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674.如果参考图爱森1921年9月22日写给巴特的信,可以发现他给巴特提出的修改建议与书中文段惊人地类似:“这里有无可能以及是否合适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致可以这样写:我们在罗马书的结尾处(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结局处那样)只会被重新放置在生活(也包括基督徒的生活和团契生活!)所包含的无法看透的困境中,找不到出路,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重新审视逼我们谈论上帝的困境。”这一段的原文为: “Ist hier eine Erinnerung an Dostoj.<ewski> möglich und angezeigt? etwa so: Nur aufs neue werden wir am Ausgang des Röm.<er>briefes (wie etwa auch am Ausgang der Romane Dostojewskis) vor die undurchdringliche Problematik des Lebens (auch des christlichen, des Gemeindelebens!) gestellt, auf dass wir keinen Ausgang finden, sondern erst recht wieder von vorne anfangen nur immer neu die Bedrängnis sehen müssen, die uns in unser Gespräch über Gott gedrängt hat.”E. Thurneysens Brief vom 22. September 1921 (an Karl Barth), Karl Barth Archiv. KBA.參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111-113.
[10]E. Thurneysen, Dostojewski, S. 38.
[11]A. a. O., S. 39.
[12]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106f.
[13]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S. 600.
[14]F. Nietzsche, Nachlass 1885-1887,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Bd. 12, hrsg. von C. Colli und M. Montinari (München: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S. 114; 140.
[15] Barth, Römerbrief(Zweite Fassung), S. 265.
[16]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25f.
[17]E. Thurneysen, Dostojewski, S. 72.
[18]A. a. O., S. 75.
[19]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35f.
[20]A. a. O., S. 238.
[21] Ebd.
[22]A. a. O., S. 239-252.
[23] A. a. O., S. 21.
[24] Armin 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1(Stuttgart: Friedrich Vorwerk, 1950).
[25] H. Liang, Leben vor den letzten Dingen, S. 264.
[26]A. a. O., S. 263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