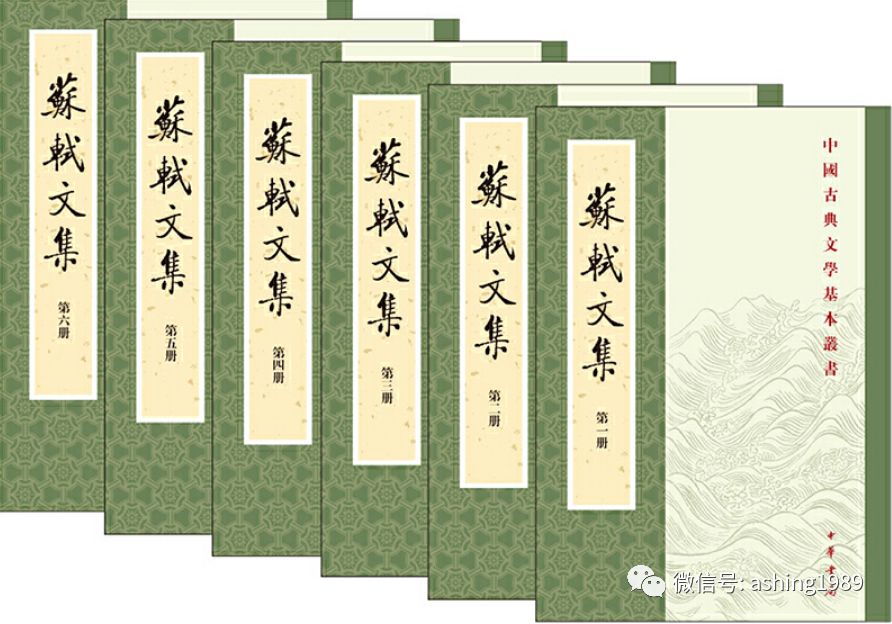
阿信注:苏轼说古今解释《中庸》的人自己都搞不懂,因此必须把《中庸》解释的拗口不同,后世人因为看不懂,越觉得其解释水平高深。吾昔日处艰难中时,受《中庸》恩惠极大,读此文,深感东坡可谓真得《中庸》之真味矣,何以言此?只因东坡曰:“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知之则达,故曰明。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知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者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
苏轼《中庸论》全文:
上、
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者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而从而和之者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原矣。
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说。嗟夫,子思者,岂亦斯人之徒欤?盖尝试论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未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以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是故去其虚词,而取其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盖以为圣人之道,畧见于此矣。
《记》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知之则达,故曰明。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知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者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与乐之者,是贤人、圣人之辩也。好之者,是贤人之所由以求诚者也。君子之为学,慎乎其始。何则?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乐焉,则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故曰:“自诚明之谓性。”
孔子盖长而好学,适周观礼,闻于老聃、师襄之徒,而后明于礼乐,五十而后读《易》。盖亦有晚而后知者。然其索县得于圣人者,是乐之而已。孔子厄于陈、蔡之间,问于子路、子贡,二子不悦,而子贡又欲少贬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乐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于卫,而不能不愠于陈、蔡,是岂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为从孔子游者,非专以求闻其所未闻,盖将以求乐其所有也。明而不诚,岁挟其所有,怅怅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则是可与居安,恶未可与居忧患也。夫惟忧患之至,而后诚明之辩,乃可以见。由此观之,君子安可以不诚哉?
中、
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晓然,知其当然,而求其乐。
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用器之为便,而祭器之为贵;亵衣之为便,而衮冕之为贵;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此礼之所以为强人而观之于其末者之过也。盖亦反其本而思之?
今吾以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将惟安之求,则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卧,偃卧而不已,则将裸袒而不顾,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夫岂惟磬折百拜,将天子之所谓强人者,其皆必有所从生也。辩其所从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是之谓明。
故《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从生而言之,则其言约,约则明。推其逆而观之,故其言费,费而隐。君子欲其不隐,是故起于夫妇之有余,而推之至于圣人之所不及,举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难,是天下之安其至难者,与其至易,无以异也。
孟子曰:“箪食豆羹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仪而与之,万钟与我何加焉。”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朋友妻妾之奉而为之,此之谓失其本心。且万钟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难,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较其轻重,是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之所能行,通而至于圣人之所不及?故凡为此说者,皆以求安其至难,而务欲诚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诚,而不得其说,故凡此者,诚之说也。
下、
夫君子虽欲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记》曰:“君子尊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途,夫虽欲不废,其可得耶?《记》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以为过者之难欤,复之中者之难欤?宜若过者之难也。然天下有能过而未能中,则是复之中者之难也。
《记》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书》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记》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皇极者,有所不极,而会于极。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故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归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记》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嗟夫,道之难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窃其名,圣人忧思恐惧,是故反复而言之不厌。何则?是道也,固小人之所以窃以为自便者也。君子见危则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于中庸。见利则能辞,勉而不辞,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愿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课矣。”以古之人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为足以已矣,则是不亦近似于中庸耶?故曰:“恶紫,恐其乱朱也,恶莠,恐其乱苗也。”何则?恶其似也。
信矣中庸之难言也。君子之欲从事乎此,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记》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选自《苏轼文集》第一集60页。
阿信,2019年12月10日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