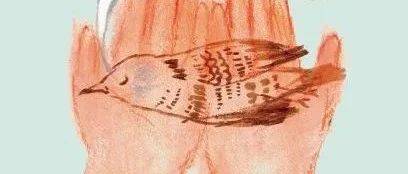回想一下,6月份最值得记住的画面是哪一个?恐怕很多人都会对北京工人体育馆那个奔跑的小子记忆犹新吧?
7月份呢?站在7月的最后一天,同样在体育馆,同样如花似玉的年纪,不一样的却是,年轻脸庞的笑容、满足、期许全被死亡吞没了。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晚上跟妻子聊天,说到孩子们写的评论文章,有从程序的角度思考事件的意义,有从人性的贪婪剖析灾难背后的原因,有的孩子站在家属的角度,悲叹生命的脆弱,无法挽回。
那天下午,大家还痛快地吃了顿火锅。正吃欢快时,心中忽然又想到齐齐哈尔的事儿,我怎么会吃得这么心安?
又想到好多年前,在大学课堂上,一位平时颇受同学们爱戴的老师,在他的博客分享自己最近听到新闻报道出来的灾难,心已渐麻木,我便拿出一位牧者的话加以留言:如果别人的苦难令你感到麻木,说明你离死也不远了。老师立刻勃然大怒:
你凭什么用这种教训人的口气发言!你有什么资格审判人?告诉我!中国那么大有那么多苦难,每天有那么多眼泪,那么多不公不义,你能背负多少?原本趾高气扬的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回复。因为无知,因为冒失而自觉惭愧。
美国文学大师德里罗在其经典著作《白噪音》White Noise 中提到:”资讯洪流是不间断的,文字、相片、数字、事件、图表、统计、微片、波动、粒子、微粒……唯有灾难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想要灾难;我们需要灾难;甚至我们还倚赖灾难;只要灾难发生在别的地方”。
究竟我们在面对苦难还是在避对苦难?还是如德里罗所预言的——我们在利用苦难?这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关掉社交软件也无法阻挡这股资讯的洪流。人类的智慧太有限,不足以擦去悲伤者的眼泪。

2018年二月,佛罗里达州派克兰(Parkland, Florida)的道格拉斯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发生校园枪击案。芝加哥地区数以千计的人们参与了抗议美国枪枝暴力的游行,其中有许多是高中学生。
道格拉斯高中在佛州排名三十八。因为此次暴力事件,学生们的生命被撼动了,在游行的队伍中,不少是从不同的学校、社区而来,甚至有很多来自富裕社区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中甚少枪枝暴力,却愿意花好几个小时坐车参加这次游行,成为抵制枪枝暴力运动的新面孔。
单纯地就着新闻事件,发表一番意见,带领学生们进行必要的反思,的确可以作为一次很好的课程实践。作为一名老师,我也常感到这样子的操作,只不过是利用了别人的苦难来完成自己的课程。
我们蒙召的人,不能只是用一句“为你祷告,为齐齐哈尔的十一位女孩子的家庭祷告“。然后就可以继续吃我们的火锅了。我们必须还要更深一步,我们太快地打发掉那一抹哀伤,甚至我们连表达哀伤的语言都严重退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新闻变旧闻,曾经循规蹈矩、照常吃喝的生活就又扑面而来了。
安慰那些伤心的人,需要自己先去真实感受对方的痛楚与哀伤。看到拉撒路的死,主哭了,周围的人立时的反应是,这个人有多么爱那个死去的拉撒路。这是最好的对于“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的示范。

昨天下午,我刚忙完手头的事情,从外面回家的路上经过肯德基。顺道打包了孩子们爱吃的薯条和鸡块。
刚满14个月的小儿,爬到餐桌上,我给了他一根软软的小薯条。过了一会儿,小儿爬到另一侧,在我和妻子聊天的时候,他就站在我俩中间,我又抽了一根小薯条递在孩子手里。
就是这半根薯条,差点要了孩子的命。
几秒钟的时间,孩子的脸失去了血色,嘴唇乌青,极力呕吐也于事无补。妻子抱起孩子,喊着我的名字,就在那一时刻,眼睁睁看着孩子身体没有了挣扎,心中快速回想着从红十字会学来的急救方法,终于听见孩子哇的哭出声来,转危为安。
这或许是一次无心的失误,提醒做父母的要小心给孩子的食物,尤其是低幼小孩,葡萄、花生、瓜子、薯条是万万不能给孩子吃的。
孩子渐渐平稳下来,在妈妈怀里睡着,“我想抱着宝宝睡。”
晚上躺在孩子身边,摸着软软的小脚丫,听着孩子均匀的呼吸。和妈妈谈了好久好久。现在,我们能够稍稍体会一点失去孩子的痛苦了。
身边有因车祸失去孩子的妈妈,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深渊啊!我们不能明白,也不能感同身受,只能求从天上来的安慰。经历这一次突然的遭遇,我们真的体会到了那种恐惧。
鲁迅先生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这的确是真实的写照。苦难面前,孩子们写文章反思,老师设计课程提供讨论空间,大家吃顿火锅联络感情,这都是好的,是美的。我们不需要拿这一部分去抵消另一部分。
喜乐时,就当感恩,哀哭时,就尽情流泪。莫让喜乐都蒙上道德的阴云,苦难再威猛,也攫不走喜乐泉源,我们做不到让一颗心免于哀伤,人生的意义就在此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