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祝各位朋友新春愉快,本期我们推送的是洪亮老师的一篇新近评论。正如卡尔维诺所言,经典是正在重读的作品。经典之作往往也伴随着细致持续的校勘与编注,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比较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与把握文本。本文关注是巴特极为重要并广为人知的作品《〈罗马书〉释义》第二版的最新校勘本。作者洪亮老师不仅针对此版的三大亮点作了精彩点评,也对第一版发行以后围绕《释义》的些许争议作了回应与澄清。洪亮老师指出,通过增添脚注,新校勘本为巴特大量来源不明的引证找到出处,并揭示了巴特的诸多影射,成为校勘本最富特色之处。在洪亮老师看来,尽管新校勘本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延续了《巴特全集》编撰专案的基本精神,并为未来的巴特研究开拓了新的起点。
本文原发表于《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11年春第36期,推送时已获发表期刊和作者本人授权,特此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和洪亮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評巴特《羅馬書釋義》第二版最新校勘本
文 / 洪 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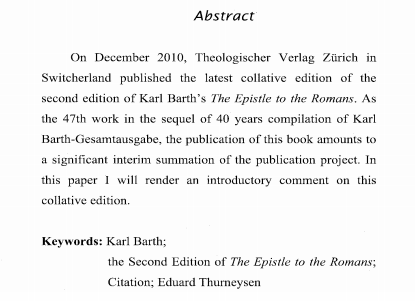
關鍵詞:巴特 《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 引證 圖爾奈森
二○一○年十二月,瑞士蘇黎世神學出版社(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推出了巴特(Karl Barth)*《羅馬書釋義》(Der Römerbrief, 1922)第二版的最新校勘本,[1]作為巴特全集(Karl Barth-Gesamtausgabe)編纂專案[2]四十年來連續出版的第四十七部著作,該書的出版是對此專案階段性工作的一個重要總結。[3]
此次校勘的底本仍是《羅馬書釋義》(1922)的第二次印行本,即通常所謂的第三版(1923),這個版本對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首次印行的《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作了一些修訂,[4]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印刷錯誤,目前通行的第十五版(1989,校勘負責人為施特韋桑德[Hinrich Stoevesandt])對此已做過校正,但此次校勘團隊在某些字句問題上仍舊參考了巴特的手稿[5]和《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首次印行本。[6]與第十五版相比,新校勘本的亮點有三處:
一、校勘團隊的兩位中青年巴特專家范德科伊(Cornelis van der Kooi)[7]與托爾斯塔亞(Katja Tolstaja)[8]合寫了一個介紹《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文本背景的前言;
二、第十五版的經文一覽表和索引得到大幅度擴充;[9]
三、增添了一個經過分類的文本注腳區(Fußnotenapparat),除巴特自己的二十四個注腳之外,此次校勘又擴充了文本考證(Textkritik)、[10]巴特引證或影射之文本出處(包括校勘團隊的相關評注)這兩類注腳,[11]以上三點使該校勘本在體例上與一九八五年問世的《羅馬書釋義》(1919)第一版校勘本[12](團隊負責人為施密特[Hermann Schmidt])得到統一,本文將結合范德科伊和托爾斯塔亞撰寫的前言[13]對該校勘本的最大亮點,即文本注腳區略作一介紹性評論。
在〈詮釋學與歷史主義〉一文中,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曾把《羅馬書釋義》(1919)第一版對自由派神學的批判稱為「一種詮釋學宣言」,[14]他認為巴特以此不僅拒絕了歷史考證方法(Historisch-Kritische Methode),同時也把醞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新的教義學需求帶入了歷史神學。[15]如果說新校勘本同樣注意到《羅馬書釋義》第一版(1919)及第二版(1922)具備詮釋學維度,那麼此一關注則首先體現於范德科伊和托爾斯塔亞對巴特「作者」(Autor)身份的強調:巴特是那位「撰寫」了《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的神學家。寫作是賦予材料以形式的詮釋過程,此一過程的落實當以(中譯本譯文)巴特所言「舊時智慧與今時智慧之間不斷進行的日益真誠、日益緊迫的對話」[16]為前提,新校勘本特別強調:「巴特是一個善於在和他人的對話中發展自己的思想家。」[17]他的這種對話能力導致《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文本內部遍佈各類(大型或微型)對話結構,並且大多數對話並非與同道(如圖爾奈森[Eduard Thurneysen])的磋商交流,而是與各色論敵的激烈交鋒,這也是巴特「對話能力」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之處。「巴塞爾人生來就好爭辯」,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曾以此評價過其師巴特。[18]
《羅馬書釋義》(1919)第一版的問世幾乎使巴特成為眾矢之的,「教條主義」、[19]「理智主義」、[20]「輕視理性與學術」、[21]對“pistis””一詞的隨意翻譯[22]等等責難一時間鋪天蓋地。巴特認為自己被誤解並遭到攻擊,他要在《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中澄清誤解並予以還擊,於是米勒(A. D. Müller)、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韋恩萊(Paul Wernle)、于利歇爾(Adolf Jülicher)、施特赫林(Ernst Staehelin)、克勒(Walther Köhler)、維爾納(Martin Werner)、勒琼(Robert Lejeune)以及菲舍爾(Eberhard Vischer)等學者對巴特的批評便相繼被整合進《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成為其或明或暗的攻擊對象,而且為了達致特定的修辭效果,巴特引證、影射了大量似乎能支持其立場的其他文本,範圍之廣,令人稱奇(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稱《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為「神學表現主義」,[23]這與巴特辭藻之斑駁陸離和怒氣之溢於言表不無關係)。以上兩個因素(論爭與修辭)的結合不但使《羅馬書釋義》(1919)第一版就存在的文辭臃腫問題未得到改善,而且在文本理解層面給讀者(包括譯者)造成了不少困難,新校勘本增添文本注腳區,意在從兩個方面疏解文本疑難:首先、為巴特大量來源不明的引證找到出處;其次、澄清《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的諸多影射,揭示巴特的論戰對象或思想來源。
我們先看第一個方面。拉德(Martin Rade)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含蓄批評過巴特不太注意學術引證的規範性,[24]《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在學術引證上可以說也是相當隨意。校勘團隊在《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中一共找出了五種截然不同的引證方式:一、用引號引證或改寫引文,只提人名,不提出處;二、直接移用文段或片語,不加引號,不提出處;三、用引號引用文段,但不提出處;四、在引號中放入關鍵詞或片語,不提出處;五、在引號中放入關鍵詞或片語,指出作者,但在該作者那裏根本找不到巴特提供的關鍵詞或片語。
一、新校勘本前言援引了施密特在《羅馬書釋義》(1919)第一版校勘本中已經指出的問題,即巴特張冠李戴,把從察恩(Theodor Zahn)《保羅致羅馬人書》(Der Brief des Paulus an die Römer)中引證的一個文段[25]歸於楚恩德爾(Friedrich Zündel)名下,該錯誤在此後印行的所有新版《羅馬書釋義》中都被沿用下來。[26]
二、巴特在《羅馬書釋義》(1926)第五版前言末尾移用加爾文的Moniti discamus[27]這一說法,校勘團隊在加爾文的一些釋經學著作(如《約翰福音評注》、《使徒行傳評注》和《撒母耳記(上)評注》等)中確定了這一說法的具體位置。[28]但巴特卻從未指明該說法來自加爾文。
三、在對《羅馬書》第九章第五節的評論結尾處,巴特用引號引證了一個句子(中譯本為)「你們聽到這個信號了嗎?」[29](Hört ihr das Zeichen?)[30]校勘團隊至今無法確定這個引文是否來源於克林格曼(August Klingemann)或勞帕赫(Ernst Raupach)的劇作,抑或只是巴特借助引號對自己措辭的強調。
四、巴特很喜歡用關鍵詞或概念的形式對某種思想傾向作素描,簡練明快且無需指名道姓,但是它卻給讀者(包括譯者)理解文本增加了難度。比如,巴特在對《羅馬書》第一章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節的評論中提及「人格」(Persönlichkeit)一詞,認為它是「必朽壞的人……的樣式」。[31]如果不了解這個概念在歐洲十八、十九世紀所謂「歷史主義」[32]中的地位,以及巴特曾熱切關注此概念,[33]那麼巴特這裏對「人格」概念的批判就會顯得相當突兀。在注腳區中,校勘團隊對這類關鍵詞或概念大都給出一定程度的疏解。這裏要提及的是,《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的中譯本在翻譯巴特的此類關鍵詞上就出現了一個錯誤。在該書第七章第一節「宗教的局限」中,巴特指出「宗教人」只是「人之可能性」的一種變體,這種人(中譯本譯文為)「在最好情況下是聖方濟各,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按意圖也許是布魯姆哈特(Blumhardt),從結果看則也必定是火災(Brand)」。[34]「宗教裁判所大法官」(Großinquisitor)一詞所指為陀思妥耶夫斯基(F. M. Dostoyevsky)的《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很清楚,但「火災」一詞卻十分突兀,與上下文難以銜接。從巴特這個排比式的行文結構來看,“Brand”這個詞的位置上應該出現一個典型人物、一部作品或其中的虛構人物,但此處的德文確實是“Brand”,中譯本此處譯為「火災」無可挑剔。然而,此處的“Brand”所指實為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劇作《勃蘭特》(Brand)中的人物勃蘭特牧師,校勘團隊在注腳區也指出了這一點。本文在此可以提供巴特一九二○年七月四日寫給圖爾奈森的一段書信作為旁證:
他(指巴特胞弟海因里希.巴特[Heinrich Barth])認為我們和易卜生的《勃蘭特》差不多,也許我們應該撰文介紹這部劇作,比如在《新事工》(Neuen Werk)雜誌上,也許要在一個更大的語境裏來寫,要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易卜生進行加工,好讓他們能夠相互解釋。我很高興,自己現在才能夠正確地去讀這幾個人(的東西)……。」[35]
”
五、這一類引證為數不多,新校勘本前言指出的第一個例子是巴特在《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前言中對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引證。這段引文(中譯本譯文,有改動)如下:「施彭格勒是否說的不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鐵器時代』(eisernes Zeitalter)?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連神學和神學家也不會不對此毫無感觸?」[36]校勘團隊在施彭格勒此一時期的論著中未能找到「鐵器時代」這一表述。[37]第二個例子是對哈納克的引證,巴特在該書第六章寫道(中譯本譯文):
人在肯定的『是!』還是否定的『不!』中認識自己的規定性,人作為罪犯還是作為聖者留下自己的履印,人想要和將要在天堂還是在地獄裏發現自己的命運,還有『善者更善,惡者更惡』(Guten immer besser, die Schlechten immer schlecht werden)(哈納克)的局面─這一切難道不是純屬偶然,難道不是任意嗎?」[38]
”
「善者更善,惡者更惡」該表述在哈納克的論著中也無法找到。[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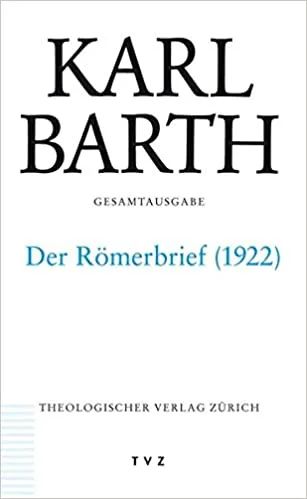
Herausgeber :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1. Dezember 2010)
Sprache : Deutsch
第二個方面涉及巴特不提人名和出處的影射,這是新校勘本最富特色之處,限於篇幅,在此只能略舉三處作為示例。我們首先來看巴特在《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前言中對伯爾尼新約教授維爾納的影射(中譯本譯文):
我將實義的內在辯證法以及在原文詞句裏認識這種辯證法稱為對理解和闡釋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但這是指甚麼?有人告訴我(一位瑞士評論家說的尤其露骨),這當然只可能是指我的『體系』。人們在評判我的全部嘗試時,的確會自然而然地懷疑我與其說是在詮釋原文,毋寧說是在添油加醋。」[40]
”
這裏的「一位瑞士評論家」指的就是維爾納,他在一九二一年的一篇文章中批評了巴特的《羅馬書釋義》(1919)第一版,因為巴特雖在這本書裏說出了一些關於保羅的正確見解,但又在其中摻雜了不少「巴特式的歷史哲學」。[41]他譏諷道:「我們將會看到一種新的系統神學流行起來,這種神學又倒退到老亞歷山大學派的路子上去了。」[42]巴特對此毫不退讓(中譯本譯文,有改動):「保羅對上帝有所知,我們一般無所知,但我們也是能夠有所知的。我知道保羅對此有所知,這就是我的『體系』,我的『教義學假設』,我的『亞歷山大主義』……。」[43]巴特這裏使用「體系」一詞原是對維爾納的諷刺性模擬,然而恰好是這個圍繞着「體系」問題的爭辯引出了巴特對「辯證神學」的著名定義(中譯本譯文):
如果說我有某種『體系』,那麼這體系就是承認基爾克果提到的時間與永恆之間『無限的本質區別』,堅持考察這種區別的負面意義和正面意義。『上帝在天上,而你是在地上』。如此的上帝和如此的人的關係,如此的人和如此的上帝的關係,對我來說,這就是《聖經》之題與哲學之和兩者合二為一。[44]
”
新校勘本對巴特與維爾納論爭關係的疏解為這一經典定義確定了其具體的歷史生成語境。
第二個例子涉及巴特「上帝作為徹底的他者」(Gott, der ganz anders ist)這個思想的可能來源。在《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開篇處巴特便提到(中譯本譯文),「在此必須注意:傳佈的是上帝的真理!這就是說:不是宗教的信息,不是關於人的神性或神化的消息和指令,而是上帝之音─上帝與凡人迥然不同,上帝的一切凡人永遠無法知曉和佔有,但正因為此,上帝給人們帶來福祉。」[45]「上帝與凡人迥然不同」,巴特的這個思想來自何處?新校勘本強調了宗教現象學家奧托(Rudolf Otto)《神聖者》(Das Heilige)[46]一書對巴特的影響,而且在文本注腳區添加了巴特寫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三日的書信作為對照和旁證:
這個星期我讀奧托的《論神聖》讀得很愉快,他的東西雖說是定位於心理學的,但卻明顯超出其界限而到達了神秘且令人畏懼(Numinosum)之處,這是用理性的方式所無法解決的,因為它是全然他者(Ganz Andre),是上帝中的神性。[47]
”
《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的確強調了人神差異,但這個思想的來源相當複雜,奧托作為來源之一,其特別之處在於為巴特提供了一個直接可用的詞彙域:徹底的他者(totaliter aliter)。[48]
最後一個例子與此次校勘團隊負責人之一托爾斯塔亞的博士論文直接相關,即巴特辯證神學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釋。由於她的研究依賴圖爾奈森和巴特早年的通信,以及前者寫於一九二一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一書,因此圖爾奈森的作用、《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之間的平行性在文本注腳區中得到了特別的關注。在《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第二章中,巴特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一種對於啟示和信仰的特殊認識,他筆下人物的「宗教和體驗」並非自認已「有律法」之人要加以同情的對象,相反,這是對未知上帝的另一種真實認識,唯有上帝能對之進行判斷,而非「有律法」之人,(中譯本譯文)「應該敢於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的宗教和經驗推廣到所有其他宗教和經驗上去!」[49]文本注腳區在此處引入圖爾奈森的文本,認為巴特的這種表述方式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的啟發關係密切。這種「並置」正確與否,可以商榷,但它能夠協助讀者意識到《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背後的複雜文本語境,卻是不爭的事實。
考察《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的形成史離不開對圖爾奈森和巴特思想關係的梳理,這不僅是因為前者向後者介紹了諸如布魯姆哈特、庫特(Hermann Kutter)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重要精神資源,[50]更在於圖爾奈森通過校訂巴特的手稿而直接參與了《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的寫作。[51]圖爾奈森對巴特手稿的校訂始於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即巴特開始《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寫作的第二天)[52],結束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即巴特結束寫作之後的第三天)。[53]在此期間,圖爾奈森與巴特進行了大量通信,其中與《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文本直接相關的書信有五十九封,但圖爾奈森只發表了二十六封,剩餘的三十三封書信仍舊存放在巴特檔案館裏。[54]通過這些信件,圖爾奈森向巴特提出了大量修改建議,而它們大都被巴特接受並寫入《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這一點巴特在第二版前言作過說明(中譯本譯文,有改動):
圖爾奈森還通讀了手稿,提了鑒定意見,做了大量更深刻、更詳盡、更明確的補充(我在大多數情況下幾乎未加改動採用了這些補充),卻無私地甘為幕後英雄。我們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無論哪位專家都不可能分清何處是我的思想,何處又是他的思想。[55]
”
校勘團隊的意圖並非在於「分清」巴特和圖爾奈森各自的思想,而是為了澄清圖爾奈森在《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文本形成史中的位置,「那些被刪去的通信可以更加準確地顯示《羅馬書釋義》中的影射、巴特閱讀過的書籍、涉及文本背景的討論、政治、神學、家庭問題及氛圍。圖爾奈森的文本具有重要的神學史和文本考證意義,因此整理出版他的全部通信仍是一項尚待落實的任務。」[56]
一九八七年,施特韋桑德在為第十五版撰寫的前言中曾提及《羅馬書釋義》(1922)第二版未來的校勘問題,二十三個寒暑之後,這一計劃終成現實。新校勘本儘管有些許不盡如人意之處,[57]但它仍以明晰的歷史意識與文本語境意識延續了《巴特全集》編纂專案的基本精神,也為未來世界範圍內的巴特「辯證神學」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起點。

作者简介
洪亮,图宾根大学神学博士,中國政法大學宗教與法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研究兴趣:系統神學(施萊爾馬赫,巴特,莫爾特曼,朋霍費爾)、實踐哲學(阿倫特,約納斯)、法律與宗教(自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