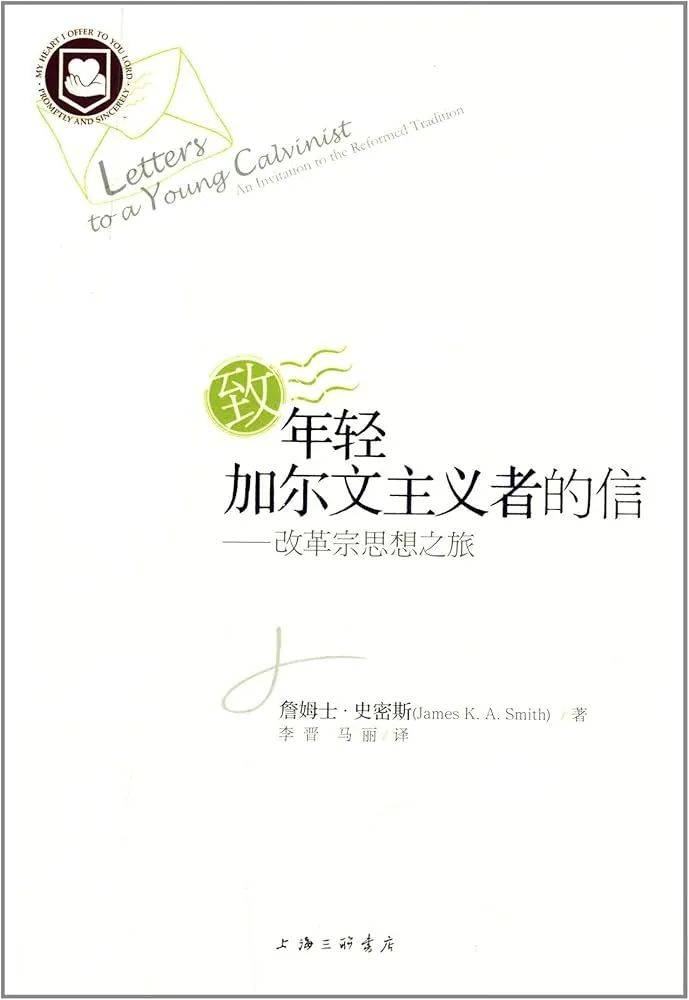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加尔文大学(Calvin College)哲学教授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所走的道路与我在《年轻、躁动、归正:一位记者与新加尔文主义者的旅程》(Young, Restless, Reformed: A Journalist’s Journey with the New Calvinists)一书中介绍的许多年轻福音派基督徒走过的道路类似。
史密斯还记得在大学时阅读约翰·派博(John Piper)的《渴慕神》(Desiring God,中译书名为《十点十分的盛宴》)时带给自己的影响。他从派博和巴刻(J. I. Packer)那里了解到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他仔细阅读了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华菲德(B. B. Warfield)和谢德(W.G.T. Shedd)的作品。他在洛杉矶的一间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属于五旬节宗,特点是强调感性经历)带领大学事工时,很好地指导了渴求圣经神学的学生。
简而言之,史密斯知道他在《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改革宗思想之旅》(Letters to a Young Calvinist: An Invitation to the Reformed Tradition)中既赞同又责备的内容是什么。
史密斯是一位研究后现代主义等议题的杰出学者,他在这本备受欢迎的书中以友好的、牧者的口吻写作。他引导年轻的加尔文主义者们参观改革宗神学的庄园,这些年轻的目标读者刚刚进入门厅,就已经开始惊叹于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他们还没有观察到这个被称为改革宗传统的宫殿式庄园中的其他房间。史密斯是一位生动和善于拓展思维的作家,他采用了书信的形式来充当读者的导游。
史密斯强调,改革宗神学来自圣经。它不是人类的发明,也不只是吸引过度理性的基督徒建立抽象概念。他对阿民念主义者(Arminians)的强硬措辞让我感到惊讶。史密斯写道:“当代福音派被一种阿米念主义共识所支配,已经变得如此彻底的以人类为中心,以至于最后把神看成了一个负责照顾我们的愿望和需要的仆人。”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他责备阿米念主义说后者认为神独自坐在那里,希望我们能请他去参加舞会。
当然,史密斯对加尔文主义者的主要关切之一就是宗教骄傲(religious pride)。事实上,他在欢迎年轻的加尔文主义者加入改革宗传统之后,立即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责备那些热情的新加尔文主义者,认为他们表现出的傲慢态度好像诺斯底主义者发现了某种秘密的知识一样,使得他们自视优于其他基督徒。史密斯说,加尔文主义“可能是致命的:一种神学上的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他不鼓励加尔文主义者把与其他基督徒弟兄的争辩看作自己的毕生使命,史密斯认为,“改革宗神学从根本上讲是关于恩典的。”因此,加尔文主义者至少可以做的是对他人表现出一些恩典。毕竟,我们有什么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呢?(林前4:7)
当史密斯讲述改革宗神学历史并为其信仰和立场辩护时,他的大部分内容都很不错,他也认为改革宗神学是“教会各时代的教师从圣灵而来的智慧”。然而,他认为《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是“干巴巴的甜点”,而《海德堡教理问答》是“带来滋润的绿洲”。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偏爱产生了神学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巴文克(Herman Bavinck)和伯克富(Louis Berkhof)的荷兰改革宗传统,而不是产生了约翰·欧文(John Owen)、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盎格鲁-苏格兰改革宗传统。
然后,此书出现了一个转折,这会让史密斯的许多目标读者感到不舒服。在向读者推销广义改革宗传统的同时,他却把矛头指向了浸信会和其他没有全盘采纳改革宗信仰告白、又声称是加尔文主义者的人。史密斯特别提到了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该学院自1859年成立以来就一直继承着盎格鲁-苏格兰改革宗传统,这一点在该校信仰告白《浸信会基本原则》(Abstract of Principles)中就有所体现。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在史密斯的这本书中成了遭到批判的典型靶子,他写道:
威斯敏斯特一脉削弱了改革宗传统的大公性,它所阐述的“加尔文主义”只是那种被消减了的、单独抽出来的救恩论,它可以被抽出来并且插入到任何宗派(和非宗派)的神学体系中。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即加尔文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被归结为“五要点”(TULIP)的救恩论,史密斯以约翰·加尔文为例,加尔文为了门训的缘故改革了教会的敬拜。可以肯定的是,加尔文对他那个时代的浸信会信徒(baptists)和他们所主张的地方教会治理方式没有什么宽容。史密斯认定改革宗传统有一个独特的教会论,拒绝这种教义和教会架构就不属于改革宗。史密斯远不是今天唯一发出这种最后结论的教会领袖。这些批评者可能无法成功地夺回“改革宗”这个词供他们独家使用,但我可以同情他们对保护这个词历史完整性的关切。
不过,我想知道,史密斯是否为着这一点而耗费了太多笔墨。他认为,改革宗的传统是大公性的,包含了其他看重恩典的神学家,如马丁·路德和希波的奥古斯丁,但这些人都没有持有与加尔文相同的教会论。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救恩论;此外,他们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婴儿应该接受洗礼。那么,婴儿洗是改革宗和非改革宗之间的主要分界线吗?高举神的敬拜和基于福音的门训这两者的地位又如何呢?如果说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进行的教会归正使改革宗传统与众不同——而不仅仅是婴儿洗或长老制教会论(Presbyterian ecclesiology),那么在地方教会和联会中追求这种目标的浸信会信徒就应当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也继承了改革宗的遗产。
该书的其他部分也同样会激起许多读者的兴趣。他责备一些改革宗的神学家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上更像路德宗而不是加尔文派。但在称赞N. T. 赖特(N. T. Wright)时,史密斯本可以与美洲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基于《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前提下批判保罗新观的文章进行有益的互动。
史密斯还为平权主义插入了一个简短的辩护,呼吁改革宗传统要反对“对妇女的奴役”——他指的是互补主义(complementarianism)。救赎使堕落的诅咒失效,他观察到耶稣和保罗通过赋予妇女权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事实上,我们的确要为马利亚、马大和其他许多忠心的耶稣门徒,以及百基拉、非比和其他与保罗一起服事的姊妹们感恩;虽然如此,保罗还是在他的书信中写道:“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提前2:12)但史密斯没有提到这节经文,他也没有提到在这里他和最近几十年平权主义的发展都偏离了历史上改革宗的立场。
这本书中最让我感到担忧的是史密斯对个人性救恩(individual salvation)的批判。他通过诉诸于三位一体和其他教义,为共同体(community)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动和信服的理由。他写道,上帝“创造世界并不是为了生产一批孤独的个体或社会‘原子’——它们自我封闭、彼此不相往来,因此只能在垂直的孤岛上与上帝‘私下里’相交”。但谁会真正相信这种夸张的描绘呢?哪怕在史密斯相信的改革宗传统之外也有许多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重洗派的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卫理公会的韦利蒙(Will Willimon),甚至美南浸信会的莫勒(Albert Mohler)等领袖都会通过呼吁认信的、可见的地方教会来拒绝这种怪异的个人主义。
但史密斯似乎走得更远。他写道:“我主张,上帝交往的‘单位’总是一个共同体、一个族类。”当然,我们西方人需要为我们的极端个人主义受到责备,但圣经支持史密斯的这种集体主义立场(absolutist position)吗?改革宗传统中的其他人也会这么说吗?史密斯正确地指出,圣经中的“你”(you’s)经常是复数的人称代词。当然如此,因为保罗的许多信件都是写给教会的。不过,在教牧书信中,当保罗劝告提摩太和提多时,读起来就不同了。保罗悔改归正的例子难道不应该让我们对“上帝总是而且只把我们当作共同体看待”这样的说法保持警惕吗?
史密斯写了很多东西,正是败坏的美国教会需要聆听的。即使是我,一个确信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浸信会信徒,也由衷地同意:“加尔文主义的‘精髓’(genius)不能被简化为关于选民得救的预定论教义。”史密斯关于享受创造的结论让我为上帝的大能工作而赞美他,并祈求耶稣能快快再来、使万物更新。但是,如果改革宗传统的捍卫者想要改造浸信会,我认为还有更好的方法。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Letters to a Young Calvinist
柯林·汉森(Collin Hansen)是福音联盟的编辑主任,也是多本书籍的作者;他在三一神学院获得道学硕士学位。他和他的妻子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救赎主社区教会(Redeemer Community Church)的成员,他是比森神学院的顾问委员会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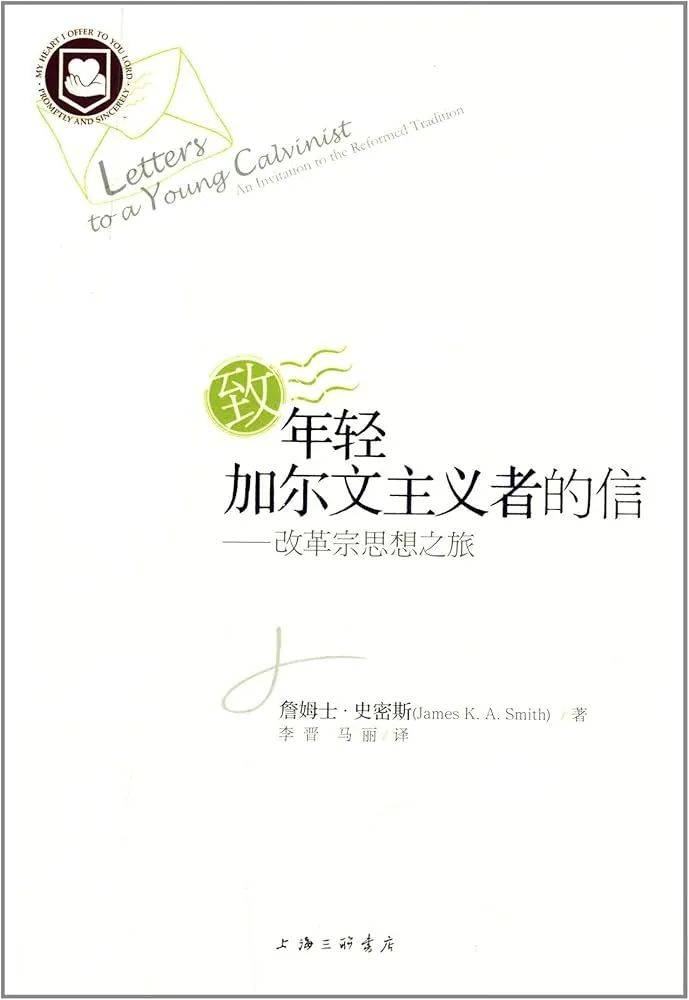
摘自:詹姆士·史密斯(James K. A. Smith),《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改革宗思想之旅》,李晋、马丽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