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今天推荐的是一组小文,前者是路易斯谈古书阅读,后者是麦格拉思谈路易斯谈文学阅读,两下合力,旨在解决当下人们在阅读上的普遍严重疾患——路易斯口中的“时代势利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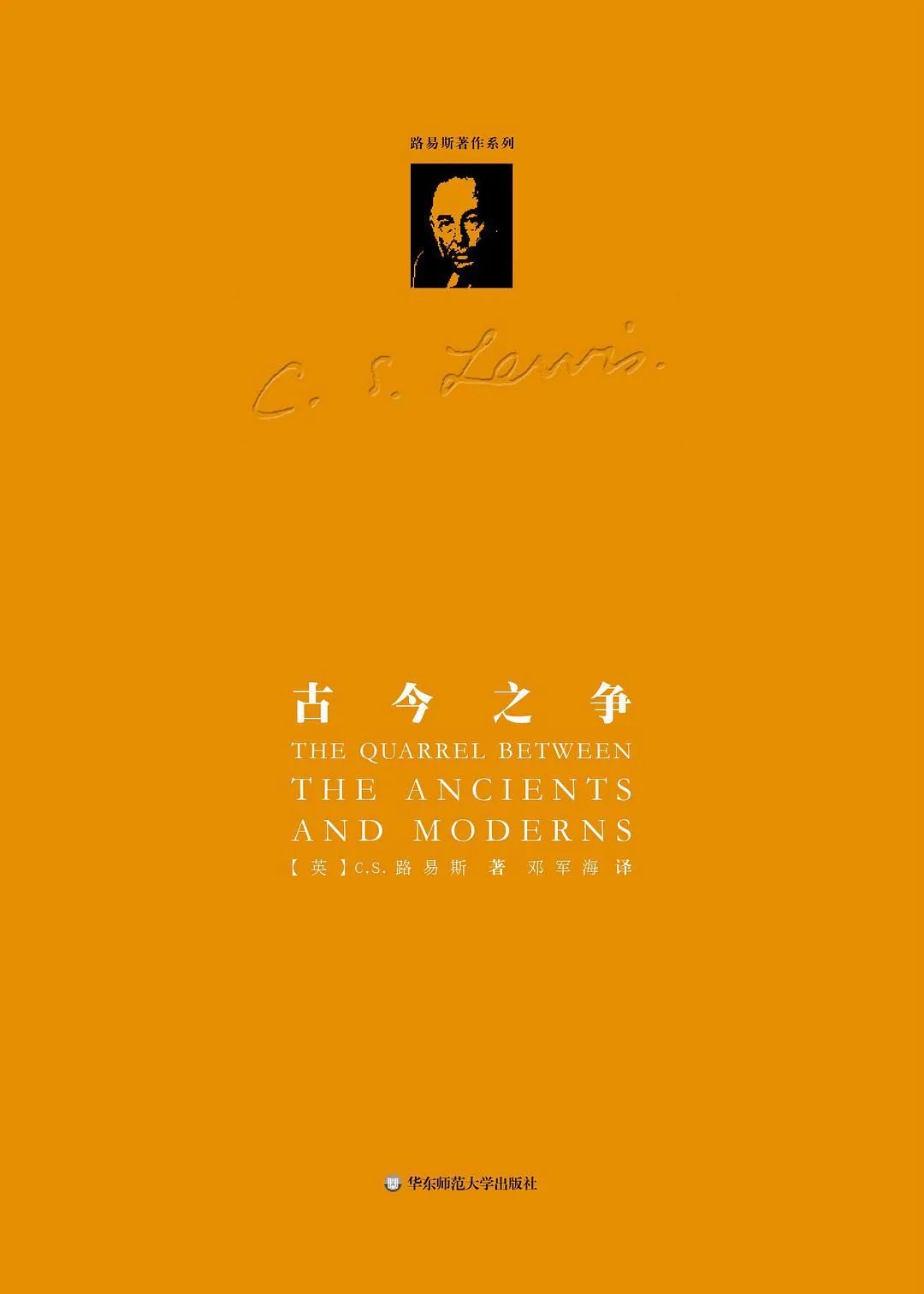

↑ 扫码购买
我们需要对过去有一种密切的认识。并不是过去有什么魔力所在,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研究未来,但又需要某种东西作为现在的参照,来提醒我们,不同的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基本假设,许多在未蒙教化的人看来确凿无疑的东西,无非只是当时的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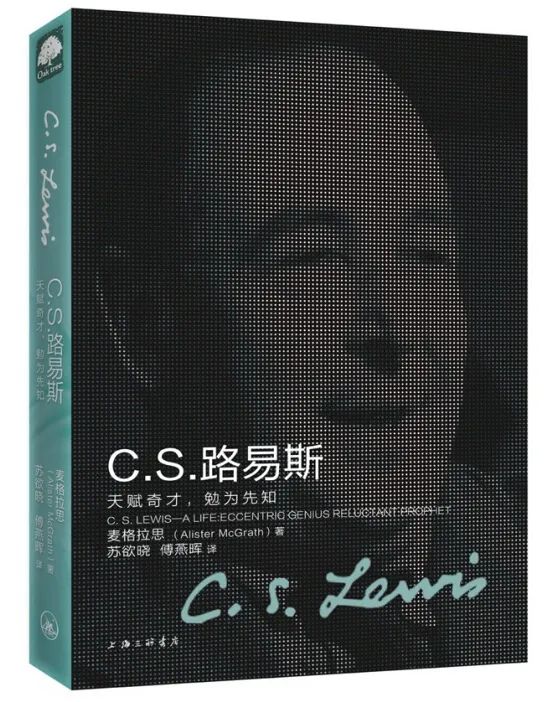

↑ 扫码购买
购买路易斯所著图书,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橡树出版之【精彩书摘】
今天推荐的是一组小文,前者是路易斯谈古书阅读,后者是麦格拉思谈路易斯谈文学阅读,两下合力,旨在解决当下人们在阅读上的普遍严重疾患——路易斯口中的“时代势利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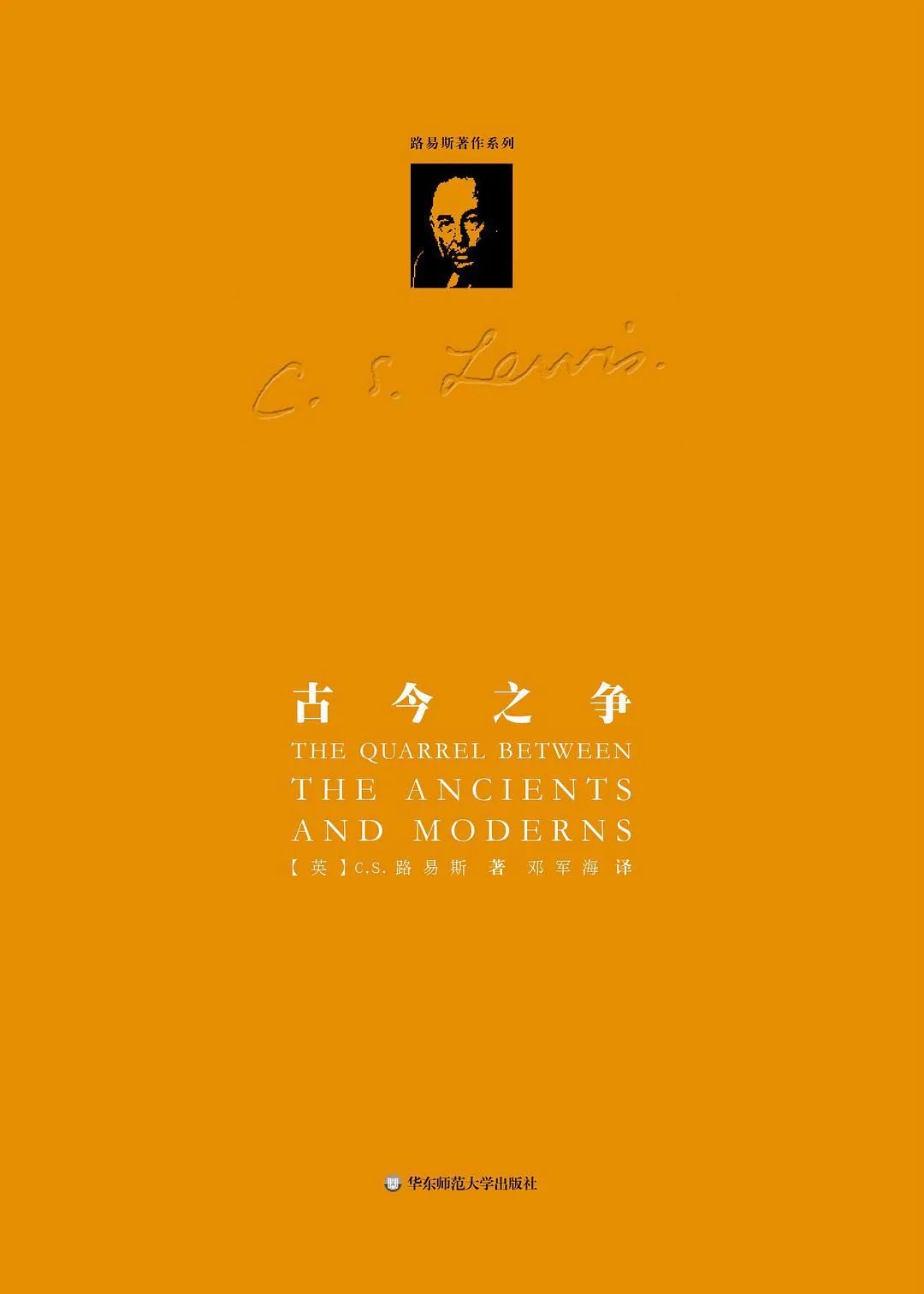

↑ 扫码购买
我们需要对过去有一种密切的认识。并不是过去有什么魔力所在,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研究未来,但又需要某种东西作为现在的参照,来提醒我们,不同的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基本假设,许多在未蒙教化的人看来确凿无疑的东西,无非只是当时的风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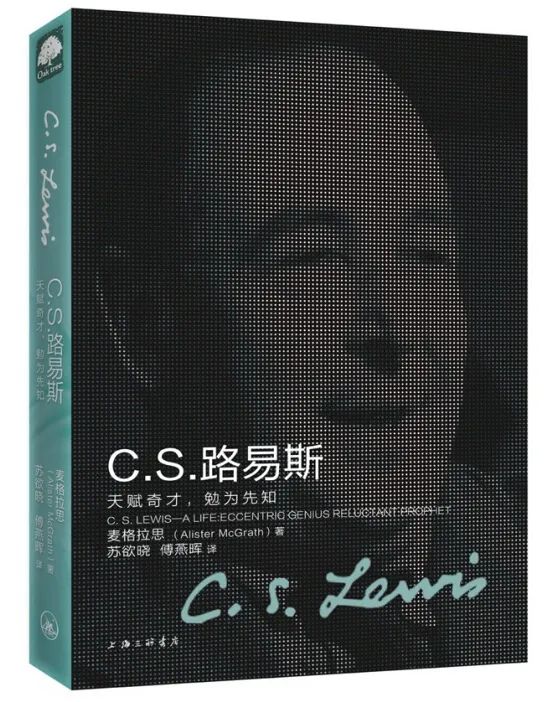

↑ 扫码购买
购买路易斯所著图书,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