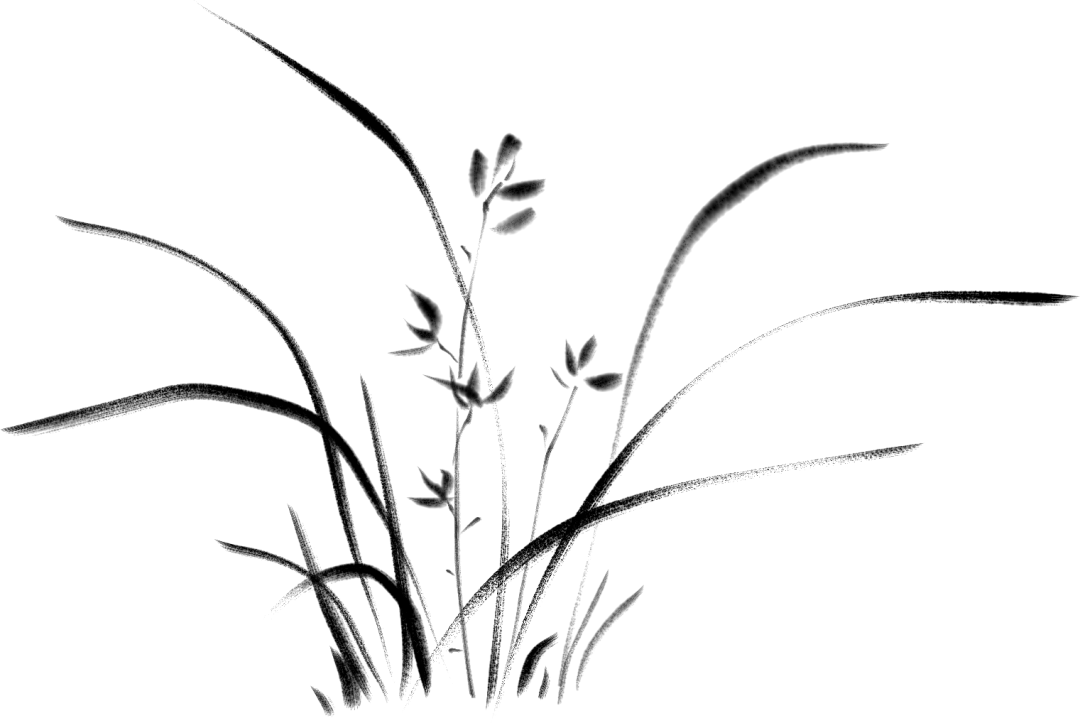当妈之后
作者/如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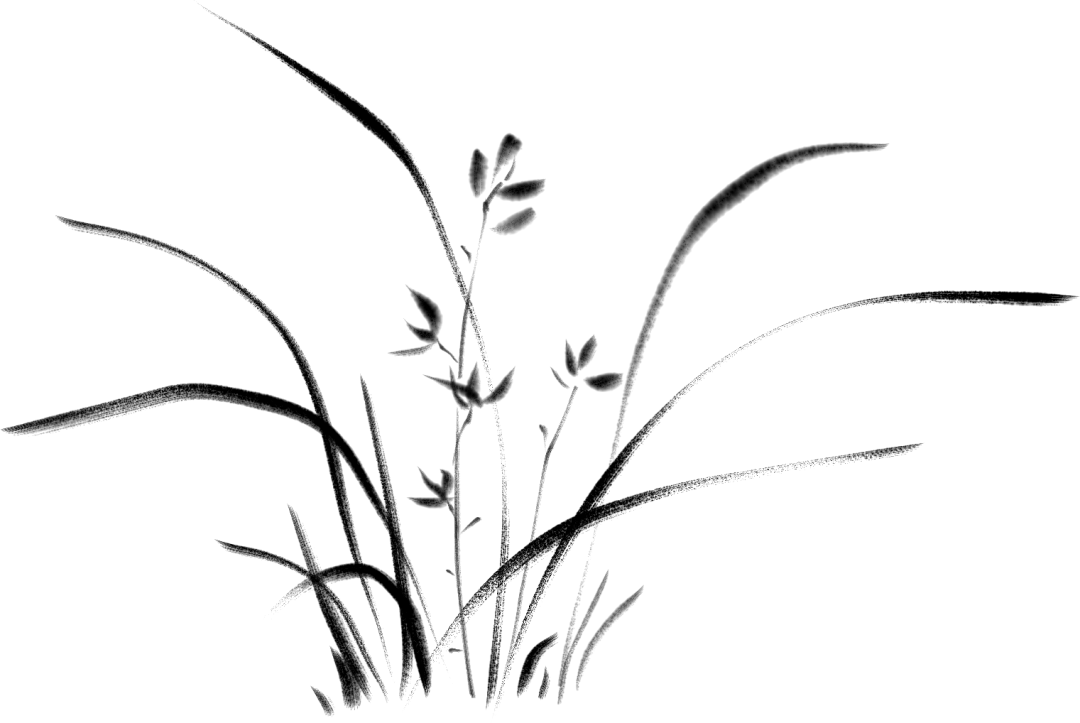
当妈之后,我开始知道“怕”。
六岁时,同院住的二妈死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媳妇,算是小口少亡。等待发丧期间,邻居们吓得骨寒毛立。我妈天一擦黑就不敢出门,那副心乔意怯的样子,我仍记得。
我竟然不怕。
一天,爷爷要去停放二妈的屋里取东西,我跟着。爷爷明知,没有阻止,大约他也希望有个人陪,哪怕是小女孩的我。进去,我看着躺在门板上的二妈,熟悉的是脸,陌生的是装束,奇奇怪怪,还扎个头巾。
出来后,我向我妈讲刚才看到的情形,她怛然失色,目瞪舌僵许久,回过神后,严严叮嘱我不许再去。我心里笑她胆小。
五年级时,总在午饭后肚子痛。村医看了说可能是阑尾炎,要手术。家里人紧张,说可不可以不做手术,看能不能吃药治疗,再不行打针……他们和医生絮絮叨叨,我躺在炕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生病了治吧,吃药,打针,做手术,总之,治就行了,有什么好紧张的。虽然后来确实没有手术,输液好了。不过,那副无知无畏的心态,真令如今的我哭笑不得。
不怕死人,不怕活病的我,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与货车相撞的凶险,一分之差落榜的失意,苦尽甘未来的失恋……我被震动,被撕裂,被伤害;我紧张、失望、愤怒,单单没有怕过。
但是,当妈之后,我才真知道怕。

女人不想怀孕时,似乎极易中标;想当妈妈时,才知生命的孕育,是一件极其高妙的难事。我备孕一年多,月月落空。终于中了,千辛万苦保护,经历排山倒海似的生产之痛,小家伙生出来——七斤半。
对生时山崩地裂、惊心动魄的痛,有耳闻,有准备。哪知道生完后,山已崩塌,地已开裂,满目疮痍,那一种“后痛”,完全没想到。
产房回病房,肚子还挺大。医生举着冰冰凉的手,过来给我压腹。她一把力气上来,肚皮外的凉气裹挟着肚皮里的疼痛,如同又一次雪崩,我的牙床都快咬碎了。
第二天,不知是哪里来的巡房医生,带着两个实习生——还是男生,来了。二话不说,一把掀起被子,查看伤口,指点症状。我如同一具活体教材,毫无遮拦呈现在几个年轻异性面前,惊诧、羞耻、不知所措。生孩子疼傻了的我,等人走之后,才想起拒绝。这猝不及防的“观瞻”,真气人!
几天后,终于从医生那里获赦:可以回家。哦,回家,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如今赋予了新的意义:逃离与回归。

可回家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侧切伤口,让人怎么坐都不对。又有乳头炎,每一次喂奶,如同一场酷刑。儿子饿吼吼叼着乳头,大口大口吮吸活命口粮;我惨兮兮咬紧牙关,倒吸凉气忍着钻心之痛。这种折磨持续了十多天。疼痛,使我无力无心好好端详儿子。
终于,下面的伤口抽线,我可以稳稳地坐着,可以抱孩子。经历了剧痛之后的我,面对这个软软、小小的人儿,根本不敢抱。我妈垫着枕头,把孩子放在上面,我小心翼翼抱起来。瞧着,哇,他样子有点丑啊,脸上好多小白点点,眼睛幽黑,头发黑而茂密。抓着他的一双小脚丫,对着灯光,十个脚指头,拢进我的虎口,一握之间,像肉珠,晶莹剔透。那一刻,人生的灯,流转着暖暖的光。
那么小,那么渴望成长。而我,弱到自顾不暇,怎么养他?
这个问题,接着成了心头大石,每天压得我喘不上气。
两位伺候月子的妈,尽职地做饭和洗洗涮涮。她们大约认为我吃饱喝足就好,哪知我在卧室看着小小婴儿,胡思乱想得要疯。大痛之后有大悲,心里好像攒了一江泪水,无处流淌。生时奋力,只为让他出来,顾不上心疼自己。生后疗伤,全身无一处不痛,开始自怜。想和两位妈妈说,她们一副哪个女人不这样的架势,堵住我倾诉泄洪的闸口。于是洪水回流、漫漶在心头久久不去,淹没了路标,模糊了界碑。
伺候月子的妈妈们,压根没有想到我里面的山高水低。她俩怕影响我休息,把卧室门关起。小屋里的我,守着十月怀胎、瓜熟蒂落的儿子,巨大的爱意裹挟着强烈的恐惧袭来:我担心自己养不活他!
喂奶时,他只顾吮吸,中间累了暂停,也口不离乳,哼哼几声后继续,那么全力以赴。我看着这个娇嫩的娃娃,似乎一捏就碎,可能稍不留神就伤。摔着,烫着,病了,丢了,甚至死了……等我回过神来,已经哭得难以自抑。

怀孕时,看了一场马戏表演,里面有几个侏儒演员。从此以后,噩梦开始,生怕生下侏儒。尽管产后医生抱给我时,说宝宝一切正常;回病房后,妈妈说孩子手全脚全,我确实如释重负。但月子中,恐惧杀了回马枪:侏儒,是养着养着才发现的。这种担心放大,成为我惊恐的主流。
记忆中那些早就压叠不知所踪的人物,一个个影影绰绰蹦出来招惹我。从炕上摔下后脊椎受伤,成了罗锅的红红;伸进热锅里,手指粘连的燕燕……还有,那个在路上跑着,被拖拉机压死的孩子;那个夏天游泳,溺死的孩子;那个……
养个孩子真不易,那么多的意外,我这么弱,怎么防得住?我心里对孩子的担心,席卷了一切人生的美好和幸运,这份焦虑,远远超过生产带来的痛苦千倍。
生了孩子,一生的悲喜,就与这个生命相连。
我开始发现,自己的人生不再单属于自己,我的命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了。如果我死了,他怎么办?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我哭得泣不成声,终于被两个妈发现。
坐月子,在中国人观念中极其严肃庄重。不能吃的东西,不能做的事情数不胜数。其中,哭,是大忌。她们慌了,急急地问询。我哀哀切切、语无伦次地说了大概。
我妈一听,一改以往的戏谑。循着自己的经历,她说:“养孩子,得心大些。我养你们三个,一个也没烫着。我就是心大,不怕。你越怕越有鬼,越出事。”是的呀,农村灶炕相连,农妇活儿多,常有孩子被热水热饭烫伤的。我们仨,确实未曾伤到。我妈粗枝大叶,不也把我们养好了吗?
我妈以她的经验和实证,暂时安抚了产后忧郁的我。“不要怕!”简简单单三个字,居然成了压住惊恐的磐石,心里的恐惧狂浪止息。
君着一抹凝视
还您一片宁静
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