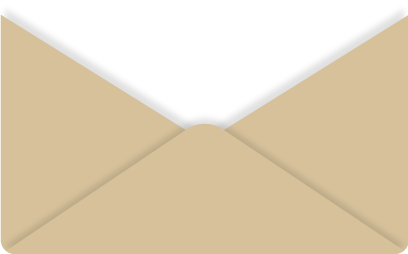編者按
《漢語神學對巴特神學的接受》壹文結合了兩篇提交給「海德堡國際科學論壇」(Internationalen Wissenschaftsforum Heidelberg) 於2005年10月27-30日所舉辦的題爲「巴特的國際性研究:核心慨念與系統視域」(Die internationale Karl Barth-Forschung. Schwerpunke und systematische Perspektiven) 國際研討會的簡短文章。第一部分由陳家富老師起草,第二部分由賴品超老師起草。另外,感謝浙江大學博士生朱彩虹女士協助從英語翻譯為漢語。原文發於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基督教文化學刊》第17輯,頁111-138,巴特研究公眾號已獲作者與學刊授權。
本文字数:13822字
阅读时间:15分钟
漢語神學對巴特神學的接受
简介
本文由兩部分組成,並帶著兩個目標。第一部分綜合考察巴特思想在漢語學界的發展,第二部分集中論述一場關於巴特基督論與大乘佛教的神學討論。第一部分的考察指出巴特思想在漢語語境還未得到充分發展,並且一直以來受到英語學界,特別是蘇格蘭,而非德語學界的決定性影響。然而,正如本文第二部分就巴特基督論與大乘佛教的討論所延伸對巴特的解釋,表明漢語神學有可能爲巴特的國際性研究發展出一些相當特殊的貢獻。
2
巴特神學在漢語學術界的來臨
巴特神學很可能在1939年首次進入漢語思想界和教會界,當時趙紫宸(1888-1979)[1]在中國大陸出版《巴德的宗教思想》[2]一書。他當時像其他遠赴海外的基督教知識份子一樣,受自由神學深刻影響。然而,在1932-1933年間,當他在英國學習時,開始認識所謂的新正統神學,這種神學當時在英語神學界影響很大。從《巴德的宗教思想》這本書中可以發現,通過英語學者的介紹,趙紫宸開始接觸巴特思想。[3]《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和《教會教義學》I/1是他的主要資訊來源或參考書目。雖然趙紫宸對巴特神學的解釋並非前沿或獨創,但巴特思想似乎對趙紫宸的個人思想起了轉變作用。
在學習巴特神學前,趙紫宸早期致力於發展一種使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文化相互補充的模式,他的基本神學定位趨向一種具備某些自由主義特徵的神學——強調耶穌的個人生活所提供的理想模範或榜樣,把基督教當成對生活的一種哲學理解,提議通過消除那種基督教的西方視角來建構漢語神學,使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智慧更爲和諧。爲了促進這種文化神學,趙紫宸從頭到尾刻意回避了基督教的超自然因素。
然而,巴特的《羅馬書釋義》第二版徹底改變了趙紫宸的神學方向,他認爲巴特神學由一種抗辯精神所構成,抗議人類文化抵達上帝的任何嘗試![4] 人與上帝之間無限的存有論差異拒絕所有這類使得人類文化絕對化的嘗試。如果尋求基督教神學與中國文化的關聯是趙紫宸早期思想的焦點,那麽,重新發現基督教的獨特性則是他後來思想的主旨。這種神學定位的改變似乎主要是他對巴特思想的挪用所導致。在趙紫宸看來,傳統改革宗神學的「有限不能承載無限」( finitum non capax infiniti) 爲巴特提供了一種武器,與從下而上來建構一種文化神學的所有嘗試以及當時的路德神學相抗衡。[5] 相應地,上帝的超越性、從上面降臨的啓示和耶穌的道成肉身爲趙紫宸重新思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提供了框架。相互補充這一模式不再有效,因爲如果它有效,那麽根據巴特的提議,基督教可能會被還原爲一種宗教智慧或者人類文化。趙紫宸寧願清楚地表達符合巴特早期神學的一種「基督高於文化」的進路。
其實,趙紫宸只介紹了巴特神學的一小部分。巴特神學留給漢語學術界的第一印象是一種辯證的二元論,它爲中國基督徒批判地重新思考自身神學的建構提供了一個重要參考點。有趣的是,七十年後,巴特的辯證神學在漢語基督教話語中被尋回,並形成了類似功能。
3
在巴特神學影響下對本色神學的拒絕
3.1 在漢語神學中「直面基督事件」
中國大陸學者劉小楓提出的漢語神學,旨在對應中國大陸特殊的學術和政治語境,它明確帶有早期巴特辯證神學的特徵。劉小楓對過去中國學者提出的所謂本色神學持批判的態度。他認為,這些本色神學的基本預設是錯誤和誤導的,因爲本色神學預設著基督教神學等同于西方文化,結果是,本色神學家試圖在建構本色神學時就剝掉西方文化的外衣,並相信這是重新獲得基督教神學的根源的唯一方式。對劉小楓而言,「問題並不在於所謂基督教的中國化,而在於漢語言之個體言說領承和言說基督性,使聖愛之言成為漢語言的具體的說。」[6]

劉小楓教授
在劉小楓看來,基督教在漢語語境中的植入是與漢語中經驗到的神聖之道的一種垂直相遇,而非基督教文化的一種水平移植。這樣一種垂直相遇指的是對基督教生存經驗的一種語言轉換,作爲基督(上帝之道)與某種文化語言相碰撞的一個結果。這種與神聖者相遇的經驗是一個後宗教事件。[7] 在這裏,劉小楓區分了兩種基督教神學:具體的歷史-地域的基督教神學,理想的基督教神學。前者無法取代後者。後者是「預設上帝的特定歷史啓示(基督事件)」的基督教神學,前者僅僅是後者的一個歷史的、具體的模式。[8] 漢語神學必須考慮的不是與歷史-地域基督教神學的一種相遇,而是上帝在基督裏所啓示的基督事件與人之間的一種相遇。每一個文化和語言體系都與基督事件相遇,由此具體産生一種歷史的基督教神學,帶著該文化的特定特徵。那麽爲什麽當前漢語神學不能像在其他文化和語言領域中所發生的那樣,經驗與基督的相遇呢?因此,
對漢語基督神學發展而言,要考慮的問題首先是自身與理想型態的基督神學的垂直關係,即漢語思想的語文經驗如何承納、言述基督事件和反省基督認信。因此,漢語基督神學就必須考慮其言述的重新奠基問題:從本色化或中國化的思維框架中走出來,直接面對基督事件。[9]
對劉小楓而言,巴特的辯證神學暗示這樣一種理想基督教神學模式。作爲一個個體歷史事件的基督之道,意味著基督事件首先是一個道成肉身的事件。在他看來,這個事件如巴特所提出的,「這不是自然歷史之事件,而是神聖入世之事件。此一事件乃上帝的話語突入自然形態,使個體之偶在生存的依持之根本性重設成為可能;儘管此一事件在某一特定民族和地域中具體地發生,不等於它即受限於某一特定民族和地域性的事件。」[10] 正如巴特所言,在神聖之道與人之言之間存在無限的存有論差異,只有當上帝之道闖入人之言的存在經驗時,神學才成爲可能。根據巴特的觀點,儘管這一基督事件發生在歷史中,然而它並不屬於歷史!歷史批判學絕不能談論上帝的道這一奧秘。其次,劉小楓認爲基督事件的情形是一種「此世的信仰事件」,「關涉個體之在性的二元品質及其重新彌合之可能性」,這一信仰事件事實上是「此世的肉身偶在相遇那聞所未聞而聞,見所未見而見的來自另一截然異樣的處身維度的原初言詞,進而不可言說而說。」[11] 對於他和巴特而言,作爲神聖之道的基督事件是來自他者的道,這種異質的言說維度是漢語思想絕不能窮盡的一種話語。歸功於基督事件的闖入和繼而發生的信仰的超驗轉變,本來不可言說的變成可以言說的。這難道不是早期巴特的辯證神學所強調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嗎?唯獨「信仰」使之成爲可能。
相應地,帶著這種巴特神學的定位,劉小楓描繪了漢語神學的獨特性,將它與所謂的「文化哲學」或「文化神學」區分開來。漢語神學應當強調「上帝的自我陳述的話語與人摸索的話語在本質上既無類比性亦無連續性。」[12] 正如巴特所言,在人的言與上帝的道之間沒有存有類比 (analogia entis),存有類比唯獨在於信仰類比 (analogia fidei)。因此,劉小楓爲漢語神學提供了一個簡單清楚的定義:「基督神學而言,本質上是關於個體認信—個體與上帝之關係的話語。在涉及與歷史—民族文化的精神觀念的相遇時,話語最終只是認信或拒信的個體表達式 …信仰在本質上是個體與自身的鬥爭。」[13] 同時,在上帝的道和人的言之間不存在可比性,然而卻可以用一種辯證的思考來理解。上帝與人之間的這樣一種辯證模式恰好是對巴特神學的一種應用。劉小楓認為,於巴特而言,
「辯證」首先意味著自認人的思維的破碎性:人的思維永遠處於矛盾的各部份之中,根本沒有指望能獲得綜合,綜合只為上帝所保留……人之思想處於如此悖論之中:必須言說不能言說的,……人與上帝的真實關係處境只是一種辯證的處境……有辯證的綜合嗎?……所謂有,乃是指耶穌基督即是綜合……然而,所謂沒有綜合,乃是因為,說到底,耶穌基督的位格存在依然是辯證存在。[14]
毫無疑問,劉小楓對漢語神學的建構明確預設了早期巴特的辯證神學。在對一種生存狀態(是漢語與基督事件的一種直接相遇)的建構中,他從巴特神學語言和該語言背後的神學精神中借鑒甚多。「直面基督」這一神學方案受到多方批評。[15] 然而,劉小楓對巴特神學的應用大大增強了中國大陸學者對於巴特神學的這種先知式的批判精神的興趣。對巴特的這種解釋和應用的流行,可能部分歸因於它所牽涉的意識形態批判。正如在其他地方已經提到的,[16] 劉小楓對於巴特的解釋和應用與他對政治極權主義的抗議相關聯,後者把政治領導的話語當成絕對真理。就劉小楓而言,這就類似於混淆人之言說和上帝神聖之道的偶像崇拜,因而要拒絕。這種對於政治意識形態的隱性批判很容易爲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知識份子所洞悉和分享。
3.2 以巴特方式做神學:來自臺灣語境的反思
劉小楓的神學建構在臺灣基督教學術界得到反響。台灣學者歐力仁對於巴特的解釋與重新建構可以在他《信仰的類比》[17]一書的8篇論文中找到。在其中一篇題爲〈無限的本體論差異:巴特與哈赫克的公開討論〉的論文中,歐力仁指出,巴特強調上帝與世界、神學與科學、啓示與理性的無限存有論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巴特的這一信念:福音應該與文化相分離,福音能夠改變文化。因此,臺灣長老教會提供的不同種類的本土神學運動,例如,敍事神學、第三眼神學、臺灣解放神學和鄉土神學等等,基本上都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神學,或者是一種基於人類學的宗教多元論。[18] 歐力仁指出,這些本土神學的弱點是,忽略在耶穌基督裏彰顯的超越性和獨特啓示經驗。簡而言之,文化與政治議程不能成爲基督教神學的起點。神學的人類學化將導致把人和文化神格化的危險。[19]
有趣的是,歐力仁對巴特的研究旨在為臺灣社會政治問題作出神學的回應。巴特這種具有處境特徵的研究也可以在林鴻信所提供的研究中找到,林探索了巴特的虛無概念、及其對臺灣的含義。[20]
4
啓示與自然神學
余達心很可能是第一位介紹巴特神學的香港神學家。在1980年,他在《今日華人教會》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巴特神學思想的簡短文章。在這五篇文章中,他概括了巴特神學從自由主義時期到《教會教義學》的內容及發展。[21] 在對巴特較成熟神學思想的考察中,余達心提到,上帝之啓示的現實性先於可能性。同樣,上帝之道的客觀性先於主觀性。[22] 雖然上帝的存在在於他的行動中,但是上帝的現實性或存在先於上帝的行動。在其自身的上帝(God-in-himself)與為我們的上帝(God-for-us)密切相關;前者是後者的基礎,而不是相反。同時,余達心反對一些福音派就巴特宣稱否定復活的歷史性和《聖經》的啓示特徵而對他提出的批判。首先,余達心認為,巴特實際上拒絕布爾特曼(R. Bultmann)對於兩種歷史觀(Geschiche和Historie)的區分。在巴特看來,Historie指的是歷史科學,它是以自然科學爲指導的一種方法論,而Geschiche是真實的歷史事實。對於巴特,復活是Geschiche,而非Historie。針對後者,要預設許多未經證明的特定假設。其次,《聖經》是否上帝的道?巴特區分了上帝之道的三重含義,耶穌基督作爲上帝的道、《聖經》作爲上帝的道、以及來自教會的宣教。根據余,上帝的道是一個事件的發生(a happening),而非一個事物(a thing)![23] 這意味著對聖靈與《聖經》的書信應當從正反兩方面加以思考。在巴特看來,應該拒絕《聖經》字面主義。在一個總結性評論中,余達心提到巴特神學中的兩個弱點。一個是三一論思想中的模態主義 (modalism)傾向,另一個是普救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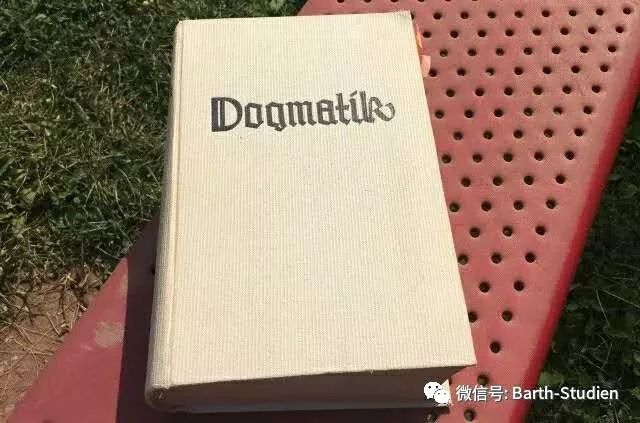
《教會教義學》
在這一階段,香港學者對巴特的接受主要由教會關懷而非政治語境所決定。在這一點上,它與臺灣的情況、而非中國大陸的情況更具有可比性。然而,後來發生了相當引人注目的變化。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起草,香港人不得不面對1997年「回歸中國大陸」這樣的安排。香港人,包括基督徒,不得不面對1997問題所帶來的挑戰,包括是否、以及如何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公民去生活的問題。在1987年,香港神學家楊牧谷(1945-2002)[24]完成了《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25]一書,對整個情況做出神學的回應。在這本書中,楊牧谷在1997這一背景下詳細闡述了複和這一基督教教義的意義,提出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一種複和關係。在這一接合點上,他大量參考了巴特對復和的討論,在巴特《教會教義學》中,神-人復和關係的焦點在耶穌基督其人及事工中,耶穌基督是上帝與人類之間永恒的約。[26] 耶穌基督的神性與人性修復了上帝與人類之間的破裂關係。楊牧谷強調,在巴特神學中複和教義與基督論相互關聯。[27] 在耶穌基督裏彰顯的上帝是為我們的上帝(God-for-us),而非完全的他者,上帝在耶穌基督裏成爲為我們的上帝(God-pro-me),是出於上帝自己的自由選擇。[28]
與楊牧谷這種對巴特高度處境化的研究不同,香港近來的巴特研究集中於一些不那麽政治性的問題。討論的焦點之一涉及巴特與布魯納(E. Brunner)的自然神學之間的爭論。一些學者試圖調和巴特代表的啓示神學與自然神學的緊張關係,他們認為,啓示並不必然與理性和自然相衝突。這就是說,他們試圖在巴特神學中重新安置自然神學。然而,這樣一種嘗試遭到巴特學者的強烈抵制,他們認為,巴特神學特別提醒我們,自然神學闖入基督教神學會帶來嚴重後果。
關啓文提出,自然與恩典並不如巴特所說的那樣沒有連續性。與巴特相反,他指出,一旦自然與恩典相分離,一個人如何能夠爲自己的行動負責?那麽,人還能稱其爲「人」嗎?此外,人類理性有可能證實基督教啓示的優越性。[29] 他試圖指出一條中間路線,以便平衡哲學進路與啓示神學的進路;前者完全擡高理性,後者完全否定理性。對於關啓文而言,上帝的啓示並不限於基督事件中的神聖彰顯,在普遍啓示與特殊啓示之間不存在反對或對抗,許多《聖經》段落能夠爲自然神學提供《聖經》基礎。他不擡高理性,也不把自然看作比恩典更重要。他提出,
世上並沒有「沒有神幫助的理性」這回事,每一個正確的推理也是靠賴神的恩典托住 …所以當我們正確地使用理性時,這是自然,也是恩典,我們實沒有可誇、可恃之處。若理性也可用來判別「啟示」,這全因為墮落之後,神仍然保守我們的理性,預備我們去迎接神的至高啟示,既然如此,使用神恩賜的理性能力如何會危害啟示的完整性和首要性呢?[30]
根據麥奎利(J. Macquarrie)的觀點,關啟文認為,為自然神學論證是必要的,因爲它從總體上把神學家與經驗世界聯繫在一起,不會使基督教信仰與世界看起來彼此孤立。[31]
關啟文的提議受到陳士齊的批評。陳在文章《巴特:自然神學的抗辯者》[32]中指出,巴特對自然神學的抗辯不僅是他的畢生神學發展中的某一個階段,不是來自對「文化新教徒」和「德意志基督徒」的一種偶然抗辯。巴特在自然神學方面的堅定立場不是來自歷史上的偶然位置。[33] 陳士齊認為,巴特在一生中從未改變他對自然神學的態度,反而是越來越否定自然神學。
早期巴特由於深切體會人神之間無限的性質區別,而否定自然神學的可能性;後期卻正面了解到基督道成肉身已經成為了神人之間的有效接觸,才在實在層面否定自然神學 …從一種否定式的二元論,逐漸進到一種肯定式的互動神學。[34]
陳士齊批評關啟文沒有從內而外理解巴特。巴特宣稱:神學本身必須否定自然神學!神學的基礎是上帝的啓示!自然神學的方法論來自自然理性之光,通過自然理性來實踐,因此它完全是一種非神學的方法![35] 陳士齊認爲,巴特不僅告訴我們基督教的上帝是誰,而且甚至指出了認識這個上帝的方法。上帝的存在和他的行動是不可分的,既然上帝想要在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中啓示他自身,那麽對於上帝的認識只有通過這一聯繫點才有可能達到!因此,巴特的貢獻是「將神學方法論後置於神學研究的對象。」[36] 鑒於這種巴特神學進路,所有自然神學和所有非啓示性宗教哲學都不能進入上帝的啓示。
江丕盛也提到,巴特對於自然神學的拒絕是基於一種神學基礎,而非基於自然神學的學術表現或者它所提供的合理性。江的一篇題爲《巴特對自然神學否定的知識論意義》[37]的文章強調,上帝的啓示是神學的預設。如果這樣,那麽,只有上帝才能啓示上帝。自然神學無法繞過上帝的啓示,在神學中佔有一個位置。神學認識論只有在上帝存在這一語境中才能夠爲人理解。在他看來,巴特清楚地說明了,上帝自身是啓示的主體與客體。[38] 自然神學試圖通過建構某種條件和前見來建立一種屬人的認識上帝的方式。然而,巴特斷言,對於上帝的認識是上帝所提供的一種恩典。[39] 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啓示自身,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因此,人類通過自然啓示認識上帝這一點是未經證明的或者不合法的。
應該注意一個有趣的現象:上述提到的大多數香港和臺灣巴特學者都受到蘇格蘭神學景觀的強烈影響。雖然余達心和楊牧谷各自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完成博士論文,但兩人都於1970年代在愛丁堡大學學習,他們與著名的蘇格蘭神學家托倫斯(Thomas F. Torrance)有密切的學術和個人關係。後來,江丕盛在托倫斯(James Torrance)的指導下於阿伯丁大學完成博士論文,該論文內容是關於托馬斯(Thomas F. Torrance)神學中耶穌基督的人性論。關啓文和陳士齊在阿伯丁大學完成神學學士。歐力仁亦是在蘇格蘭聖安德列大學完成博士學位,似乎蘇格蘭神學對巴特神學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香港和臺灣對巴特神學的接受,尤其在1980年代期間。[40]
5
巴特與比較宗教
5.1 巴特對宗教的理解:對漢語神學的一個思考
賴品超指出,在西方學術界,巴特神學由於其基督中心論常常給人留下一種排他主義印象,然而,事實上,巴特對於宗教的神學理解比這樣一種宗教神學複雜得多。[41] 就《教會教義學》I/2中一個題爲「作爲宗教之揚棄的上帝啓示」的部分,賴品超指出,「揚棄」(Aufhebung)不是一種純粹否定,它可以指「取消」 (annulment)、「提升」 (elevation)和「保存」(preservation)。[42] 上帝在宗教世界裏的在場是一種審判與複和的辨證在場。所以,對於巴特,宗教問題涉及上帝與宗教之間的垂直關係,而非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水平關係。基督教神學應該處理的是這一問題:從上帝的啓示來看待宗教,而非把宗教當作用來解釋上帝的啓示的標準。因此,巴特在根本上談論的是「宗教」(Religion)而非「諸宗教」(religions)。這就是說,「宗教」是人類通過自身努力來證明自己,並拒絕上帝的恩典的一種嘗試。[43] 因而,巴特清楚地指出,「宗教就是不信」!這一斷言也適用於基督教,因爲在基督教中也存在「不信」,所以,基督教必須接受上帝的審判。
在一種語境反思中,賴品超認爲,巴特絕不會反對亞洲神學家利用本土文化資源來建構一種本土神學,巴特最爲關心的是,是否本土神學會成爲對於基督教的一種特定形式或者一個特定方面的擡高或吹捧。[44] 此外,在對巴特神學的解釋中,賴品超指出,儘管宗教對話不是巴特所關注的方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巴特會反對神學與世界的任何對話。在亞洲背景中,一些基督徒可能會貶低其他宗教,從而試圖贏得與其他宗教的爭論。然而,根據巴特的神學,這是不必要的!因爲把基督教當成高於其他宗教很可能是不信的一種表達。賴品超提出,巴特神學可以提醒神學家,當進行宗教研究或者宗教間對話時,不需要失去自己的宗教身份,但同時也不應該吹捧自己的宗教。[45]
5.2 耶儒對話中的巴特
在題爲《人性與基督:巴特的基督論人觀與耶儒對話》的論文中,陳家富試圖初步闡明巴特的基督論人觀在耶儒對話中可能做出的貢獻。他指出,基督教與儒家在過去的敵對關係似乎是不必要的,並找到基督教神學與儒家思想在人觀問題上的許多相似之處。[46] 陳家富從巴特人觀的分析入手,指出人的存有論置定(ontological determination)是「成爲人就是與上帝同在」(to be a man is to be with God)。[47] 這樣一種存有論置定只有在耶穌基督裏才能完全實現,因爲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在他那裏,神性與人性在一個人裏面完全統一。根據巴特的揀選論,唯獨耶穌基督是進行揀選的上帝和被揀選的人。再者,「非實體—在實體」(anhypostasis-enhypostasis) 的基督論框架清楚地表明,在基督裏體現的人性是一種無法與神性相分離,而是必須與神性聯繫在一起的人性。[48] 在陳家富看來,巴特對於這樣一種本質的人性——既包含神性又包含人性——的強調非常接近儒家的理想人格概念。
首先,因爲基督教與儒家思想都在原則上贊同人的本性的本質部分是善的,所以雙方事實上都能贊同人在存有論上是「天人合一」,或者「既包含神性又包含人性」,這正是巴特對人類的存有論置定的理解。[49] 其次,在巴特的揀選論中,人的本性是上帝賦予的,就是說,人的存有論置定是基於上帝的揀選。這正好類似於儒家《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的思想,據此,人性的善是內在所固有的,是由超層級(trans-hierarchical)的天所安排和賦予的。[50] 因此,在人性本善的人類學立場上,儒家與基督教可以在巴特神學中找到一個聯繫點。
鄭順佳在著作《唐君毅與巴特:一個倫理學的比較》中試圖描繪巴特神學與當代儒家學者唐君毅(1909-1978)的思想在倫理學上的相似之處。[51] 在鄭順佳看來,儘管巴特的神學體系與唐的儒學體系之間存在實質性差別,但是他們之間在形式上有巨大相似之處。[52] 首先,兩者都從一種具體—普遍性進路(concrete-universal approach)來理解人的本質,將人的本質看作一種理性存在。其次,當比較他們倫理學的形而上學基礎時,我們發現,他們都贊同倫理學的形而上學基礎是一個動態的終極實在,唯一的不同之處是,是否把上帝或天看成是人格的。第三,他們都以「命令-順從」的形式定義倫理學的本質。鄭提出,巴特的倫理學擺脫了「行爲-義務論」的框架,對於巴特而言,上帝的道德命令是完全實現人格的一個重要基礎。在這個方面,它與儒家的主題相一致。[53]
然而,在這些試圖縮短雙方距離的比較研究中,也存在對立面。在對鄭順佳著作的評論中,鄧紹光明確指出,在這種強調相似之處的研究方面有所保留。[54] 他認為雙方的差別在於他們對於「神人差異」和「天人合一」 的理想類型,兩者完全背道而馳。儒家的「天」與「本性」合一是內在固有的;人的「心」是一種超越的自我意識。這種本質上自我超越的自我不需要是「他者」。然而,在巴特神學中,上帝與人之間存在一種無限的存有論差異,他們之間沒有存有的類比。此外,儒家強調道德實踐中人的自由,這是一種自主的自由,它導向帶有道德意識的主體性的形成,然而,巴特的神學恰恰反對這種主體性,因為它取消關係性存在,忽略他者,認爲唯獨它自身是至關重要的!巴特所強調的自由是一種順從、傾聽,是在恩典引導下的自由。因此,鄧紹光認為,雙方不可能在更爲基本的問題上獲得一致。[55]
此外,韓國學者金洽榮(KIM Heup-young)比較了王陽明和巴特所代表的兩種範式,並指出這兩種範式在一個共同問題上是「非常相似」:如何成爲一個完全的人。[56] 他認為,在教化的根源隱喻(root-metaphor)中,巴特的成聖說與陽明的自我教化觀點基本上是類似的,可以相互比較。「自我教化的目標是實現隱藏在原初人性中的真我(良知),而成聖的目標是實現真正的(揀選的)本性。」[57] 然而,香港學者郭鴻標宣稱,在金洽榮的論證中有幾個弱點。首先,他質疑是否基督的人性(Humanitas Christi)能夠作爲巴特神學的核心與解釋原則。[58] 根據郭鴻標,「金洽榮無法給出對於巴特基督論的一種全盤理解。」[59] 另外,他也沒有注意到巴特神學中稱義與成聖的密切關係。[60] 第三,在他解釋巴特對於(作爲上帝的形象的)基督的人性所持的觀點時,金洽榮忽視了神人關係與三一論。[61]
6
漢語語境中的巴特與大乘基督論
鄧紹光與賴品超就巴特的基督論和大乘佛教開展了一場重要的討論。[62] 兩人曾合編了一本關於巴特與漢語神學的書,[63] 但似乎他們對於巴特的理解彼此不同。
衆所周知,基督論是巴特神學的核心。[64] 英國和德國學界關於巴特的基督論有大量研究,但似乎很少關涉到與佛教的對話。[65] 一些學者可能假定,巴特神學即使並不排外,也是過於基督中心論,因此不適合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對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巴特的基督論卻或明或暗地在最近漢語神學界就大乘基督教神學的討論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而大乘基督教神學試圖以來自大乘佛教的觀念重新系統闡述基督教神學。
6.1 巴特的基督論——從後臺走向前臺
這場討論始于賴品超的一篇題爲〈從大乘佛教看迦克敦基督論〉的文章。[66] 當中提出根據大乘佛教思想,包括借用如來藏的思想(強調人的本性或心靈的純潔,以及所有有情眾生在本質上的平等),重新解釋迦克敦信經的基督論程式。依此,因爲耶穌基督是沒有罪的完全人,所以,有可能由此得出一種肯定人性的純潔和良善的人性觀。在這一接合點上,論文提到巴特的基督論,尤其包括他的基督論人觀,目的是支援這一論證:如果人從基督論的觀點看,而不是從人的行爲的經驗觀察來看待人的本性,那麽他就能夠肯定,真正的人性與上帝是相一致,而不是與罪相一致。 [67] 論文沒有直接提到巴特的著作,取而代之的是,它指向上面提到的陳家富的研究。[68]

賴品超教授
在鄧紹光發表他的論文〈從天臺宗佛學看巴特的基督論〉後,巴特的基督論成爲討論的焦點。[69] 除了以使用如來藏思想,尤其是在《大乘起信論》中「一心開二門」可能導引出幻影說這一點爲基礎來批評賴的文章外,鄧論文的主體部分是以中國佛教天臺宗觀點來重新解釋巴特的基督論。
鄧紹光提出,巴特基督論一個相當特殊的特徵是:耶穌基督所假定的人性是有罪或墮落的,而非中立或無罪的。根據天臺宗提出的判教理論,圓教有如下特徵: 一念無明法性心、本是無本、「即九界而成佛」皆可有助說明巴特的基督論中神性與罪性的吊詭性結構。從這一視角來看,鄧紹光提出,巴特基督論連同它根據「非實體—在實體」(anhypostasis—enhypostasis) 對迦克敦基督論做出的解釋,可以說是一種圓教,因爲它肯定神性與罪性在基督的實體聯合 (union hypostatica) 中吊詭性地共存。因此,鄧紹光指出,
“別教的基督論必然不會以人的罪性為基督的存有結構,僅只肯定基督具有人性而已。但若基督不具罪性,則衪必然不是一個在世存有(Being-in-the World),不具有罪惡的世界在其內,那麼祂又如何可以拯救世界?”[70]
6.2 人觀的基督論進路——巴特的幽靈
賴品超在他的論文〈罪身、罪性與如來藏:一個基督論式人類學的探討〉[71]中給出了一個反駁,作爲對鄧紹光論文的回應。賴品超贊同,當應用於迦克敦基督論時,用天臺宗框架來解釋實體聯合(the hypostatic union的吊詭性質是很有用的。然而,爲了避免與「本性」(nature)這個詞聯繫在一起的含糊性和可能的誤解,在基督吊詭性構成中的人這一極(pole)應該理解爲罪身(sinful flesh),而非罪性(sinful nature)。對於人這一極的這種理解更加符合迦克敦定義,後者指出神人二性的區別絕不會因聯合而被取消反得以保存。如果罪性是人性的一個必然部分或者全部,那麽根據迦克敦程式,這種罪性在實體聯合 (the hypostatic union)中應該被保留,而非被克服。這將會引起這一問題:這種罪性是否會完整地保留在復活的基督裏,直到永遠。一個更好的選擇是,從主張佛陀本性與眾生本性相同的如來藏思想這一視角來解釋迦克敦定義,而不是以罪來定義人的本性。如來藏傳統認為,即使人的本性吊詭地處於一種經驗上墮落狀態,但本質上仍是「清淨」的(就是說,有成長、並潔淨自身的力量),相應地可,以肯定,基督的人性在本質上並非不同於其他所有人。在神聖恩典下,基督的人性能夠擁有不犯罪的罪身,它展示了人的本性的全部潛能,或者作爲造物的人類在上帝的恩典下有可能是清淨。人性連同神性在實體聯合(hypostatic union)中得以保留甚至增強,這意味著真正的人性應該根據它向神聖者的開放和由此而來的戰勝罪的能力來理解。因此,復活和隨之而來的在永恒中這種受祝福狀態,可以理解爲是對人性的一種進一步實現或完成,而非一種否定或減少。
論文結束部分提出,除了天臺宗提出判教,中國佛教的華嚴宗提出了另一個判教的體系,同樣值得基督教神學加以考慮。
特別透過過艾雲(Edward Irving)這位以認為邏各斯所取的是有罪肉身而著稱的神學家,論文論證,甚至對於艾雲而言,他對基督肉身的有罪肯定也不忽略這一點:因爲基督是人性的目標,所以,人性在其最初與最後是純潔的。換句話說,人性本質上是純潔與神聖的。巴特在其《教會教義學》中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洞見。賴品超的論文副標題似乎暗示,論文所闡明的觀點背後是巴特對人觀與罪觀的基督論進路。然而,值得強調的是,論文只有一次提到巴特基督論——並且是在引用鄧文時,賴品超的論文本身沒有詳細說明巴特的立場。[72]
6.3 是否追隨巴特?
鄧紹光在他的文章〈也談罪身,罪性及方法的問題〉[73]中繼續這場討論。鄧在論文中提出六點,而最後一點針是對蘇遠泰的一篇文章。
除了重申用《大乘起信論》中「一心開二門」來解釋基督的人性會導向幻影說(文章的第一點),鄧紹光還試圖澄清艾雲的基督論立場。他認為,艾雲所說的罪身的意思是罪性(文章的第二點),艾雲根據基督其人對聖靈的順從和依靠,而非透過「自主的本性」(autonomous nature)來理解基督的人性(文章的第三點)。鄧紹光另外補充了與巴特更爲相關的兩點。文章的第四點是,
“我們不必以迦克敦基督論的立場為,若非主張以基督的為有罪的人性便是主張基督的人性為無罪;這是因為迦克敦信經只論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之間的關係。 ”[74]
易以言之,迦克敦定義所提出的關於基督的神性與人性的關係問題,並沒有神學人觀方面的重要關聯。他的第五點是:“關於圓教,拯救上的圓與終末上的圓,並非互相排斥。前者指向後者,而後者暗示前者。”[75]
對於迦克敦程式的評論顯示,鄧紹光沒有追隨巴特總體上對神學的基督中心主義進路、以及具體對人觀和罪觀的基督論進路。他承認,如果接受罪性爲基督的人性的一個本質部分或必然部分,那麽在解釋迦克敦程式時會出現一些困難,因爲這可能暗示基督有永恒的罪性。出於這個原因,他寧願把迦克敦定義理解爲嚴格針對僅僅塵世的耶穌基督的人性與神性的關係。它與理解復活之後的基督或者人性,應該沒有認識論上的牽連。然而,這正是賴2000年文章中所隱含的對人觀與罪觀的基督論進路,它在賴2003年的論文副標題中得以明確敍述。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在賴2005年發表的最新近的反駁中得到明確討論,這篇反駁則廣泛地涉及巴特。[76]
與之前兩篇文章不同,賴的第三篇文章集中在巴特的基督論。這篇文章的主要目標是雙重的。一方面,它試圖探討巴特的基督論人觀和罪觀,特別是對佛教與基督教對話的含義。另一方面,它努力對鄧紹光的觀點提出回應,相應地,文章分成兩個主要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賴品超論證,根據巴特的迦克敦式基督論,特別是從已經戰勝罪的復活基督的視角來看,罪被認爲是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依此,雖然罪是一種人類現象,但是真正的人性,正如在耶穌基督裏所顯現的,是排斥罪的。在巴特看來,因爲罪被認為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故此無關涉於真正的人性,這完全取決於上帝恩典的揀選,所以,沒有任何理由在教義上或實踐上爲罪辯護。賴品超進一步詳細闡述,根據巴特的觀點,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已經被信仰喚醒,但每個人都在成聖途中。這一觀點類似於《大乘起信論》中的空性思想。[77]
回應鄧紹光認爲在巴特神學中基督參與在人的罪性的強調,賴品超提出,這十分符合天臺佛學所提出的、強調圓融性的「圓教」。然而,這是對巴特神學的一種相當片面的理解,沒有注意到巴特基督論在其他方面,更接近強調「圓滿」特徵的華嚴佛學。「圓教」中的「圓」有圓圈或圓形的意思,而描述圓教時,則可理解為「圓融」或「圓滿」(完全或實現)。天臺採納「圓」的前一種含意,強調善與惡之間的吊詭性的合一,華嚴卻採納後一種含意,強調所有有情眾生的實現或完全。賴品超提出,鑒於兩人對巴特基督論的說明,巴特的基督論作爲一個整體是結合了華嚴和天臺提出的圓教的特徵。[78]
在第二部分,賴品超進一步逐一回應鄧紹光提出的五點。
第一,問題的關鍵,不是是否基督擁有一個屬人的、有罪的肉身,而是這個有罪的肉身是否耶穌基督的人性的一個必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爲罪不是人性的一個必要部分,所以,可以移除它而不減少基督的人性。在這一意義上,罪身不是基督的人性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基督的復活證明它可有可無,基督是完全的人,擁有一個無罪的肉身。所以,鄧紹光的擔憂,即用《大乘起信論》的「一心開二門」來解釋基督的人性會導引出幻影論,是沒有充分根據的。這是因爲,根據《大乘起信論》,二門(一淨一染)並非現實的實體,分別指靈魂與肉體──純潔的是靈魂,不潔的是肉體。取而代之,《大乘起信論》的人觀在其斷言雖然不潔/有染是一種人類現象,但是真正的人性仍然是純潔的這一點上相當接近巴特的人性觀。[79]
第二,問題的關鍵是,哪一個詞——「罪身」或者「罪性」——更適當。這並沒有假定存在兩個不同或分離的實體——一個是罪身,另一個是罪性。「罪身」更可取,因爲與「罪性」不同,它能夠避免這一聯想:罪是人的本性的一個必要部分。[80]
第三,賴品超贊同艾雲所理解的對聖靈的依賴可以根據空這一佛教教義來重新解釋。然而,出於兩個理由,這種理解仍然是不充分恰當。鑒於艾雲的人觀,對聖靈的依賴僅僅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人的自由意志,它與上帝的形象相關聯。涉及強調基督的兩個本性之間的區別在合一裏得以保留的迦克敦程式,空的概念就其本身而言,並沒有成功地解釋基督的人性與神性之間的區別,因爲兩者都同樣是「空」。而且,用它來解釋人的本性與其他被造物(比如狗)的本性之間的區別會相當困難,因爲兩者都是「空」。因此,賴提出,在試圖以佛教辭彙來解釋迦克敦程式時,除了介紹中觀哲學之外,也值得介紹如來藏的教義。[81]
第四,雖然迦克敦程式的主要焦點在於兩個本性之間的關係,但是不應該忽略它對於人觀的含義。這是因爲迦克敦程式有其救贖神學關切和人觀含義,對此巴特已經相當清楚地加以說明。這些含義有助於更完全地理解迦克敦程式,對佛教與基督教的對話也很重要。[82]
最後,賴品超表明他基本同意鄧紹光所提出的第五點。賴品超澄清,他在之前的論文中所陳述的不是天臺和華嚴是兩個相互排斥的體系,而是兩個佛教宗派所提出的圓教標準的不可共量性。華嚴把終末的實現視為圓教,而天臺把沒有障礙或分離的圓融珍視爲標準。然而,針對個別教義而言,比如巴特的基督論,很有可能可以結合天臺與華嚴各自珍視的特徵。[83]
在鄧紹光最新近的文章〈大乘神學的再思〉[84]中,重申了大乘神學中的基督論這一中心,然而他所詳細討論的神學家是布爾特曼與潘能伯格,而非巴特。討論的焦點似乎從巴特那裏轉開了,但實際上它暗中呼應了賴品超所提出的最後一點。鄧紹光提出,布爾特曼在強調基督的此世性可以與天臺相比較,而潘能伯格相對來說更集中于基督的終末,這種強調更符合華嚴佛學。大乘基督論必須折衷這兩個方面。正如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的,這兩個方面在巴特的基督論中已經結合在一起。
7
总结
上述對巴特的基督論和大乘神學的討論,對於理解巴特的基督論本身,可能並沒有太大幫助。但討論的背後,卻是漢語語境所特有的一個實際關懷——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人性方面的對話,包括基督教與中國佛教的對話。在漢語語境中經常討論的一個神學問題是,基督教強調人性的罪觀是否與(認爲是)儒家的人性本善相一致。上述討論證明,可以通過另一個框架以一種相當意外的方式——中國的大乘佛教——來認識巴特的神學洞見。它可以進一步表明,來自不同文化、社會與神學背景的巴特學者之間的觀點交流,對於巴特學說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
8
注释
作者简介
陈家富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事工主任及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
赖品超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教授课程包括基督教研究、宗教多元主义、宗教哲学等领域。
往期文章
曾劭愷 :巴特與自由神學:回應瞿旭彤教授「比自由神學更自由」一文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巴特研究Barth-Studien
公号邮箱:[email protected]
编辑:Vanci
校订:然而、巴特研究、语石、Shooki、Lea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