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基督教的无神论者中,有不少人认为,相信上帝的信徒有认知方面的问题。“新无神论者”的代表道金斯在他《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一书中说,成年人相信上帝真的存在,就像小孩子相信圣诞老人或独角兽存在一样,是一种“错觉”(delusion)。当然,这样的看法并非道金斯首创,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著名的“老无神论者”对宗教有过类似的批判,比如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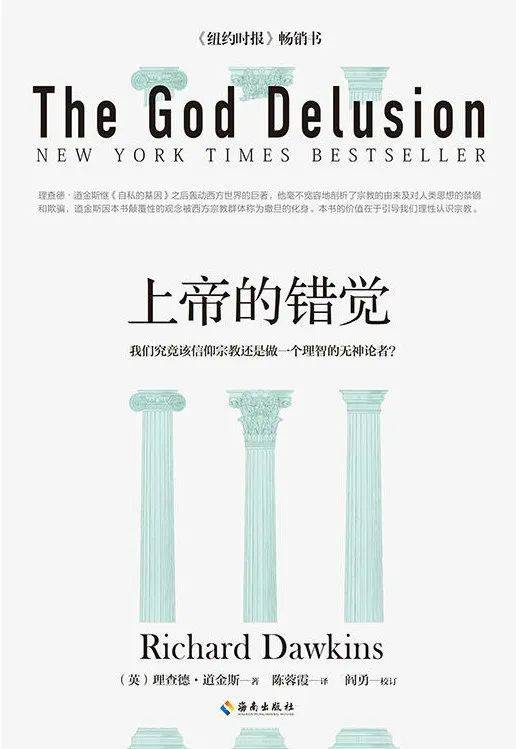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方法,得出相信上帝的宗教信仰是源自“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的结论。弗洛伊德认为,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们对父亲既有爱也有惧怕和敬畏,这种情结可能通过一个父亲的替代物来抒发。在作为人类“儿童期”的原始社会中,动物图腾就是父亲形象的替代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人崇拜的对象逐渐被人格化,最终人格化的上帝取代了图腾的位置,宗教由此产生。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源于人类在儿童期的欲望与无能的宗教,究其本质,是“一种普及的、强迫观念型的神经质病”。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我们可能更加熟悉。他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很多人对这句话的含义其实是有误解的。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人性世界中的人性,是没有灵魂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批判的不是宗教,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中的统治阶级,马克思认为他们是现实苦难和人性异化的根源。马克思表达了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认为,宗教对于社会,就像那个时代被用于止痛的鸦片对于病人或受伤者一样,具有缓解痛苦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是宗教在实用主义意义上的一种功效。
尽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本意可能被人误解,但马克思对宗教的主要看法仍是负面的。他认为,宗教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鸦片虽然可以减轻疼痛,但它给人带来的其实只是一种暂时快乐的幻觉。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人的认知过程失序造成的“对世界的一种变态的意识”——也就是说,相信上帝是一种认知上的病态。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方法,得出相信上帝的宗教信仰是源自“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的结论。弗洛伊德认为,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们对父亲既有爱也有惧怕和敬畏,这种情结可能通过一个父亲的替代物来抒发。在作为人类“儿童期”的原始社会中,动物图腾就是父亲形象的替代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人崇拜的对象逐渐被人格化,最终人格化的上帝取代了图腾的位置,宗教由此产生。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源于人类在儿童期的欲望与无能的宗教,究其本质,是“一种普及的、强迫观念型的神经质病”。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我们可能更加熟悉。他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很多人对这句话的含义其实是有误解的。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没有人性世界中的人性,是没有灵魂处境里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批判的不是宗教,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中的统治阶级,马克思认为他们是现实苦难和人性异化的根源。马克思表达了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他认为,宗教对于社会,就像那个时代被用于止痛的鸦片对于病人或受伤者一样,具有缓解痛苦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是宗教在实用主义意义上的一种功效。
尽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本意可能被人误解,但马克思对宗教的主要看法仍是负面的。他认为,宗教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用来麻痹人民、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鸦片虽然可以减轻疼痛,但它给人带来的其实只是一种暂时快乐的幻觉。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人的认知过程失序造成的“对世界的一种变态的意识”——也就是说,相信上帝是一种认知上的病态。
普兰丁格的反驳
宗教信仰是一种认知上的病态吗?相信上帝是不是一种精神疾病的症状?美国分析哲学家普兰丁格在其著作《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中,针对这个问题,回应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普兰丁格指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把宗教信念视为反理性的认知,是因为他们认为宗教的存在来源于人的认知官能(cognitive faculties)失调而不能产生正确的信念,导致关于上帝的信念变成错误的迷信。
但是把相信上帝视为一种认知失调,甚至精神疾病,在理性上是缺乏根据的。绝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相信上帝的人,都是精神正常的人,他们对世界的很多其他认知都没有问题。他们能够跟他人正常交流,在自己的工作上可能有优秀的表现,能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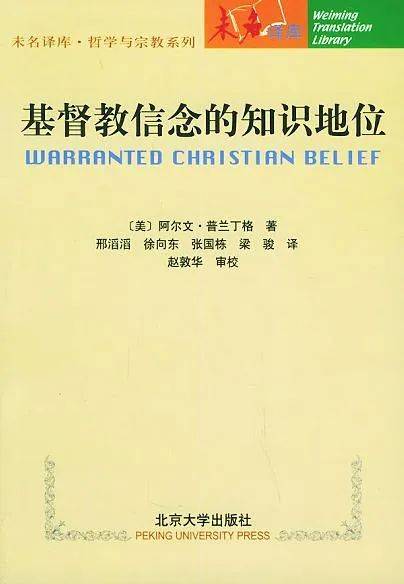 到他人(包括信仰不同者)的尊重。他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是合理的。实际上,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包括基督徒)会反过来认为,否认上帝存在的无神论信仰,才是认知出现问题导致的不合理的信念。
所以,争议的核心是:相信上帝存在或者不相信上帝存在,到底哪一个才是人本来应该有的正常认知?这首先是一个哲学上所谓的“认识论”(epistemology)问题,而认识论正是普兰丁格的哲学研究所专注的领域。
针对现代西方哲学对宗教采取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态度,普兰丁格指出,即使上帝的存在不能在逻辑实证的意义上被证明,对上帝的信仰仍然是理性的,并且是“可以得到保证的(warrant)”。(“保证”是普氏用的一个哲学术语,用来取代“证明”。他认为有“保证”的信念才可能是真知识。)普兰丁格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正当的基本信念”,就像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相信“2+2=4”或者“今天我的早饭是稀饭和包子”一样,无须经由其他更基本的真知识来证明,却是正当而合理的。
普兰丁格发展出了一种“恰当功能”(proper function)的认识论,论证对上帝的信仰可以独立于证据而得到保证。他认为,一个信念能得到保证的必要条件,是赋予人“形成信念与维持信念的能力”的认知器官必须正常地工作,而我们的认知官能,例如感知、记忆和推理,跟我们“被设计的蓝图”及合宜的认知环境相关。只有当这些认知器官恰当地发挥功能,而我们的认知环境也正常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才有保证,我们所信的才可能成为真知识。
普兰丁格用“阿奎那/加尔文模型”(Aquinas/Calvin Model)来论证有神论信仰的合理性。他同意神学家加尔文的观点:因为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有“神圣感知”(sensus divinitatis),上帝借着大自然和人类良知的普遍启示,把“宗教的种子”播种在人心中。这是人能够认知关于上帝的事情的基础。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罪性的干扰,相信上帝的存在本来是人应该有的“自然”的正常认知。然而,因为人悖逆上帝、犯罪堕落,理性受到罪的污染,因此就认识上帝而言,人的认知官能可能失调,丧失恰当发挥功能的能力,导致无神论等错误的信念。普兰丁格也同意加尔文所说,除非人接受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及其见证的基督),除非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新和重生的工作,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对上帝有正确的认知。
到他人(包括信仰不同者)的尊重。他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是合理的。实际上,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包括基督徒)会反过来认为,否认上帝存在的无神论信仰,才是认知出现问题导致的不合理的信念。
所以,争议的核心是:相信上帝存在或者不相信上帝存在,到底哪一个才是人本来应该有的正常认知?这首先是一个哲学上所谓的“认识论”(epistemology)问题,而认识论正是普兰丁格的哲学研究所专注的领域。
针对现代西方哲学对宗教采取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态度,普兰丁格指出,即使上帝的存在不能在逻辑实证的意义上被证明,对上帝的信仰仍然是理性的,并且是“可以得到保证的(warrant)”。(“保证”是普氏用的一个哲学术语,用来取代“证明”。他认为有“保证”的信念才可能是真知识。)普兰丁格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正当的基本信念”,就像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相信“2+2=4”或者“今天我的早饭是稀饭和包子”一样,无须经由其他更基本的真知识来证明,却是正当而合理的。
普兰丁格发展出了一种“恰当功能”(proper function)的认识论,论证对上帝的信仰可以独立于证据而得到保证。他认为,一个信念能得到保证的必要条件,是赋予人“形成信念与维持信念的能力”的认知器官必须正常地工作,而我们的认知官能,例如感知、记忆和推理,跟我们“被设计的蓝图”及合宜的认知环境相关。只有当这些认知器官恰当地发挥功能,而我们的认知环境也正常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才有保证,我们所信的才可能成为真知识。
普兰丁格用“阿奎那/加尔文模型”(Aquinas/Calvin Model)来论证有神论信仰的合理性。他同意神学家加尔文的观点:因为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有“神圣感知”(sensus divinitatis),上帝借着大自然和人类良知的普遍启示,把“宗教的种子”播种在人心中。这是人能够认知关于上帝的事情的基础。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罪性的干扰,相信上帝的存在本来是人应该有的“自然”的正常认知。然而,因为人悖逆上帝、犯罪堕落,理性受到罪的污染,因此就认识上帝而言,人的认知官能可能失调,丧失恰当发挥功能的能力,导致无神论等错误的信念。普兰丁格也同意加尔文所说,除非人接受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及其见证的基督),除非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新和重生的工作,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对上帝有正确的认知。
挑战无神论
普兰丁格不但正面建构他的认识论,而且满有智慧地运用他的这一理论回应无神论者在认识论方面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他挑战无神论的自然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前提,指出无神论信仰无法为人的认知器官发挥恰当功能提供根据:
既然我们只是由(没有引导的)进化拼凑出来的,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很难是完全准确的。自然选择只对适应性行为感兴趣,它不关心信念是否真实……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的:“人是物质的对象,而不是连在身体上的非物质的自我或灵魂或实体。人身上的部件不包含任何非物质的实体。”由此看来,我们相信什么取决于神经生理机制,我们的信念是某种复杂的神经生理结构。这个神经生理无疑将是具有适应性的。但为什么道金斯们(无神论者)认为这样的依赖神经生理机制的信念多半的时候会是真的?他们为什么认为我们的认知官能是可靠的呢?……
从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相信我们的认知官能可靠的看法最多只是一种天真的期望。自然主义者可以合理地确信信念形成背后的神经生理机制具有适应性,但这绝不等于基于这样的神经生理机制而形成的信念就是真的。实际上自然主义者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如果进化是没有引导的,我们的认知官能就不大可能是可靠的。如果进化是没有引导的,我们可能生活在世界之中而能够真的认识关于自己的某些事情、也认识这个世界,但我们也同样可能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面。”
因此无神论信仰在认识论上必然陷入自相矛盾,“自然主义是自毁长城,是违背理性的信仰。”
而相信上帝存在的有神论信仰则没有这个问题:“从有神论的观点来看,我们会预期我们的认知官能是可靠的(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限制条件和例外)。上帝按照他的形像创造了我们,我们因此像上帝,可以形成真的信念,可以获取知识。”
本于圣经真理
故此,如果我们的正确认知是基于认知器官的“恰当功能”,那么相信我们的认知器官是上帝创造、所以有“智慧设计”的有神论,比相信我们的认知器官是从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漫长进化而来的自然主义无神论,更能为“恰当功能”提供保证,也更能为“人是否以及怎样能够认识关于上帝的事”提供更合理的根据。
因为普兰丁格的认知理论汲取了加尔文对人类认知的看法,符合改革宗神学的观点,所以他的理论被称为“改革宗认识论”。实际上,加尔文的观点也不是原创,而是来自圣经。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虽然神是个灵,肉眼不能看见,但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彰显在大自然和人心中,“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另一方面,圣经也指出“不虔不义”的罪人必然会“压制”关于上帝的真理,因此虽然上帝已经向罪人显出他存在的证据,他们仍然“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参《罗马书》1:18-23新译本)。普兰丁格的认识论在这些方面是完全符合圣经的。
普兰丁格一生恪守敬虔的基督教信仰,治学严谨,为人谦和,连很多不认同他的理论的非基督徒哲学家都非常尊重他。而他对逻辑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无神论的哲学基础的批判尖锐犀利,并且富于睿智和幽默。他对无神论者的宗教批判的回应,是基督徒为信仰辩护非常宝贵的参考资源。
基甸(Gideon Ch’eng),旅美成都人。曾任福音杂志主编,现为全职基督工人。音频播客“基甸聊天”和视频直播“甸二哥的龙门阵”主持人。本文原载于《海外校园》第146期,转发略有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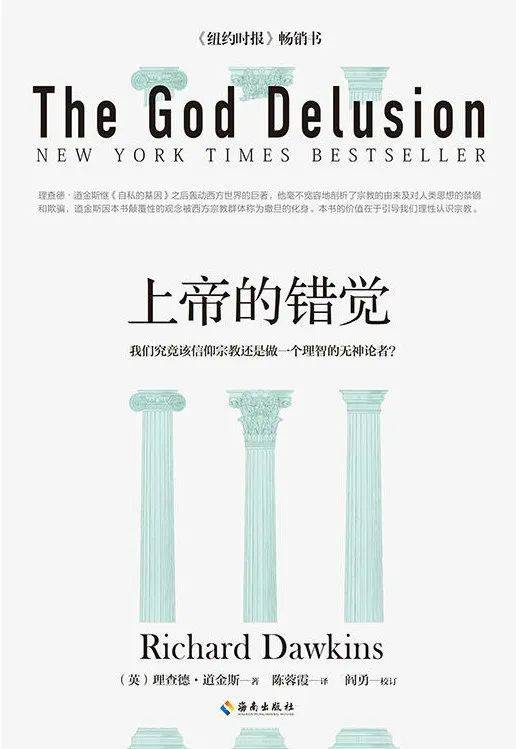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方法,得出相信上帝的宗教信仰是源自“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的结论。弗洛伊德认为,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们对父亲既有爱也有惧怕和敬畏,这种情结可能通过一个父亲的替代物来抒发。在作为人类“儿童期”的原始社会中,动物图腾就是父亲形象的替代物。
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方法,得出相信上帝的宗教信仰是源自“愿望满足”(wish-fulfillment)的结论。弗洛伊德认为,孩童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们对父亲既有爱也有惧怕和敬畏,这种情结可能通过一个父亲的替代物来抒发。在作为人类“儿童期”的原始社会中,动物图腾就是父亲形象的替代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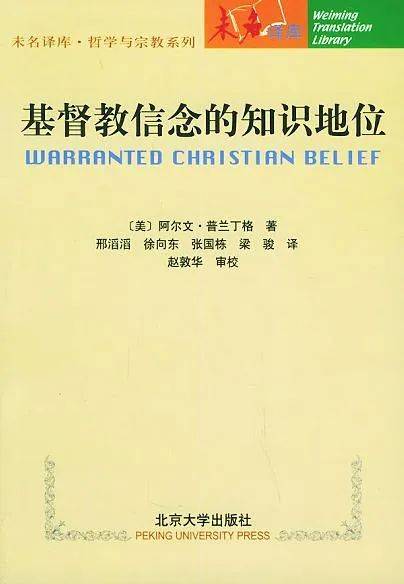 到他人(包括信仰不同者)的尊重。他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是合理的。实际上,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包括基督徒)会反过来认为,否认上帝存在的无神论信仰,才是认知出现问题导致的不合理的信念。
到他人(包括信仰不同者)的尊重。他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是合理的。实际上,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包括基督徒)会反过来认为,否认上帝存在的无神论信仰,才是认知出现问题导致的不合理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