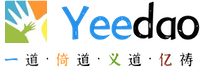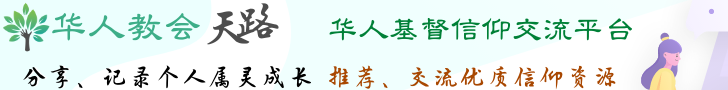记得去年在埃及旅游的时候,常常发现某些贫穷而普通的埃及人有一种喜悦、天真和坚毅的神情。直觉中我将这种美好归咎于他们虔诚的信仰。信仰维系着生命中某些领域的神秘和颤栗,那里,神圣、美丽、天真晶莹剔透地彼此闪耀中现身;在那里,人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和信赖才能趋近,犹如《路加福音》中所言:“父啊……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里,经济理性、权衡和明智、甚至思辨理性都无法把捉其真相,虽然思辨理性并不是无法触及其边界或述说其所见的。
然而,我并非要为信仰唱颂歌,而是要为自己的缺信哀叹。很羡慕那些真正虔信上主的人,他们敬畏,他们纯真,他们追随主的脚踪前行,他们背对世界,他们稀少。然而我虽然努力地捧起《圣经》,却只是聊以自慰,其处境犹如但丁《神曲》中落在地狱门外那些叹息和哭泣的灵魂,那些被天堂驱逐而地狱也不收留的灵魂:“这是一群胸无大志的懦弱之徒,他们得不到上帝以及上帝的敌人的欢心。”
在我与纯真的信之间有一道巨大的裂痕。我并非像奥古斯丁那样认为生活抉择是要么天堂要么地狱那么泾渭分明,而是倾向于阿奎那那更和缓的观点,恩典成全自然:在深秋校园那深红的遍地落叶的凄美中,在小孩子笑盈盈地扑进爸爸的怀抱那舔犊情深的时刻,在那些满怀朝气的学子们追逐知性和绽放青春美丽的流光溢彩中,在眷怀共同体流金岁月的自豪时刻,在维系着每一个个体的安全、平等、自由和尊严的得体的政治社会秩序中,都看得见神恩的祝福和引领,无限甚至托住此世并以其无限的境域惊醒可能的停滞。由此,纯真的信可以基于美好的此世生活,虽然美好的生活也可能足以让脆弱的我们沉迷其中而不再与无限相关,就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Dasein)在世的基本样式就是沉溺其中。
然而,在此世中我没有与幸福相遇,转向上主时我也失落了或未曾遭遇上主和祂的爱。像德尔图良一样选择守候在耶路撒冷而不是雅典,像奥利金一样为天国而燃烧自己,像亚他那修一样在灵魂和自然中认识上主,像亚西西的方济各一样吟唱自然,像小德兰一样被爱吞没。他们都被上主所把握,上主点亮了他们的灵魂,他们深邃的目光定睛在上主身上,再也不曾离开。
羡慕这些有福的灵魂,却也知道自己不曾如此全心全意地转向上主。这灵魂是软弱的、是迟钝的、是平庸的、是不坚贞的、是模棱两可的。我之渴慕上主,并不比渴慕世界更多更深。相信那些为上主所震慑的灵魂是持守着神秘的,然而我却眼见自己赤露奔命于此世的繁华诱惑——别道我孤灯默守,只一瞥就揭示了内心的沉迷。就像两手空空的沦丧的乞丐,无论是上主的赐福还是魔鬼的诱惑,我都会接受。知道永恒,却随时准备让自己迷失在温柔之乡,只是如今却在地狱门外哭泣。这就是我的忧伤,但丁首先谴责的那些人的悲哀:就算未犯下重重大罪,却也一生未曾清白,不过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在漫漫一生中卷入了种种不洁和错失,玷污了灵魂,最后像《理想国》卷十中的护海之神格劳克斯的躯干一样难以辨认:“由于海浪的冲刷,一部分被折断,一部分则由于冲击磨损而完全毁损了,又添上了新的部分——牡蛎、海带、岩石等,以至于他看起来竟毋宁是一头野兽而不像他的天性所是的他。”
然而,这种忧伤并非无限的,因为我只是一个有限者。或许终有一日,上主亲自让我得以洁净,引领我前行。即便并非如此,有限者也能够像《申辩篇》最后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无论死亡是虚无还是迁居另一个世界,都是好的,前者中,永恒不过香甜的无梦的一夜,后者中则能与那些因正直而为神的人共处——甚至罪孽者也因落入上主之手而安心。
江绪林
2013年11月30日星期六
(此文最初发表于江绪林老师的豆瓣日记,后经编辑收录在《生命的厚度》一书中。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江老师发布在豆瓣上的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