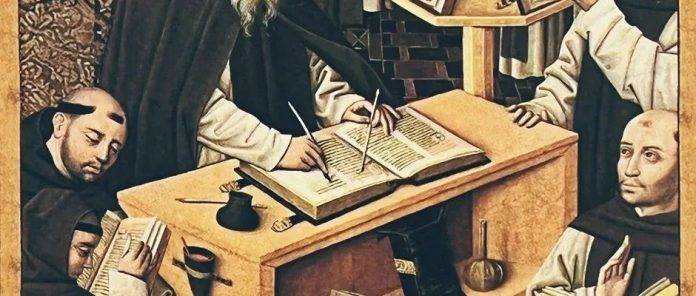最近,我的一个学生问我教神学多久了。“十年,”我说。但当我回到办公桌前时,一个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十年后,我给学生留下了什么?
在我自以为是的想象里,我认为自己就是那个赋予学生满腹知识的人。但事实上,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的学生进入现代事工波涛汹涌的大海之前,把教会历史上一众先贤经过时间检验的智慧交给他们。
我教书的时间越长,就越能认同 C.S.路易斯在《人之废》(The Abolition of Man)中的训诫:“现代教育者的任务不是要砍伐丛林,而是要灌溉沙漠。”然而,在神学院教育领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沙漠,尤其是在整合大量基督教的伟大传统方面。
多年前,作为新教神学院的一名神学博士生,我收到了一份必读清单。在128本书中,只有3本 (!) 是出自现代之前的作者(写于1世纪至15世纪)。
甚至当我因学位研究需要而跨入历史时,研讨会也是从教父时代直接跳到了宗教改革时代,又再直接进入美国历史。但因为教会历史有一半的时间——是的,一半——发生在中世纪,我的这个教育缺口就像一个大峡谷。所以我请求学校让我做中世纪神学和历史的独立研究。
那么,神学教育到了今天有什么改变吗?
克里斯托弗·克利夫兰(Christopher Cleveland)记录了福音派神学院如何试图用保守的神学家取代自由派,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忽视或刻意回避——“产生了一整代对教父时期、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正统思想中经典神学范畴不熟悉的福音派学者”。
作为新教徒,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受到教导:基督教的一切都始于辉煌的初代教会,但随后教会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庆幸的是,改教家们重新点亮了灯,建立了自使徒时代以来就已失传的真教会。
我们错误地认为改教家们追求的是完全且彻底地与过去决裂——一场开创了新教会的反叛——而不是寻求去更新那唯一的、神圣的、大公的、使徒性的教会。
这种心态的实际影响很严重:今天大多数新教徒不知道整整一千年间教会发生过什么。然而他们对一件事有信心:现代之前的时代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我们花时间去了解,它们只会腐蚀基督教。
这是许多日常去教会的新教信徒的心态,其最终来源是讲坛上的讲道。而且由于大多数牧师都在神学院接受过培训,问题的根源往往始于新教学术机构的态度。
福音派圈子之外的人经常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们之中许多人就读于世俗机构,在那里,这种知识的断层是无法想象的。但愿我可以说这一切只是管理上的疏忽,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所有的观念都是有后果的。
那么,我们如何改变现状呢?答案与谦卑有关。
我们都知道C.S.路易斯的名著《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该书强调了他对正统——即古典基督教——的坚定委身是不容让步的。
然而许多人忘记了,在这部经典的护教学作品中,路易斯用了整整两章来重述《尼西亚信经》及其关于圣子永恒受生的复杂教义。他还为基督教历史上的一部伟大著作——东方教父亚他那修的《论道成肉身》——写了一篇序言。
路易斯建议——不,甚至是恳求——现代人要阅读更多的古书。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现代之前的作家没有缺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盲点。但他们的盲点并不一定跟我们的盲点一样。
“我们谁都无法完全摆脱这种盲目性,但如果我们只阅读现代书籍,我们肯定会增大盲点,并削弱我们对它的警惕,”路易斯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几个世纪前干净的海风吹过我们的脑海,而这只有通过阅读古书才能做到。”
例如,路易斯经常深思以上帝为中心的中世纪神学观,他认为这是对当代盛行的怀疑论现代主义祛魅世界的解药。正如杰森·巴克斯特(Jason Baxter)在他最近出版的《路易斯的中世纪心灵》(The Medieval Mind of C. S. Lewis)中指出的那样,路易斯认为,“他的责任不是挽救这个或那个古代作家,而是挽救漫长中世纪的普遍智慧,然后将其翻译成大白话讲给他的时代听。”
在现代主义祛魅世界的威胁下,路易斯对他那个时代“贵今贱古”(chronological snobbery)的风气没有耐心。由于担心这样的怀疑主义会破坏基督教正统本身,路易斯认为这种自命不凡的态度不仅无知而且不敬虔。
而我们也应该如此。
对于自认什么都懂的人而言,怀念传统并不是值得吹嘘的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需要带着谦卑之心愿意停止说话——无论我们有多沉迷于自己的声音,转而聆听。
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在《回到正统》(Orthodoxy)里说:“传统拒绝屈服于那些只是碰巧路过之人微小而傲慢的寡头统治”。切斯特顿和路易斯都呼吁现代人谦卑自己,聆听 “死者的民主”。否则,教会只会落入各种新、旧的异端。
许多我们信仰的先驱也都有类似的心态——包括宗教改革的领袖们。
当时,罗马教廷指责宗教改革领袖标新立异,因此是异端——并将他们与当时的激进派(重洗派)混为一谈。这些激进分子认为,从使徒时代直到激进分子到来前,教会在黑暗中迷失了。他们声称只相信圣经,并唾弃古代思想家。激进分子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教会。
宗教改革领袖对激进分子的傲慢感到愤怒,而对自己被误认为是激进派而感到沮丧。与激进派不同的是,宗教改革领袖不是一心只想分裂教会的叛逆者或革命者——那些本质上的分裂主义者。打从一开始,宗教改革领袖的目的就是更新教会,他们认为罗马教廷不能垄断教会的大公性。
正如我在《作为更新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as Renewal)中解释的那样,宗教改革领袖不断地诉诸圣经,但他们通过援引过去的神学家来证明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正确的。圣经是他们最终的上诉法庭,但不是他们唯一的权威;他们相信教会需要对信经负责。这些信经保守了教会忠于圣经本身的见证。
虽然他们在关于救恩和圣礼等教义上对罗马教廷表达严厉的批评,但他们也对罗马教廷许多其他的教义表示认同。若非如此,他们的正统观念也会令人质疑,只会坐实罗马教廷对他们的指控。
研究宗教改革的专家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宗教改革家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义。”
虽然救恩论和教会论等教义需要认真纠正。然而,作为基督教核心的教义 “上帝、三位一体、创造、护理、预定论和末世论在被宪制改教家接手后,几乎没有改变,” 穆勒说。几乎没有改变——真正的新教教义会站起来吗?
我们的新教父辈不仅继续撷取初代教父的神学,而且他们受惠于包括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内的中世纪经院学者,远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多。
在教会历史上,很少有神学家能像阿奎那那样,将关于上帝和基督的正统且符合圣经教导的教义长远延续下去。
正因如此,我经常在我任教的福音派神学院的三位一体论课程中介绍阿奎那。每年,学生们都兴奋地向我报告他们略带讽刺的发现:他们发现阿奎那在三一论上比某些当代福音派信徒更正统。
但有一天下午我走进教室,发现讲台上有一串巨大的玫瑰经念珠、十字架和各类天主教的东西——上面写着“给巴雷特教授”的字条。所要传达的信息很明显:一位推荐阅读阿奎那的教授必定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如果不是因为替这个匿名的学生感到难过,我会笑出来的。作为新教徒,我们是否如此缺乏安全感,以至于我们无法受益于教会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尤其是在像三一论这样重要的教义上——仅仅因为我们可能在救恩论和教会论上不同意他的观点?
甚至我们的宗教改革先辈,他们在新教信仰中也有足够的信心在很多领域批判性地运用阿奎那的神学——从释经学到上帝的属性,从三一论到伦理学和末世论。改革宗神学家不仅运用阿奎那反驳罗马天主教徒,而且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也证实,许多宗教改革的先辈甚至比他们的对手更加是托马斯主义(Thomistic)的跟从者。
那些避开阿奎那的现代福音派神学家通常会借鉴清教徒思想家约翰·欧文 (John Owen)等新教经院学者。然而,新教经院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神学之所以忠实于圣经正统,正是因为他们是阿奎那的学生。
他们之间的关联是如此无法反驳,以至于福音派出版社十架之路(Crossway)将要出版《给新教徒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 for Protestants)多卷本套书——该书由一群新教作者联合撰写。
归根究底,我们并不是要把阿奎那或任何其他思想家奉为神圣。相反,当阿奎那揭示他那跨越时代的卓越思想时,我们将批判性地、但谦卑地聆听,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在这逐渐祛魅的世界中重新找到上帝永恒的良善、真理和美丽。
福音派信徒会带着所有现代文化的倾向,经常喜欢充当法官,将基督教历史上的“好人”与“坏人”区分开来——只为了尊崇前者而消灭后者。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会无情的偶像化和抹黑历史人物。
这种心态不仅助长了分裂的宗派主义——“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其他人都不是真正的教会”——并且缺乏同理心。我们无法理解过去的人、运动、机构和整个时代的复杂性,更不用说从中学习了。在这种论断行为背后隐藏着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政治议程和派系思想。
俗话说,人们总是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这种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掩饰在敌意的言辞中,转化到未来的教会领袖的课堂上,再进一步影响平信徒。
我最近与一个对当今福音派心灰意冷的年轻人进行了交谈——因为有一些福音派信徒转变为基要主义者,对所有现代之前的事漠不关心或心存怀疑——他想知道福音派教会是否还有任何真正的历史根源可以提供。
如果今天的福音派领袖不能追随他们新教先辈的带领,持守教会的大公性(catholic),下一代就会去寻找一个能如此做到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