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九讲 颜李学派:实践理性利弊
这一讲我们讲“颜李学派”。颜李学派,是指颜元与他的弟子李塨创立的实践主义学派,这个学派的特色在高扬实践理性和实用理性。
颜元(公元1635年-1704年)是个纯民间的思想家,一生没做过官。他是河北博野县平民之子,父亲是蠡县朱姓人家的养子,所以他小时候姓朱。他三岁那年,清兵入关,父亲被掳到辽东,母亲也因此改嫁。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的生世,于是改回自己原来的姓,并决定出关寻父。但当时正逢三藩之乱,蒙古响应三藩,辽东实行戒严,使他无法成行。直到五十一岁,他才再度出关,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打听到父亲下落。原来他父亲早就死了,于是他把父亲的遗骨背回了故乡安葬。他一生主要在家乡度过,也曾去过河北南部及河南,时间都很短。在河南,他受邀办书院讲学,书院被洪水淹了,他就又回到老家。他一生与同辈学者、名士交往也很少,谈不上相互之间有什么深入地思想交流。
颜元最重要、最有名的学生是李塨(公元1659年-1733年)。颜元不喜欢交际,李塨则广交天下名士。当时学者,几乎都是通过李塨而知道颜元的,有人甚至通过李塨拜了颜元为师。李塨名气很大,又喜交游,但却与权臣保持了一定距离。“理学名臣”李光地当直隶巡抚的时候,招他去见面,他拒绝了。“西北王”年羹尧两次礼聘他,他也不去。他继承了颜元的思想,但具体观点与老师并不完全相同。李塨曾问学于名儒毛奇龄,毛希望李抛弃颜元的思想,成为他自己的忠实弟子,李不肯,毛奇龄居然写文章大肆攻击颜元。总之,没有李塨的宣讲、发展,中国思想史上未必会出现颜元这个人,更不会出现“颜李学派”。
要理解颜李学派,首先要了解颜元的思想转变历史。颜元二十岁前后,很喜欢阳明心学,其后兴趣又转到程朱理学,信之弥坚。但后来,他又认为程朱大错特错,必须予以大力批评。他说过他最后这次思想转变的机缘:“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他还用文字给孔子、程颐画了两张像,以说明“孔孟、程朱,判然两途”:“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觽、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磐算器马策,及礼衣冠之属。一堂坐程子,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返观静坐,或执书伊吾,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研梨枣。此二堂同否?”也就是说,颜元反宋明理学家,尤其反程朱,主要是受当时读书人的现状刺激。
那么,如何把握颜李学派的思想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看他们反对什么——程朱;二是看他们主张什么——实践;三是看他们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人性论。
首先来看颜李反程朱。事实上,此前虽然有人反程朱,但作系统性的驳论,几乎认为程朱的所有主张都一无是处的,颜元是第一人。因此可以说,颜元对程朱的反对是空前的,这也意味着他对自宋以来中国思想史的反对是空前的,他有一笔扫清这一段思想史的大抱负。下面我们来看他反对程朱的几个方面:
一,他反对程朱式读书、著书、注书,根本不认为书本上有所谓学问。他说:“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而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又说:“书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读书者之祸,读书者自受其祸,此局非得大圣贤大豪杰不能破。”他认为,后儒之所以死读书,一个重要原因是误读了孔子“博学于文”的教诲。“儒道之亡,亡在误认一‘文’字。试观帝尧‘焕乎文章’,固非大家贴括,抑岂四书五经乎?周公监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谓‘在兹’,颜子所谓‘博我’者,是何物事?后儒全然误了。”“汉宋儒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然则虞夏以前大圣贤皆鄙陋无学矣。”“后儒以文墨为文,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讲、博著,不又天渊之分耶?”至于著书,不过是“空言相续,纸上加纸”。
颜元反对人读书,理由是,读书让人愚昧,让人虚弱,浪费时间,办不了正事。颜元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文家把许多精神费在文墨上,诚可惜矣。……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此岂男子态?”颜元甚至说,读书犹如服用剧毒砒霜:“仆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气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余岁,终不能入尧舜周孔之道。……故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李塨也赞成颜元的观点:“读阅久则喜静恶烦,而心板滞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实,曰‘白面书生’,曰‘书生无用’,曰‘林间咳嗽病猕猴’。世人犹谓诵读可以养身心,误哉!……颜先生所谓读书人率习如妇人女子,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也。”
二,他反对程朱式讲学。颜元说:“近世圣道之亡,多因心内惺觉、口中讲说、纸上议论三者之间见道,而身世乃不见道。学堂辄称书院,或曰讲堂,皆倚《论语》‘学之不讲’一句为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门为学而讲,后人以讲为学,千里矣。”为什么不能讲学呢?因为“道不可以言传也,言传者有先于言者也”。宋儒讲学,重点在性命天理,颜元却认为,这些东西太虚,根本讲不清:“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在颜元看来,这是因为孔子认为,普通人根本不需要知道天道,所以孔子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三,他反对程朱式静、敬为主的修身工夫。颜元说:“终日危坐,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此真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尝闻也。”“你(朱熹)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十二个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颜元认为,宋儒之所以主张静坐修心,实在是因为受到了佛教的毒害,以为“洞照万象”就是最高境界,这是大错特错。在他看来,这个境界不难达到,但问题是,即便达到也毫无作用。“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镜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为腐朽之枯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沟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而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工夫,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颜元为什么反对主静?一方面是因为无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此以往,对身体、精神都有害。
颜元并不反对“敬”,但他反对程朱以静坐集中精神的方式居敬。他说:“(《论语》)曰‘执事敬’,曰‘敬事而信’,曰‘敬其事’,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则是儒其名而释其实,去道远矣。”李塨也认为,“圣门不空言敬”,不能离事而言敬。
四,他反对程朱的天道、天理观。程朱所谓道,源自天,天与道是一回事。程朱所谓理,分“天理”、“百理”,前者就是天道,后者是万物之所以运行发展的具体规律,也即事理。虽然如此,宋儒最看重的还是天道、天理,因为它们是最高存在。颜李则从字词训诂的角度出发,解构了程朱的“道”、“理”。在颜李看来,“道”并不虚玄,不过是人走的“路”而已。李塨说:“道者,人伦庶物而已矣。……伦物实事也,道,虚名也。异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独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谓之道哉?”在他们看来,根本无所谓先验的天道,他们只在乎人道,人道就是天道。宋明儒学又称“理学”,但颜元说,“理”字的原意是“木中纹理”,引申出来不过指“条理”而已,而不是高悬的天理。李塨说:“后儒改圣门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气为谈柄,而究无了义。……不知圣经无在伦常之外而别有一物曰道曰理者。”他还说:“事有条理,理即在事中。《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颜李对“道”、“理”如此定义,显然是拉低了“道”、“理”,所以他们眼里的穷理当然也就与程朱不同。朱熹要穷尽世间一切道理,颜元却说:“圣人亦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为愿,能乎?”颜元眼里的穷理是什么呢?“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谓穷理。”朱熹说,明理就能处事。颜元却说,明理而不能处事的人多得很,因为“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李塨说,像程朱那样穷理,结果只能是让人养成自以为是的武断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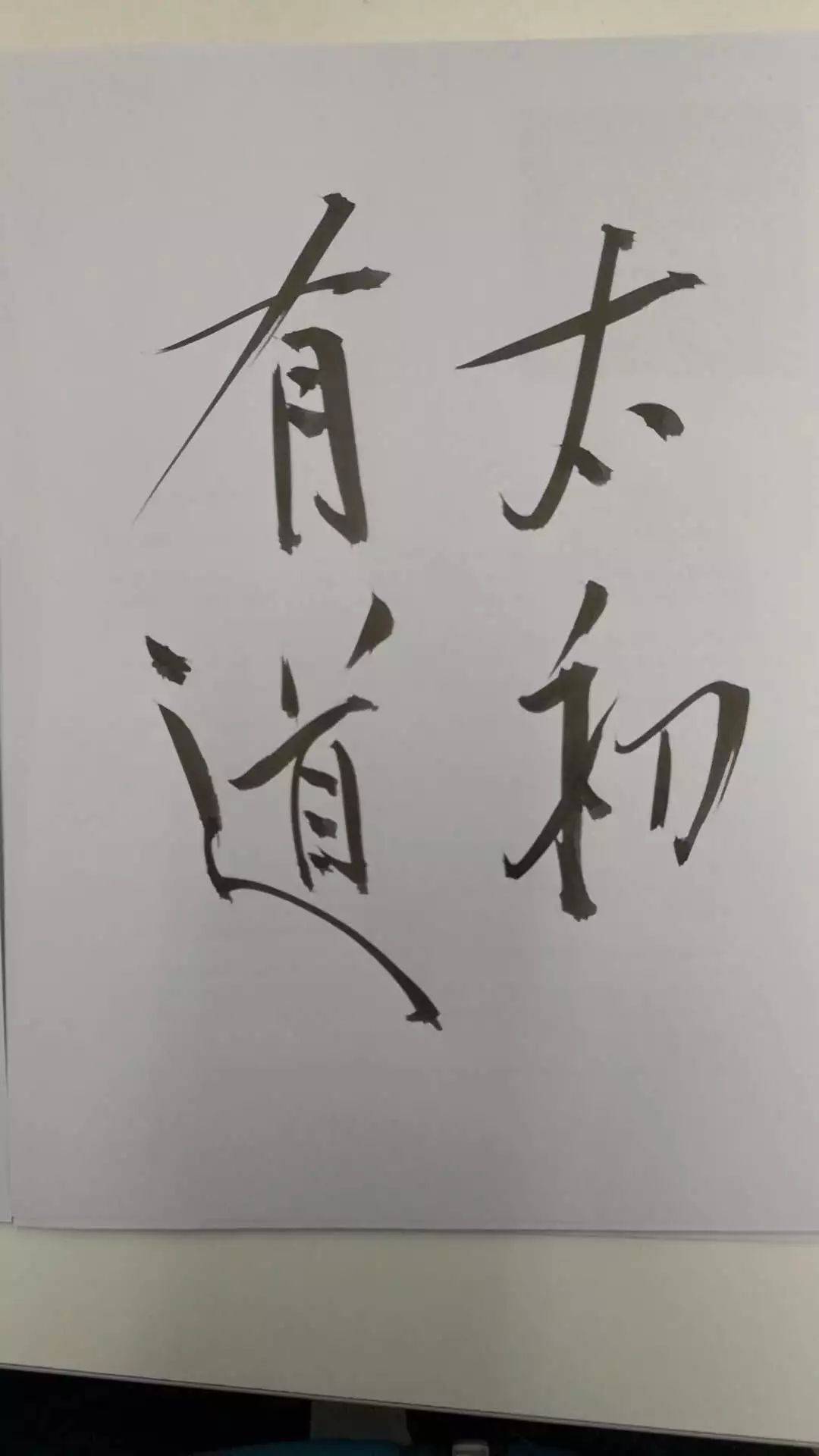
将颜李学派对程朱的批判说到此处,颜李的正面主张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或者说,他们的正面主张,在批判程朱时已经点到了。一言以蔽之,颜李学派的正面主张,就是强调实践。颜李对力行的强调所在多有,这里仅引三处以证明之。颜元说:“圣人只要人习行,不要人解惺。天下人尽习行,全不解惺,是道之明于天下也。天下人尽解惺,全不习行,是道之晦于天下也。”又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周行芜榛矣。”又说:“以此知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
下面我从颜李的知识论、人生观、实践内容、实践方向、实践目的几个方面来考察一下他们的实践主义。
颜李的知识论可以概括为“实践出真知”。让我们来看颜元如何解释宋明儒非常重视的“格物”。颜元所谓“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所以“格物”就是亲手接触事物。“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他打比方说,要知道什么是音乐,读乐谱没有,只在脑子里想也没用,必须拿起乐器吹拉弹唱一番,才是正道。这个道理当然很浅显,谁人都能理解。王阳明不是提倡“知行合一”吗?颜李与阳明又有何不同呢?简单来说,阳明还是更重视知,知是出发点,真知必行;但颜李认为,没有先在的知,只有在行(实践)中才能获得真知;所以我说,颜李的知识论可以概括为“实践出真知”。
颜李的人生观与程朱针锋相对,程朱主静,颜李“主动”。颜元说:“常动则筋骨悚,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肿’。宋元来儒者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颜元最喜欢说:“提醒身心,一齐振起。”不仅每个人要动,整个天下都应该动。“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考其前圣而不缪,俟后圣而不惑矣。”
那么,颜李的实践内容是什么呢?颜元说:“故古之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学教以格致诚正之功,修齐治平之务,民舍是无以学,师舍是无以教,君相舍是无以治也。……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向,则人材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他主张“浮文是戒,实行是崇”,所以认为“外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外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他所强调的“实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活中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二是个人修养上的“格致诚正之功”;三是政治上的“修齐治平之务”。但这三个方面,他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修齐治平之务”。他批评程朱教学失掉了尧舜以来的“成法”,而他所在乎的“成法”,也是与政治有关的古法:“何不观精一之旨惟尧禹得闻,天下所可见者,命九官、十二牧所为而已。阴阳秘旨,文、周寄之于《易》,天下所可见者,王政、制礼、作乐而已。一贯之道,惟曾、赐得闻,及门与天下所可见者,诗、书、六艺而已。乌得以天道性命常举诸口而人人语之哉! ”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颜元的实践方向是复古。儒家普遍以复古为思想底色,但大多数儒家,虽然提倡复古,其目的却是通过复古来开新。他们所谓的复古,究其实,不过是遵循古代经书的精神,而非完全把经书当教条照搬执行。颜元则不然,他自称“思古人”,对西周封建、井田等制度,无不主张重新恢复,他甚至主张宫刑。他恢复井田制的理由是:“岂不知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王道之顺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他主张宫刑的理由是:“吾所谓复古刑者,第以宫壶之不可无妇寺,势也,即理也。”
就此而言,他的学生李塨的态度与他有着很大的不同。李塨对颜元的思想并非完全墨守,就连他都不认可老师的封建井田制设想。在颜元的《存治编》的后记里,李塨就写道:“井田则开创后,土旷人稀之地,招流区画为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业时,行之难。意可井者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李塨还说,他并非刻意要与老师唱反调,老师生前,他们已经对此商榷数年,只是直到老师去世,他们的意见都没有合一,实在是因为他既爱老师,更爱真理,所以在老师死后,他不得不再次提出来。
对颜李的思想述评至此,其实不用说颜李实践主义的目的,大家也能看出来,那就是“功利”二字。李塨说:“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语具《春秋繁露》,本自可通。班史误易‘急’为‘计’。宋儒遂酷遵此一语为学术,以为‘事求可,功求成’,则取必于智谋之末,而非天理之正。后学迂弱无能,皆此语误之也。……事不求可,将任其不可乎?功不求成,将任其不成乎?”颜元更是直接把董仲舒这句话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了。他还说“《尚书》明以利用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易》之言利更多”。他们为什么这么在乎功利?因为在他们看来,宋儒不重视功利正是宋代积弱以致灭亡的原因。颜元说:“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才,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乃如此乎?”又说:“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尹和靖《祭程伊川文》‘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还说:“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此风不变,乾坤无宁日矣!”由此可见其沉痛至极。
颜李的这套学说如果要成立,需要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这就不能不谈到他们的理气论。前面我曾讲过,程朱认为,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来自天道天理,纯善无恶,恶是从后者而生,所以修养的实质是改变气质。颜元根本反对此论,他反问道:“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统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余谓更不必分何者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更何况,“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也。今乃以本来之气质而恶之,其势不并本来之性而恶之不已也。”在颜元看来,恶并不从气质之性生出,而来自于外部习染,而且只要“尽吾气质之能,则圣贤矣”。每个人的性格都有所偏,但“偏胜者可以为偏至之圣贤。……宋儒乃以偏为恶,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气禀偏而即命之曰恶,是指刀而坐以杀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杀贼乎!”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迁善避恶呢?颜元的主张很简单,那就是,因材施教,不必去改变什么气质,但可以改变人的行为习惯。他说:“大约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矣。其误世岂浅哉!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颜李学派的是非曲直?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颜李言说的处境。那就是,当时读书人的确有过于追求虚玄之理而不务实的大毛病,更何况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确实也发展到压抑人性的地步了,颜李的言说,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颜元就说:“宋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辟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世之尧舜周孔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州决杖,况敢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诣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纳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大声呐喊呢?因为他们想要转变世俗风气。颜元说:“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他给李塨的遗言是:“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抱着转移世风的目的,以先知自命的颜元敢于做一个孤独的呐喊者。他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更重要的是,他洞穿了世风如果不转向务实的结果,那就是后人会全面、彻底打倒中国文化。他说:“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考诸中国文化在晚清、五四及后来的命运,我们不能不承认,颜元确实是先知,不幸的是,中国事实上走上了“灭文”之路。悲夫!从上述意义看,颜李学派可谓居功至伟。遗憾的是,颜李学派在思想史上不过是一朵即开即谢的昙花,开过以后,很快就凋谢了。到李塨晚年,乾嘉学派已经开始走上思想史的舞台了。
但我们是把颜李当思想家来评论的,而思想家不能就时代言时代,他们的理论必须超越时代,具有普适价值,这就要求他们的理论“致广大而尽精微”。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颜李学派的实践主义存在很大问题,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主张处处都存在问题。我们先来看他们的分论点的问题。
比如,颜李反对读书、注书、著书,堪称是清初版本的读书无用论,但人类的智慧是积淀起来的,书籍是这种积淀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不是说舍弃书籍就没有学问,但毕竟很多学问是载之于书籍的,完全舍弃书籍,难道不是自愚之道吗?颜李将读书与做事对立起来,认为读书越多,越不会做事,读书与做事在逻辑上矛盾吗?在事实上矛盾吗?
比如,颜李反对讲学,但讲学不正是人类智慧传承的重要渠道吗?颜李认为性命之道讲不清,因此根本不用讲,但人活着,就必然有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也即是,人必须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我为什么能成为道德的人?进一步的问题是:怎样的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只讲实用、实践,回避根本问题,试问实用、实践的目的何在?只是功利吗?功利为什么是目的?人能满足于功利,人只是逐利动物吗?
比如,颜李反对程朱式静、敬,但程朱是让人枯坐不动吗?静、敬在程朱那里难道不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吗?他们虽然强调内圣,但反对过外王吗?老实说,颜李关于“镜花水月”的批评,对佛教则可,对宋明理学则不可,因为凡是儒家,认识到那个最高存在的本体以后,并非仅止于此,终归都要追求人文化成。这一点,我在讲程朱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了。宋明理学固然受了佛教影响,但也仅仅是影响而已,甚至可以说理学只是借鉴了佛教的某些优点,而不是与佛教等同,颜李显然没有看到二者的巨大差异,就胡乱将两教拉来一起批评,显然是不公允的。
比如,颜李拉低天道、天理,不能理解天地未有之前已有道存在,所以认为人道就是天道,则更显浅薄了。我在此前多次论述过天道的重要性,归结为一句话,如果没有天为宇宙万物提供恒定的、绝对的价值,宇宙万物则根本不可能有所谓价值可言,人心也不可能真正安定。宋儒的天道观虽然驳杂不纯,但他们毕竟认识到了有一个天对人类的重要性,颜李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由此带来的问题堪称巨大。这一点,我论到颜李的正面主张时再分别说说。
比如,颜李强调实践、实用,这本没有错,但认为真知只源于实践,则大错特错了。人的知识来源非常复杂,岂只实践一条路径?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众多哲学家论证过知识来源问题,兹不详论,下面我会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比如,颜李“主动”,其实,动静相宜才是正理,单纯主静当然会导致呆滞,单纯“主动”难道就不会导致盲动吗?
比如关于实践方向,也就是复古。这里的问题更大,就连李塨都部分地看到了问题所在。颜元对此毫无所知,以为一味复古,一味照搬古人教条就可实现王道,可谓刻舟求剑、可笑至极。以他所主张的“六艺”中的“射”而言,到明末可谓毫无作用,完全过时了。要知道,明末已逐渐进入热兵器时代,明清两军征战已采用红衣大炮了。
再比如他的哲学基础更是荒谬,他主张气质不必改变,可以改变的是习惯。问题在于,连天道都不存在,人连天道都不敬畏,为什么有动力去改变习惯呢?难道仅仅可以靠功利?天下有靠功利建立道德秩序的共同体吗?
说到底,颜元的实践主义本不是什么新鲜思想。我在前面多次讲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本就以实用理性和常识理性为预设和底色,它们合力阻碍了中国思想传统实现进一步的超越突破。实践不过是人的观念的外化,观念是引领实践的决定性力量。学术研究必须独立、自由,否则无法生出引领社会进步的新观念。颜李对实用、实践的过分强调,绝对杜绝研究“虚理”,在实践中就必然导致反智主义。有人因为颜元提倡实用、实践,就以为他的思想彰显了所谓科学精神,其实他的思想不仅不会导致科学精神的发扬,反倒会阻碍科学精神的发生。道理也很简单,以为倡导复古,以为上古已经尽善尽美,谁还会深入去探究自然的内在原理呢?古今中外,有任何科学家会拘泥于上古“成法”吗?
总之,颜元强调复古、实用,但他不知道复古则根本无法实用。他的思想一旦落到现实生活中,必然走向反面:因为无法落地,“实”就会变成“虚”,“用”就会变成“无用”。李泽厚先生认为,颜元继承的其实不是孔孟思想,而是墨子思想,颜元和墨子的思想都体现了小生产者思维的浅薄与狭隘。当然,这与颜元是否读过《墨子》一书无关,因为墨子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维,其实一直潜伏在中国人思想意识的深层。
以上,只是从一般层面评论颜李学派的得失,下面我想从认识论层面来衡断颜李的缺陷。这就需要引入西方哲学视角了。
一般来说,笛卡尔把西方哲学带进了现代,也就是认识论时代。笛卡尔被认为是唯理主义代表人物,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他的墓志铭上也刻着:“笛卡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与唯理主义相对的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洛克与休谟。洛克说:“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我们可以假定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标记,没有一切观念,那么它如何会又有了那些观念呢?……我可以一句话答复说,他们都是从经验来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唯理主义推崇理性思辨,但休谟说:“我就餐,我玩双六,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三四个钟头的娱乐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冷酷、牵强、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再继续进行这类思辨了。”他还说:“一切从经验而来的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他还认为,道德理论属于实践科学而不是思辨科学,思辨科学推崇理性,讲究真伪,而实践科学则注重行动。休谟将经验主义原则贯彻到底,甚至认为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必然性,它只是人的主观联想,所以要回到常识。
大家发现了没有,颜李二人说的很多话与洛克、休谟极为相似,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颜李是经验主义思想家。不过我必须指出的是,颜李只是半个经验主义思想家,因为如果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则不会给人们认识经验设定任何限制,但颜李的经验主义则指向了复古方向。不过,就算颜李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又如何呢?
这就要回到康德的视角了。众所周知,康德的伟大在于,他认识到了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都存在巨大问题,极端的唯理主义会导致独断论,极端的经验主义则会导致怀疑论,也就是一切标准都将失去。他既反对独断论,又反对怀疑论。他的伟大在于,一方面给理性划界,认为人在理性不及的领域,也就是超验的信仰和道德领域应该保持沉默,一方面又论证了科学理性在自然领域的确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开始于”感觉经验,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源自于”感觉经验。也就是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接受感官刺激开始的,但如果想要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就不能仅仅诉诸于感官经验,必须要引入理性来保证普遍必然性。康德说:“如果没有感性,则对象不能被给予我们;如果没有知性,则对象无法被思维。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在康德这里,知识又分为先天知识和后天知识。我的朋友周濂教授把康德在认识论上的主张概括为“知识的归知识,信仰的归信仰”,这是相当精准的。
对比颜李和康德,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没有认识到人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复杂的,他们没有认识到信仰和道德真正的价值,因此他们是单纯的经验主义者,他们的认识论是残缺的。我相信颜李会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论断,但这个论断本身是错误的,因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是不需要实践来检验的,实践也没有资格来检验真理,能被实践检验的东西,必然是相对的,而真理是绝对的。颜李之所以认识不到这个问题,根本上在于他们眼里没有一个主宰之天,他们不认为主宰之天能够提供绝对价值,所以他们的思想在实践中也必然滑入相对主义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