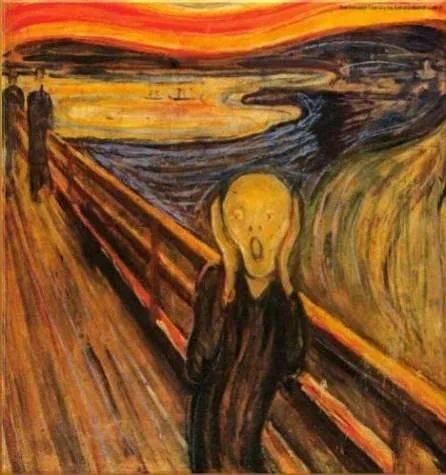
作者 王学良 萧三匝
网上经常见到各种“盛世危言”,在我看来,这些危言几乎一点用都没有。
每当看到各种“盛世危言”,我就想起它的鼻祖——晚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今天就来说说这本书。
郑观应是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家、实业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郑观应所受到的关注远逊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但这无妨其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作为郑氏维新思想的集中表达,《盛世危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十分特殊。
为什么说它特殊呢?
第一,《盛世危言》一书首次要求清政府“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郑观应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宪法”一词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开一代先河。
第二,《盛世危言》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被时人称作“医国之灵枢金匮”,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文化、医疗等方面,而且每个方面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在政治上,此书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制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的观点;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强调女学与男学并重,广建学校与图书馆,在教学重点上,强调发展自然科学,探求自然不仅是为了道德玄理,更是为了科学进步;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法律的黑暗与残暴,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
其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是改良君主专制政体,逐步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正因为拥有如此详细、完备的思想体系,郑观应被誉为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的思想家。
《盛世危言》问世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前夕,光绪皇帝看完此书后,立刻下令印刷两千部,分发给大臣阅读。张之洞也说本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这本书的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等人。
《盛世危言》的横空出世,与郑氏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与后来的孙中山是老乡。他出生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行将结束,《中英南京条约》草签之时。五口通商后,民间人士终于可以直接与外商打交道、做买卖,或直接受雇于外商。香山因为毗邻广州,最先享受到了发展红利,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买办之乡。家乡的生存环境对郑氏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时候,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频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口岸的“猪仔”贸易十分猖獗。所谓“猪仔”贸易即中外逐利客勾结串通贩卖华工,情形与当年欧洲人贩卖非洲黑人为奴相似。耳闻目睹同胞处境,郑观应在十几岁的年纪就写下了《澳门猪仔论》《论禁止贩人为奴》等文章,广受称赞。
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给自己取的笔名是“杞忧生”,这个笔名显然用的是“杞人忧天”的典故,彰显了郑观应无尽的忧思。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国内局势相对平静,朝廷上下弹冠相庆,阿谀者粉饰太平,“同治中兴”成为官场人士的口头禅。“杞忧生”这个笔名与《盛世危言》的书名一样,也体现了郑观应超前的战略眼光。
17岁后,郑观应来到上海谋生。三十岁出头,就被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聘为总经理。后又受到李鸿章赏识,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从太古公司到轮船招商局,意味着他从一个洋行买办转变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对于一个以富强救国为志业的人来说,这是重要的一步。
1884年-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人生蜕变,从洋务派转变为维新派。1884年,郑观应临危受命,前往南洋侦查敌情,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思考。他在《南游日记》中指出,中国之所以难以富强,是因为学习西方不得要领。他说“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
这趟行程使郑观应悟到中国改革的更深层次问题,促使他在53岁时发表集一生思想大成之作《盛世危言》,这本书也是国内最早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进行批判的著作。
《盛世危言》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那么怎样才能让国家从落后走向富强?1900年,郑观应对此书做了最后一次修订,最终本书分为八卷。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宪政”“礼政”“吏政”“刑政”“户政”“兵政”“工政”等部分。郑氏著书之时,更多着眼于实际问题,现实针对性极强。如今时过境迁,“兵政”“工政”乃至“户政”等大部分内容失去了现实土壤,已不足论。如“银行”“保险”“船政”“治河”“电报”“开矿”等节早已失去恒久价值。
所可论者,一是立宪,二是商战,这两点也是郑氏为富强救国开出的两味主药——前者对症于制度救国,后者对症于经济救国。前者又是后者的前提,郑观应就曾愤然指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
让我们先说说立宪。从目录可以看出,郑观应认为立宪之要,首先在于开选举、设议院。他在《公举》一节中写道,今天的官员在剥削民众上无所不用其极,在保育民众上却始终漠视。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
解决之道就是开选举、设议院,公民不限资格,均有选举权。但是郑观应却说公举议员之法不可立即实施,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一制度的实施,必须仰赖于民众智慧达到一定程度,只有开启民智,所选举出的议员才能贤明。
郑观应虽然急于富强救国,但是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他深知变革自有其节奏,急不得。因此他说要广开学校、培育人材,之后才是“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否则议院不过是叫嚣之地。
郑观应理想中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宪制,除了开选举、设议院外,另一要点是明确君主权力。
他在《原君》一节中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简单来说,国家不是皇帝一家的天下,其所有权归于每一个国民。郑观应引用的汉代名著《淮南子》中也提到,“三代”时期之所以要立帝王,目的不在奉养其欲、逸乐其身,而在于为民众谋福利。
然而宋儒读《春秋》,却得出了“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须受无贰”的结论,意思是说,无论君主怎样残暴,臣民都必须忍受。郑观应认为这纯粹是误读,国家不是刀殂,人民更不是鱼肉。
总体来说,郑观应的《原君》思想并未脱出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范围。黄宗羲说:“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原来没有君主的时候,人人还能维护自己的私利,而现在有了君主,连个人的私利都保不住了。可以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个时代反专制、张民权的最强音,郑观应的《原君》说并未能提出新见。
清朝究竟走英式君主立宪之路还是日德式君主立宪之路,郑氏亦未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过从书中议论可以推定,日德式具备相当权力的君主似乎更符合郑氏的理想,也更能为当局所认可。
从思想理路上看,郑观应重视西方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结合,从而对儒家思想进行重新阐释和挖掘,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的康有为等人。虽然在思想转化过程中时常失真,但从现实来看,这也是更能为时人所接受的思想传达方式。
郑观应的另一核心思想是“商战”,在《盛世危言》中,“商战”思想几乎可以占据主导地位,本书的副标题正是“首为商战鼓与呼”。如前所述,“立宪”和“商战”有深刻的内部联系,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
郑氏认为商务是国家之元气。晚清时期,坚持重农抑商的时代虽已远去,但明确提出“商务是国家之元气”的主张依然振聋发聩。他在书中写道“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意思是说,要改变近代中国落后局面,仅仅采取“强兵”政策是不够的,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抵御外国殖民经济入侵,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郑观应将列强的侵略手段总结为三类,分别是“兵战”“商战”和“传教”。他把“兵战”和“商战”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实际上是围绕着经济侵略进行的,是为商战服务的。比起“兵战”,“商战”有更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可以使国家在不知不觉中灭亡。因此郑氏认为,想要自强,必须要振兴商务。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具备两方面特点:一是始终贯穿着抵御列强经济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主线;二是不仅仅停留在思想或口号的提倡上,郑氏一生身体力行,无论是在轮船招商局还是在汉阳铁厂,都立下赫赫功绩。可以说,郑观应是“产业报国”的先行者。
可以说,郑氏的“商战”思想至今还不算过时。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从整体来看,郑观应的思想已经不再具备超越时代的价值了。
让我们先来反思郑观应的“立宪”思想。
首先,那个时代的思想者普遍对宪政进行了误读,即便是“宪法”一词的首次使用者郑观应也没能逃出陷阱。他们将宪政作为一种实现富强的工具,郑氏也不例外,甚至在他看来,开选举设议院不过是为了祛除官吏弄权、躁进、钻营的习气。
从结果上看,宪政与国家走向富强当然有关系,但宪政制度本身并不是为了国家富强而被设计出来的。
简单来说,实行宪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最大程度上保障国民权益,国家富强仅仅是宪政的附属品,绝非其主要目的,将宪政作为一种实现富强的工具完全是本末倒置。
其次,包括郑观应在内的诸多维新思想家将宪政制度简化为设内阁、开议会,对宪政的实施条件和分权制衡理论了解甚少。
真正的宪政包涵三大要素:首先是自愿同意与和平施政,其内涵是政治权力的取得、行使、更迭应当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获得公民的自愿同意,未经公民同意就上台的执政就不是宪政。它解决的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另外,宪政体系下的民众对政府有和平否决权,政府对社会行使和平管理权,双方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
第二个要素是分权制衡与法治。在“无赖假定”之下,公民对国家与政府的权力总是投以怀疑的目光,仅靠定期的自由选举并不能确保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还必须对权力加以分立、制衡。因此,政府权力的范围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即所谓“有限政府”。
第三个要素是对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这也是宪政的最终目的。公民拥有一系列基本权利与自由,任何政府机构和个人不得侵犯。所以西方有句话叫“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从超越的视角来反观那个时代的维新派,不难看出他们的思想有巨大的局限性。但让人遗憾的是,即便至今,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这个局限性:政治制度的背后是文化风俗,文化风俗的背后是宗教信仰。历代的观察者往往忽视了宗教的重要性。
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一篇著名文章中也写道“宗教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
美国学者拉塞尔·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提到,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政治首都,但耶路撒冷是美国的精神首都。作者也在书中阐明,美国秩序不是起源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而是起源于旧约《圣经》,起源于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神,才是美国秩序的首席作者。
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信仰,就没有美国的宪政。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说的那个“无赖假定”正是源自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一切政治哲学都始于对人性的预设,西方宪政思想就是建基于人人都是罪人这个前提之上的。抛开这一人性预设谈宪政是不现实的,试图将宪政与儒家思想结合更是南辕北辙。
为什么呢?因为在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对人性的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既然人性本善,那么我们期待圣君贤相就好了,何必限制最高权力呢?而宪政学说,不就是限制权力的学说吗?
关于人性到底如何,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看法不同,衡量谁对谁错也很简单,我们对比由此建立的一套制度的优劣就一目了然了。既然历史上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也就反证了人性善的预设实在是过于理想主义了,圣君贤相的理想必然是一场迷梦。
郑观应的大问题是只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他既没有深入到西方政治哲学的精髓,更对西方政治制度背后的宗教信仰的基础影响缺乏基本的认识。不仅如此,他居然认为西方人向中国“传教”是列强的侵略手段之一,这就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了。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在历史的三峡中跌跌撞撞穿行了近两百年,但很难说中国人真正理解了西方。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两希”文明,即希伯来信仰与希腊文化。从一开始,我们就只知道“西学东渐”,而不知希伯来信仰为何物,更不知道希伯来信仰的价值甚至高于希腊文化的价值。这,既是因为中国近代积贫积弱,思想先驱对于救亡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人生价值追问的兴趣,也是因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自古就存在浓厚的实用理性传统,以至于至今知识分子还仅仅从所谓的常识出发考虑问题,而没有上升到超验层面深度审视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
“盛世”不需要“危言”,凡盛世,危言也流行不起来。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说郑观应写的是《盛世危言》,不如说是“衰世危言”。
但如果已经到了衰世,危言也就没有任何作用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连皇帝都重视,结果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