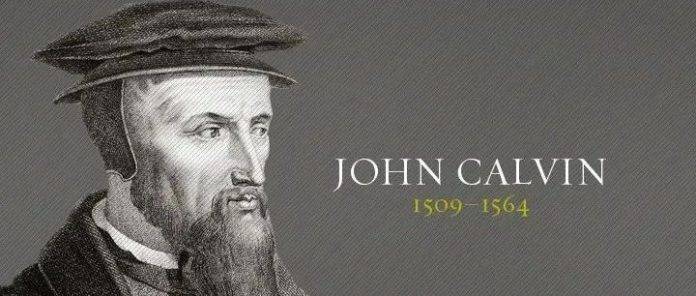一、问题界定:对“加尔文主义”的不同理解
“加尔文是加尔文主义者吗?”[1]要回答这个历史悠久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它本身产生于对于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改革正统(post-Reformation orthodoxy)之间关系现代式的误解。我在此主张研究隐藏在这问题背后的问题,并且通过一些方法来理解其中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以及一些特定主题在改革宗思想中的发展(例如神的预旨、预定和被称为“限定的代赎”的教义),并特别关注加尔文在十六、十七世纪改革宗传统中的地位。
暂不讨论著名的郁金香(TULIP),首先需要讨论的是更基本的问题:“加尔文是加尔文主义者吗?”如果没有给予进一步的限定,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或“可能是”皆有可能,取决于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然而答案必然是混合的或不确定的,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事实上,“Calvinist”(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者的)和“Calvinism”(加尔文主义)这两个词有几种不同的理解,这既决定了人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还界定了人们最初为何提出这个问题。“Calvinist”曾经被用来描述加尔文自己关于特定神学问题的立场,可能最典型的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它也被用于指代加尔文的跟随者,或被一直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宗神学。“Calvinism”这个词也类似,被用来指加尔文独特的神学立场,有时是指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中的神学;它同样也会用来指加尔文跟随者们的神学;更常见的是,它被用作“改革宗”或“改革宗传统”的同义词。
1、“加尔文主义”作为加尔文自己的立场
如果将第一种用法——即“加尔文的”(Calvinist)和“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表示加尔文自己对于一些问题的具体观点,这些问题可能涉及神学、教会、政治甚至哲学等诸多方面——作为这个问题的基础,那么答案很简单:“是的,加尔文当然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这也许正是亨利·科尔(Henry Cole)将他翻译的加尔文关于预定论的多篇论文的合集,命名为《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Calvin’s Calvinism)的用意。彼得·图恩(Peter Toon)和巴兹尔·霍尔(Basil Hall)等作家也采用这种用法,霍尔甚至使用 “加尔文主义”一词来专指1559年的《基督教要义》所展现的完美的“平衡”神学[2]。然而,这种用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至少这使得加尔文成了唯一的加尔文主义者(这显然是有意为之)。
此外,这种用法还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认为1559年的《基督教要义》代表了一种完美的平衡神学,那么评价标准是什么?同时这个结论暗示其他神学家的神学都是缺少平衡的。这些神学家包括乌利希·慈运理、约翰内斯·厄科兰帕迪乌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马丁·布塞尔、海因里希·布林格、彼得·马蒂尔·维米格利(Peter Martyr Vermigli)、沃尔夫冈·穆斯库鲁斯(Wolfgang Musculus)、扎卡里亚斯·乌尔西努斯,以及很多其他与加尔文一样同属改革宗传统的神学家。可以说,这个标准一直是众多这种用法的支持者的个人神学偏向,它包含在对《基督教要义》的现代解读中。这种解读脱离了历史处境,将其看作某种现代神学体系的原型——无论是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卡尔·巴特、伯克维尔(G. C. Berkouwer),还是其他现代神学家的神学体系。这种所谓的平衡,无论是建立在加尔文对预定的理解、所谓的基督中心论、或者他对奥秘的联合(unio mystica)的倡导,都声称在加尔文的思想里有一个连贯性的教义,而这是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的思想里没有的。然而,对于这种用法的支持者们很不幸的是,这个核心在加尔文的思想中也是不存在的。这种融贯主义(coherentist)的用法不仅使加尔文成为了唯一的加尔文主义者,也将加尔文的加尔文主义描述成是原型-施莱尔马赫主义、原型-巴特主义或者是原型-伯克维尔主义。
当围绕着新正统或其他主题的融贯性的现代神话消散后,新的问题仍会出现。将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自己独特的教义等同起来的方法,遇到了一个极度困难的问题,即很难在加尔文那里找到所谓的独特教义。众多书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加尔文的基督论”或者“加尔文的圣餐论”等进行去语境化的建构和解释(仿佛加尔文真的提出了这些独特的教义),又加剧了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在十六世纪进入日内瓦的真正独特的神学家是米格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他没能活着离开日内瓦。独特的或个人化的教义表述并不是加尔文的目标。如果非要说在他的预定论里有独特之处,那就是它的表述方式——加尔文从传统中的思想家那里收集要素,并将它们融合到他自己的神学表述之中。事实上,他的神学表述方式也与布塞尔、维雷特(Viret)、穆斯库鲁斯以及维米格利的表述非常相似。即使是布林格的神学表述也与加尔文的教导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虽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比如亚当与神的预旨之间的关系[3]。同样,在加尔文的圣餐论中也有一些独特的要素——但大部分是来自于布塞尔和墨兰顿。如果有人忽略掉这些共同的部分,单单关注那很少的不同的部分,那么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神学被保留下来,也不会有一系列相关的主题足以构建一个神学体系——即使有人尝试这样做,他也不能拥有加尔文的神学体系,而是一种混杂的教义的集合。这就像一堆切碎的食材,因为烹调的厨师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口味。换句话说,以加尔文神学的独特性来定义加尔文主义,代表着一种错误。
最后,这种用法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它假设了加尔文以及那些在他之后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者”的思想家们共同所属的神学传统,完全是建立在加尔文个人的神学认识上的;并且假设加尔文的神学主要展现在1559年最终版的《基督教要义》里面,成为评估其他人是否属于该传统的基础。它假设后来的改革宗神学家要么有意成为、或者说应该成为加尔文的忠实跟随者,而不能既是加尔文的跟随者,同时又是慈运理、布塞尔、厄科兰帕迪乌斯、布林格或其他人的跟随者。而且他们不能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加尔文跟随者,不能是在他的短文、论文、注释书和讲道集中表达自己的加尔文,不能是1539年、1543年或1550年《基督教要义》中的加尔文,而只能是1559年版《基督教要义》中的加尔文[4]。这种用法获得大量讨论加尔文神学的书籍的认同和煽动,他们都是完全或者几乎完全基于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并且没有检视加尔文之前或与他同时期的其他神学家的观点。他的思想成为了其自身的评估标准,并由此扩展为一切加尔文主义的指南[5]。这种用法如此具有误导性并且把问题简单化,根本无需更多的反驳。它通过否认加尔文大部分作品的重要性,将加尔文从真实的加尔文自身中抽象出来,甚至将他从他所在的历史背景和他所参与的传统中抽象出来。
2、“加尔文主义者”作为加尔文“跟随者”的方法
然而,如果“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是指加尔文的跟随者,“加尔文主义”(Calvinism)是指加尔文跟随者们的神学,那么很显然,没有人可以成为他自己的跟随者。第一种用法让加尔文成为了唯一的加尔文主义者,而第二种用法要么阻止了加尔文成为加尔文主义者,要么退回到助长第一种用法的那种情绪之中,即根据由加尔文自己的神学构建出来的相当狭窄的规范来判断其追随者。同样应当清楚的是,在那些可以被认定为是加尔文跟随者的人中,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与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完全一致。因此以这种方式来提出问题,基本上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按后来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者的人不是加尔文思想的克隆体之程度,加尔文不应该被视为与他们等同;而按加尔文的思想理应为后来的改革宗神学提供规范之程度,那些通常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者的人,因为没有跟随他,就在神学上有严重问题。在这样的框架下,坦率地说,这个问题就成为了假问题。它把加尔文和之后的改革宗作家,都从各自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使用教义概括取代了历史分析。当我们考察有关教义形成轨迹时,例如预定论或基督偿付罪债(satisfaction)时,就会发现类似的情况。
在更复杂的层面,这个问题假设“加尔文主义者”是一个加尔文自己以及那些在他死后一百年内与他同属一个神学轨迹或传统内的牧师、神学家和释经家都会欣然接受的称号。这个假设在这两方面都错了。加尔文本人视“加尔文主义者”这一称号为侮辱,他认为自己的神学是大公信仰的表述。有充分的文献表明,“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这两个词是加尔文的反对者所提出的,尤其在路德宗对加尔文的圣餐教义的批评中明显体现。这两个词的出现,并不是标志着一种来自于加尔文的传统的形成;而是显示了改教家之间存在的分歧。改教家们最初都认定自己是“福音派”(evangdelical),直到十六世纪中期之后才开始有意识地分成不同的认信宗派,即路德宗和改革宗[6]。之后,与加尔文属于同一个传统的神学家们基本都认定自己是改革宗大公信徒(Reformed Catholics),是改革的因而是真正的大公教会的会友和教师,意在与大公教会或普世教会中未进行改革的罗马分支区分开来[7]。当著名的释经学家、神学家安德里亚斯·里韦图斯(Andreas Rivetus,1573-1654)为加尔文的释经要素进行辩护时,他竭力地指出加尔文不是“我们的宗教信仰”的作者和教主[8]。类似的评论在十七世纪改革宗思想家中十分常见,也经常与拒绝“加尔文主义者”这个称号有关[9]。1595年,当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攻击加尔文、维米格利、贝扎、赞奇(Zanchi)和朱尼斯(Junius)的教导时,他被批评的原因就包括用“加尔文主义者”这个“可恶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坚定的信仰者[10]。改革宗神学家开始相对地接受“加尔文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这两个词,并不是改革宗正统或英国清教徒主义崛起的特征——而或多或少地可以被视为是,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的正统神学开始衰落的特征[11]。当时,在改革宗传统经历了非常多的发展之后,将其定义为“加尔文主义”,这与其说是基于其教义系统的大部分内容,倒不如说更多地是基于对它的一些独特要点的确认,例如那些包含在著名的“郁金香”(TULIP,一个血统可疑的缩写词)中的要点。简言之,几乎没有神学家的思想是围绕“加尔文是加尔文主义者吗”这一问题的,他们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这个意义上的加尔文主义者。
那么,扩展开来,这个问题引出了关于鉴别跟随者身份的问题——尽管这可能是一种相对清晰的提问方式,但在历史上,却相当难解决。确切地说,怎样才算是加尔文的跟随者呢?如果定义跟随者的条件是这个人必须自己承认的话,那么在加尔文死后的一个世纪里,可能只有一个加尔文主义者:摩西·亚目拉督(Moïse Amyraut)。更进一步,在关于阿米劳特的所谓“假定普救主义” 的辩论中,许多被当成是“加尔文主义者”的神学家都认为阿米劳特明显背离了加尔文神学的精神,特别是在他引用加尔文的时候[12]。当然,改革宗正统时代之后,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自诩为“加尔文主义者”的人开始大量出现。通常他们这样称呼自己是因为他们拥护某种形式的预定论,不管这种预定论是否清晰地来自于加尔文自己的表述;或者是因为他们反对所谓的阿米念派——那些相信神人合作救恩论的人被称为阿米念派,不管他们是否跟随的是真正(通常不是)阿米念本人的教导。
事实上,大部分被我们认为是加尔文主义者的十六、十七世纪思想家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加尔文的跟随者。当然,一些改革宗传统的奠基者们,例如慈运理、布塞尔、厄科兰帕迪乌斯和法雷尔,属于加尔文之前的时代,他们自然不会认为自己是他们后辈的跟随者,不管这个后辈多么优秀。其他与加尔文同时期的改革宗作家——在这些人之中有沃尔夫冈·穆斯库鲁斯、彼得·马蒂尔·维米格利、海因里希·布林格和约翰内斯·拉斯科(Johannes à Lasco),也不认为自己是加尔文的跟随者,或在这位大师面前扮演次要的角色。在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改革宗作家中也没有人声称自己是加尔文的跟随者或“加尔文主义者”,这些作家包括扎查里亚斯·乌尔西努斯、卡斯帕·奥莱维亚努斯(Caspar Olevianus)、耶柔米·赞奇、阿曼杜斯·波拉努斯(Amandus Polanus),甚至加尔文自己的直接继承人西奥多·贝扎也不曾如此声称。
如果把自我认定的问题暂放一边,仍然存在着如何在相对广阔的传统中来识别跟随者的问题,而这个传统的内容和特征并不是建立在跟随者是否有意追随某个人的脚步的意图上。同时,直到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才开始愿意接受“加尔文主义者”这个名称。有一位神学家,他比加尔文大差不多十岁,在帕多瓦(Padua)和博洛尼亚(Bologna)的大学受训,此后在斯特拉斯堡、牛津和苏黎世教书,基本同意加尔文的观点,虽没有提到双重预定,但是将预定和拣选等同,比加尔文对中世纪神学家(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和里米尼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Rimini])的看法更积极,从不认为自己是加尔文的跟随者,而且希伯来语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加尔文,他应该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者吗?这位神学家就是彼得·马蒂尔·维米格利,他的作品很大地影响了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发展。不管他自己是否承认,他确实经常被称为是“加尔文主义者”[13]。此外,另一位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剑桥大学的神学家明确表示自己是“改革宗”(而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他支持主教制度,他的教导与加尔文相近,但也与维米格利、赞奇、贝扎、乌尔西努斯和奥莱维亚努斯的思想有颇多相似之处。同时,他的教导也显示出一些后期改革宗思想的特点,是在这些改教前辈的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例如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的区分。他应该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者”吗?这位神学家就是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在一些作品中,帕金斯经常被认为是“加尔文主义者”,又鉴于他的思想与加尔文的一些差异,于是被当作将“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者”对立起来的主要例子。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扩大。
那么,有人可能会重新表述一下这个问题,继续问:“加尔文主义者真的是加尔文主义者吗?”或者是更尖锐地提问:“加尔文主义者想成为加尔文主义者吗?”如果“加尔文主义者”是指加尔文的有意追随者,或者确实是加尔文思想的模仿者或复制者,那么答案就很简单:“不,没有加尔文主义者”——当然,除非我们退回到最初提到的定义模式,使得加尔文自己成为了唯一的“加尔文主义者”。
3、“加尔文主义”作为改革宗传统的代名词
当然,还有第三种使用“加尔文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的方式,即指代改革宗传统有关的思想家和教导,这是最常用的用法。历史学家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约翰·托马斯·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l)和最近的菲利普·贝内迪克特(Philip Benedict)的著作中都有证明[14]。在这样的架构下,问题就变成了“加尔文是改革宗吗?”以及“其他与加尔文属于同一认信传统的作家们,不管他们是否作为加尔文的跟随者,是改革宗吗?”可能有人会认为对于回答这个转化后的问题很简单:“是的。”但是这些问题也因为人们对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革宗”的界定方法不同而变得复杂——特别是如果改革宗被当作是“加尔文主义者”的同义词,那么这就或多或少地被要求要符合加尔文本人的神学,无论是建立在对其神学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的理解上,还是在对1559年版《基督教教义》的认同上。如果更好地关注历史背景和相关文献,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种问法:“约翰·加尔文与后来在改革宗认信边界内的思想家们,他们的神学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本质和根源是什么?”——这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神学思考。
二、神学思考:加尔文和之后的改革宗的联系
当然,“加尔文是加尔文主义者吗?”这个问题也常是在一系列神学问题上进行辩论,也许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与著名的“郁金香”相关的两个要点,即预定论和所谓的限定的代赎;以及与圣约相关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呈现为这些内容时,通常会得到否定的回答,而且常常是基于高度可疑的理由。例如将加尔文的预定论和之后改革宗对此教义的理解在几个方面进行对比:据说在《基督教要义》中,加尔文将预定论从神论的范畴关系中“移”出来,放到了更为友好和温和的位置——而加尔文主义者又把预定论放回到了神论附近,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预定论和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15]。此外,加尔文的神学不是预定论式的,而是“基督中心论”式的——而此后的加尔文主义者失去了这种基督中心论的特征[16]。或者,通过混淆方法和内容的方式称加尔文为一位人文主义者——一位以圣约为方式来思考神学的人文主义者,而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们是预定论式的、经院主义式的,失去了这位宗教改革奠基者的人文主义倾向[17]。或者,最后,鉴于加尔文神学的基督中心论倾向,他对基督工作的观点倾向于“非限定的赎罪”,与后来加尔文主义者们的预定主义所导致的“僵化”的“限定的赎罪”观点形成对比[18]。总之,加尔文教导的是一种精致平衡的、基督中心论的神学,而加尔文主义者们则把他们的神学集中在神的预旨上,因此产生了僵化的、经院主义式的“五要点”,也就是以首字母缩写“TULIP”所概括的教义。
1、郁金香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TULIP本身的问题。这个缩写给改革宗传统带来了很多麻烦,并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与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相关的混淆。把一份1618-1619年在荷兰写成的文件与整个加尔文主义联系起来,然后又把其含义降低到只有TULIP的程度,这是相当奇怪的做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毕竟,《多特信经》(Canons of Dort)从未打算成为改革宗神学的综述,也没有被当作是改革宗教会的一个新的认信告白。相反,为了驳斥抗辩派(Remonstrants)的五项主张,《多特信经》是作为荷兰改革宗教会的主要认信告白文献的解释附录而存在的,这些认信告白是:《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教理问答》。
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荷兰语中的“郁金香”不是“tulip”,而是“tulp”。“Tulip”不是荷兰语——有时我在想,当阿米念被指责去掉了“不可抗拒的恩典”时(指TULIP中的I所代表的意义),他是否只是在试图纠正某些人的拼写错误。严肃地说,TULIP与《多特信经》并没有历史关联。据目前所知,TULIP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用法都起源于盎格鲁-美国人(Anglo-American),并且不早于十九世纪[19]。可见,糟糕观点的流行是如此之快。因此,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的关系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简化为了关于TULIP的想象——加尔文教导TULIP吗?任何回答都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解。加尔文自己当然从没想到这个模型,后来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者的人也没有。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加尔文和他的改教同工们所持守的教义与《多特信经》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但无论是加尔文,是他的改教同工,还是多特信经的作者们,都不会把他们的认信立场缩减到仅有TULIP的程度。
事实上,TULIP与加尔文或加尔文主义的关系非常薄弱, 在“T”(全然败坏)和“L”(限定的赎罪)上尤为明显。加尔文论到人类意志和能力的完全扭曲或堕落,是为了反对神人合作主义(synergism)或半伯拉纠主义,同时也指涉罪的普遍性。将这些意义简化为“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一词,会危及到这论证本身[20]。加尔文也从未使用过“限定的赎罪”(Limited atonement)这个词。这两个词都没有出现在《多特信经》中,它们也不符合十七世纪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正统所使用的语言特征。就像TULIP本身一样,这些术语都是盎格鲁-美国人相当晚近的发明。
虽然加尔文自己使用了“完全败坏”(totally depraved)或“完全堕落”(utterly perverse)这样的短语,它们并没有出现在《多特信经》之中。《多特信经》简单地宣称“所有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因此在诅咒之下,命定永远的死亡[21]。换句话说,在TULIP关于“T”的问题上,《多特信经》的用语比加尔文更加考究。“全然败坏”,至少在英语口语中是一个如此吓人的概念,以至于只适用于路德宗神学家马赛阿斯·弗拉齐乌斯·伊利里库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的神学,他对堕落前后的人性有着近乎二元的理解,认为堕落后神的形象(imago Dei)完全被撒旦的形象(imago Satanae)所取代,而堕落后的人性,其实质是罪。无论是加尔文还是后来的改革宗思想家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对路德宗来说,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在《协同书》(Formula of Concord)中拒绝了这种说法。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人是否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良善”,而是“没有能力从罪恶中拯救自己”,而这个意义被现代早期文献中的“全然败坏”一词所掩盖了。因此,加尔文使用“堕落”(pravitas)之类的词语来表示人类的乖戾、邪恶、扭曲或人格的堕落,并不是要否定人在外在行为上有遵守律法的能力,而是指人类普遍的内在人格扭曲玷污了所有人类行为,使得人在神面前成为完全无价值的存在。在这个基本的神学观点上,加尔文的神学和后来的改革宗思想之间有明确的连续性。可以说,《多特信经》以及遵循并支持《多特信经》的改革宗正统神学家们,在人性的堕落这一问题上与加尔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内容相比,提供了更为清晰、细致、甚至是更为温和的理解。
TULIP中“L”的问题,即“限定的”还是“普遍的”救赎, 在关于加尔文是否是加尔文主义者的问题上也很突出。这个问题也是产生于一系列现代的混淆,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将一种高度含糊和时代性错误的语言应用到了十六、十七世纪的问题上。简单来说,加尔文、贝扎、《多特信经》,以及十六、十七世纪正统改革宗的思想家们,都不曾提到“限定的赎罪”这个用法——如果他们不曾提及,也就几乎不可能教导这个教义(毕竟,atonement这个词是英文词汇,而几乎所有古老一些的教义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也为了更关注史料,我们要知道,这个在十六、十七世纪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对圣经中几段经文的理解。这些经文称基督为所有人付上了赎价,或者说神希望救恩临到所有人或整个世界,但同时圣经中也有大量经文表明救赎是专赐给指定的一群人,即选民或者说信徒。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它属于古代教父时期和中世纪教会,也同样属于早期改革宗,并且自彼得·伦巴第(Peter Lombard)的时代以来,人们一直讨论基督偿付罪债的充足性和有效性,及其与救赎宣告的普遍性的关系。
关于加尔文和后来的改革宗之间关系的议题,并不包含任何关于基督之死的价值或功效的争论: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基督之死足以为全世界的罪付出赎价。问题也不在于是否全人类都能得到救恩:所有人(包括阿米念)都同意并非如此。换一种说法,如果“赎罪”(atonement)是指基督之死的价值或充足性,那么在现代早期参与辩论的神学家中,只有极少数人教导“赎罪”是有限的。如果“赎罪”是指在特定的人身上成就的有效的救恩,那么辩论参与者中没有人教导“无限定的赎罪”,除了饱受诟病的撒母耳·胡博(Samuel Huber)。
从历史上看,以十六、十七世纪能够理解的语言为框架,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首先是由阿米念提出并在多特会议给予了回答的问题:既然基督的死足以为所有的罪付上赎价,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它只对某些人有效呢?在阿米念看来,只对某些人有效是因为这些人选择了相信,而其他人选择了不信,预定是建立在神对人的选择的预知(divine foreknowledge)上。而《多特信经》认定,基督之死仅对神的选民有效,这预设了得救是唯独依靠神的恩典。加尔文在这一点上也非常明确:基督之死的应用或功效仅限于选民。此后的改革宗神学家对这一结论也是一致认同的。
第二,另一个问题隐含在十六世纪改革宗作家的诸多表述里,并且明确地出现在多特会议之后十七世纪的一系列讨论中,即鉴于基督的满足的无限价值或者说充分性,是否可以认为基督之死是假设普救性的(hypothetically univdersal)?简单地说,如果上帝意愿如此的话,基督的死是否足以赦免所有人的罪?[22]——或者说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基督之死的价值是否可以使所有人都得救?对于这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可以说加尔文是沉默的。他不经常提到传统的充足性-有效性的模型(sufficiency-efficiency formula),他也没有处理过阿米劳特所提出的问题,即在实际拯救选民的绝对预旨之前,上帝制定了一个假想的或有条件的拯救预旨:若相信就得救。但他确实经常不加修饰地说,基督为世人赎罪,这种“恩宠”将“不加区别地扩展到整个人类”,正如他与稍后的《多特信经》一样认为,上帝的意愿是拯救特定的人[23]。在关于假设普救性的辩论中,许多后来的改革宗人士都诉诸于加尔文(只有十七、十八世纪的少数作家认为,基督的死仅够偿还选民的罪债,无论是在宗教改革时期还是正统时期,他们的观点在改革宗的认信中都没有明确的体现[24])。因此,后来的改革宗神学在这一点上的阐述比加尔文更明确,并且我们可以说加尔文的模糊表述指向(或者可能指向)了若干方向,而多特会议形成的信经正是其中更为清晰准确的一个。
2、预定论、基督中心论和核心教义的问题
关于预定论的问题多少有些不同:没有人否认加尔文教导这个教义,虽然有人声称以基督为中心的加尔文在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中将预定论移到了一个更温和的位置,而他的继任者则重新将预定论与神论联系起来,进而产生出了一种对该教义更加“严厉”的理解。但实际上,加尔文并没有将预定教义的位置移来移去。按照他认为的适合教导教理问答的次序,以及与保罗书信一致的顺序,他基本上将该教义保持在了他第一次放置的位置[25]。认为这是一种更温和的教义布局的想法,忽略了加尔文对预定、拣选和弃绝(reprobation)的定义——无论这个教义是放在其神学作品中的哪个位置,都很少或根本不能削弱预定论这一教义的力量;并且它也相当精确地与后来的改革宗作家们的定义相契合。此外,后来的改革宗神学家们也几乎没有人忽略教义的位置与神学作品的文学类别的关系,他们依据写作体裁的不同而组织教义的次序。一些人呼应了加尔文的放置方式,一些人将预定论放在教会论中,当然,还有很多人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在神论范畴内安排预定论教义的位置。可以说,不同的安排是依据写作体裁的不同:是适于教理问答和认信教导,还是适于在大学研究中更细致的学术或教理讨论。[26]
这里的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核心教义(central dogmas)问题。关于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关系的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人们很大程度上一致地认为,加尔文的神学主要关注在预定论上。这种认定,再加上当时的一种倾向,即认为整个改革宗传统,是关注预定论并事实上围绕预定论而建立起来的,这样就在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之间创造了一种连续性。然而对加尔文思想的研究趋势如今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已经指出的,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神学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加尔文是“基督中心论”的。而后来的改革宗思想被解读为缺乏“基督中心论”,于是将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者对立起来就成为了一种时尚——人们通常会责备西奥多·贝扎,认为是他将改革宗神学从基督中心论转移到了预定中心论[27]。这不但是一种相当武断的方法,忽略了改革宗传统的广度,也忽略了后来改革宗神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即创造了一副关于教义的讽刺漫画,用一个反对另外一个,仿佛加尔文的思想可以被简化为新正统神学基督中心主义的前身,而后来的改革宗作家仅仅是预定论者。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走出这种谬论多长时间,就进入到了一个同样错谬的新阶段:因为基督中心论的说法已经过时了,新的教义核心主义试图将“与基督联合”的模型强加在加尔文的神学中,然后对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做出同样的负面评价——现在加尔文被视为专注在“与基督联合”上,这样他的思想就可以从根本上与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分离开来,据说后者从未考虑过这个概念。正如帕提(Partee)所评论的:“加尔文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与基督联合是他的神学的核心——而不是其他人的核心”。(然而他没有引用任何后来的改革宗著作作为其评论的证据)[28]。我们可以推测,当“与基督联合”的主题过时了,会再有另外一个加尔文思想的核心被识别出来,然后与后来改革宗神学中声称的中心或遗漏相对比[29]。
至于基督中心论的问题,或者说将关注基督论与关注神的预旨对立起来的问题,从历史上来说,是个虚构的问题。它并不是十六、十七世纪的神学关注,而是产生于二十世纪神学的特定模式。如果“基督中心论”(christocentric)是指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论,那么后来的改革宗作家对此的理解虽不比加尔文更多,也不比他更少。所有人都明白基督的死是救恩的唯一缘由,所有人也都把拣选定义为“在基督里”。如果“基督中心论”是指其他的内容,例如把“基督事件”作为上帝的唯一启示,从而成为其神学的中心(这是二十世纪神学的典型作法),那么这个术语既不适用于加尔文,也不适用于后来的改革宗——事实上可以说,从第二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的任何神学家或神学作品都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基督中心论”。无论如何,将“基督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分类标准,用来评估加尔文与其他现代早期改革宗作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有效的方法[30]。
有人认为后来的改革宗作家们提出了加尔文的思想中不存在的特定形式的决定论(determinism),即“预旨神学”(decretal theology),或是一种“预定论式的形而上学”(predestinarian metaphysic)。与这样的议题相关,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些术语和TULIP、“限定的赎罪”、“基督中心论”一样,都不产生于十六、十七世纪,而主要是二十世纪发明出来的术语。当然,几乎所有老的基督教传统的神学家们,都认同一系列名义上的形而上学预设,例如上帝是绝对的或必要的,而创造的秩序是相对的或偶在的。但老的改革宗神学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其归类为某种形式的决定论。后来的改革宗神学家们比加尔文更清楚地指出,上帝是完全自由的并且可以随己意行事;世界是偶在的,并且理性被造物能够按照受造本性而自由行动,拥有矛盾自由和冲突自由[31]。在这里,有人可能会声称加尔文和后来的改革宗作家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不连续性,但仔细阅读他们各自的作品就会发现,加尔文更容易让人产生决定论式的解读, 而改革宗作家的作品反而不那么容易。但是关于预定论的问题,加尔文和后来的改革宗神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加尔文和其他改革宗思想家,无论是他之前的、与他同时代的还是在他之后的,都坚持某种奥古斯丁式的对预定论的理解,正如罗马书第九章和其他圣经文本所教导的那样,也就是,救赎取决于永恒的上帝的恩慈的旨意,所以在永恒中,上帝决定一些人蒙拣选而被拯救,而另外一些人则不是。既然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种长久以来被广泛持守的观点表述,它当然就不能作为标准来判断加尔文或其他任何人是否是“加尔文主义者”。
3、人文主义-经院主义的二元对立
人文主义-经院主义的二元对立以多种形式出现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中。其中一种形式是简单化地对比加尔文的人文主义和后期改革宗神学家的经院主义:简单地说,加尔文是人文主义者;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们则是经院主义者;加尔文不是加尔文主义者。
这种方法会讨论到作品中体现了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方法的思想家,并将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对立起来。最近的学术研究已经明确地表明,加尔文尽管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接受了语文学(philological)和修辞学的训练,但同时在他的思想中又融合了经院主义方法的多重因素,无论是他作品中论题式的和辩论式的表述方式,还是对论题的区分方法[32]。而后来的改革宗,那些“愚昧”的加尔文主义者,不仅在他们更细致的学术研究和论辩中遵循经院主义的方法,并且也使用他们接受人文主义语文学和修辞学训练的成果。事实上,人文主义语文学训练是经院正统时期典型特征[33]。更重要的是,所谓经院主义方法的众多要素,例如对标准话题或普遍要点(loci commune)的识别和排序,实际上都起源于人文主义。
另一种形式的人文主义-经院主义的二元对立,试图克服这个明显的问题(即声称加尔文完全是人文主义的,后来的思想家则完全是经院主义的),而描述了一个在心理上有明显分裂的加尔文,使他成为了这样的一位思想家:他的人格中有广泛的人文主义、恩慈和关注圣约的一面,也有相当学术性、黑暗、以及关注预定论的一面[34]。这种方法出现后,就促成了加尔文和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比——不幸的是,后者忽视了加尔文的人文主义的一面,从而成为了他的传承中学术的、关注预定论的那一面的拥护者。
从几个方面看,这个方法都很有问题。首先,正如布夫斯马(Bouwsma)的著作表明的那样,这种方法建立在一个未经验证的心理学论点上,声称加尔文精神分裂,然后武断地把人文主义和其中的一面联系起来,而又把经院主义和另一面联系在一起[35]。这些结论的得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代作者自己的喜好,将人文主义方法和经院主义方法与特定的内容联系起来,从而混淆了问题,仿佛一个人不能成为人文主义的预定论者或经院主义的圣约神学家。改教家们的思想中,人文主义和经院主义的相结合是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36]。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把“人文主义与圣约思想”以及“预定论甚至决定论与经院主义思想”必然性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像皮埃特罗·庞帕纳齐(Pietro Pomponazzi)和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相信决定论的哲学;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由圣约神学家撰写的经院主义著作,例如著名的圣约神学家若阿内斯·科切乌斯(Johannes Cocceius)和他的学生弗兰斯·伯尔曼(Franz Burman),他们持有典型的改革宗预定论,并遵循经院主义的方法[37],或者因经院主义方法和预定论教义而出名(尽管这对他也许并不公平)的改革宗神学家弗朗西斯·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他也教导相当标准的改革宗关于诸约的教义[38]。
4、加尔文、加尔文主义者和圣约神学
加尔文思想与后来改革宗圣约神学的关系一直是争议颇多的话题。鉴于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关于圣约的简短和似乎单边性(即单方面——编者注)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加尔文根本不是一个圣约思想家,而后来改革宗的作家们则沉浸在圣约的思考中,并且坚持圣约的双边性特征[39]。但还有另一些人称加尔文是坚定的圣约思想家,但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失去了他对恩典的强调,于是沦落为预定主义和律法主义[40]。当然,历史的情形比这两种说法都要复杂得多。但正是这个复杂性多少澄清了加尔文与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
首先,相当奇怪的是,对加尔文的圣约思想持极端单边理解的学术路线,一直拒绝承认其他认为加尔文非常谨慎地区分圣约中的单边和双边特征方面的学术工作。同时他们还拒绝考察加尔文的圣经注释,而这种区分就存在其中。可以说,这种区分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改革宗思想中是普遍的,既存在于加尔文的作品中,也存在于后来的改革宗作家们的著作里。
加尔文的作品和改革宗的圣约神学之间还有其他重要的关系。毕竟,加尔文确实陈述了他对恩典之约的定义,认为其本质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但在实施方式上有所不同[41]。这个定义延续到了十七世纪的圣约神学中。在这个表述上,加尔文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独创的:这种理解在慈运理和布林格较早期的作品中,几乎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现过。把布林格和圣约神学的起源联系起来,认为其区别于加尔文式的预定论,这样的学术路线通常淡化了这种平行关系的重要性,也通常忽略了加尔文实际上并没有就着这个定义来发展他的圣约思想。恩典之约的定义出现在《基督教要义》讨论两约关系的首章。换句话说,除此定义之外,没有太多的圣约神学内容可以从《基督教要义》中挖掘出来——因此,《基督教要义》才没有被后来的改革宗圣约神学家大量引用。但他们频繁又详尽地引用加尔文的圣经注释,因为他关于圣约的思想大部分都记录在其中。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从赫尔曼·韦修斯(Herman Witsius)这样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得着证实[42]。
三、结论
简而言之,“加尔文主义”这个术语和缩写TULIP一样,已经引起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宗传统的身份、以及加尔文与该传统的关系的问题。这两个时代性错误的术语都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加尔文主义”的每一种含义都会导致对约翰·加尔文思想本身,及其与十六、十七世纪改革宗传统的关系的错误理解。缩写词TULIP的使用导致了对《多特信经》的狭隘(如果不是错误的话)理解,而这造成对改革宗传统和加尔文神学的误读。
这些术语,以及如上所述的,加尔文的著作与后来的改革宗传统在神学和思想上的关系的例子,都提出了一个潜在问题,即传统的本质,以及在一个传统内,连续与发展的特征及多样性。正如卡尔•楚曼最近指出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问题需要考虑大量的细微差异[43]。首先,大公教会和《使徒信经》所确认的传统内有基本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宗教改革的两大分支(改革宗和路德宗)和罗马教会中都得以保留。第二,属于特定的宗教改革与后宗教改革时期认信传统内的广泛连续性问题——就改革宗认信传统而言,十六世纪中期的主要认信文本即《高卢信条》、《比利时信条》、《苏格兰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英国国教三十九条》,都有着共同的神学基础。它们的写作群体要么与加尔文存在对话,要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益于他。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加尔文所属的改革宗信仰的国际共同体。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加尔文与他同时代的人,以及加尔文和后来的改革宗传统之间都有明显的连续性。当然,这不是因为加尔文思想的独特性,而是因为它的大公性。
这也是加尔文思想与他所属的传统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个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系列复杂多样的历史处境下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加尔文与改革宗传统的关系是,作为其第二代作者中的一位——即使不总是那个最首要的声音,相对于其他人他可能是这群人中最突出的一个——引领了改革宗传统的特定阐述或思想发展。在威利斯顿·沃克(Williston Walker)看来,“加尔文的思想是规范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44]他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包括慈运理、布塞尔、墨兰顿、法雷尔和厄科兰帕迪乌斯等,也与同时代的人展开对话和讨论,例如布林格、维米格利、穆斯库鲁斯、M. 维雷特、拉斯科。他的著作得到了详细的认可和辩护,他的表述(也许最显著的是他的圣经注释)被参考、修改,并被融入到一个不断发展的、变化的和多样性的神学传统中。加尔文并不是这个传统的缔造者。在这个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加尔文并不是唯一的声音;他也不是该传统发展的标准(norm)[45]。
就像这篇关于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关系的简单综述一开始所指出的,这个问题相当复杂——特别是如果恰当地将“加尔文主义”理解为粗略地指代改革宗传统时。这个问题因为在改革宗正统衰落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个人和团体都自我认定为加尔文主义者或者加尔文派,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团体包括浸信会人士,他们拒绝为婴儿施洗,因此无论是在加尔文的日内瓦,还是在正统时期任何认信改革宗的处境中,都不会受到欢迎。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现代神学家和哲学家也称自己为加尔文主义者,因为他们相信严格的形而上学决定论或兼容论(compatiblilism),而这种观点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改革宗圈子里也不受欢迎。
因此,在这些试图使得加尔文与所谓的僵化的正统神学对立的作法中,存在着高度的讽刺和时代性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认为正统神学没能严格地重现加尔文神学的观点,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产生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教义标准甚至教义口号的驱使。通过对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文献的详细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后期改革宗思想的发展是一场相当广阔的运动,在教会早一些的传统、在改教家群体中都有为数众多的先辈,无论是加尔文的前辈还是与他同时期的神学家。这场运动的多样性反对将之描述为僵化的正统。更重要的是,假若后来的改革宗神学按照那些提出“加尔文是加尔文主义者吗?”这个问题的人所认可的理想方式来阐述自己,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加尔文的思想,那么它作为一场认信运动不仅会失败,而且还会产生最大程度的僵化。恰恰相反的是,后来的改革宗传统借鉴和诉诸加尔文,将他视为改革宗传统的众多奠基人之一,承认他作为第二代改革宗信仰规范者的能力,也承认他作为一个专业思想家的局限,以及他无法解决在变化的处境和其他时代会面临的所有问题。
作为结论,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加尔文是加尔文主义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加尔文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但话又说回来,“加尔文主义者们”也不是。他们都是改革宗传统的贡献者。这个故事也许是告诉我们,要认识到加尔文、改革宗的各种信仰告白,以及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的所谓的加尔文主义者们所拥有的共同立场,并且从源头上认识到该传统的丰富性(当然是在它认信允许的范围内)。如果你确实想的话,“花开堪折直须折”,但请不要在改革宗的花园里种下“郁金香”。
[1] 本文出自Richard A. Muller, 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On the Work of Christ and the Order of Salvation (Ada Township,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12), 51-69。本文为该书的第二章。承蒙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编者注
[2] Peter Toon, The Emergence of Hyper-Calvinism in English Nonconformity, 1689-1765 (London: The OliveTree, 1967), 143; 以及Basil Hall, “Calvin against the Calvinists,” in John Calvin: A Collection of Distinguished Essays, ed. Gervase Duffiel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6), 19、25-26。
[3] 留意Cornelis P. Venema, Heinrich Bullinger and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Author of “the Other Reformed Tradition”? (Grand Rapids: Baker, 2002)一书的结论。
[4] Hall, “Calvin Against the Calvinists,” 19.
[5] 例如T. H. L. Parker, Calvin: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5); Charles Partee, Th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2008)。
[6] 参考John Clvin, Clear explanation of sound doctrine concerning the true partaking of the flesh and blood of Christ in the holy supper, in order to dissipate the mists of Tileman Heshusius, in Selected , Works of John Calvin: Tracts and Letters, ed. Henry Beveridge and Jules Bonnet, 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3), II: 502、 510、526、563, 以及Brian Gerrish的评论, The Old Protestantism and the New: Essays on the Reformation Herit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27-48。
[7] 例如 William Perkins, A Reformed Catholike: or, A declaration shewing how neere we may come to the present Church of Rome in sundrie points of religion: and vvherein we must for euer depart from them, in The Whole Works of…Mr. William Perkins, 3 vols. (London: John Legatt, 1631), I。
[8] Andreas Rivetus, Catholicus Orthodoxus, oppositus catholico papistae (Leiden: Abraham Commelin,1630), 5.
[9] 例如Pierre Du Moulin, Esclaircissement des controverses Salmuriennes (Leiden: Jean Maire, 1648), 231-32; Jean Claude, Défense de la Reformation contre le livre intitulé Préjugez légitimes contre les calvinistes,4th ed. (Paris: L.-R. Delay, 1844), 210-11; Pierre Jurieu, Histoire du Calvinisme et celle du Papisme mises enparallèle: Ou apologie pour les Réformateurs, pour la Réformation, et pour les Réformés…contre…Maimbourg, 3 vols., 2nd ed. based on the Rotterdam printing of 1683 (S.l.: s.n., 1823), I: 417-18。
[10] 见John Strype, “eos odioso nomine appellans Calvinistas.” in The Life and Acts of John Whitgift, D.D.,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22), III: 318。
[11] 参考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Dewey D. Wallace, Shapers of English Calvinism, 1660-17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14; 注意Christoph Strohm坚持使用这个词,尽管它有本质性的问题, “Methodology in Discussion of Calvin and Calvinism,” in Calvinus Praeceptor Ecclesiae, ed. Herman J. Selderhuis, Pap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alvin Research, 2002 (Geneva: Librairie Droz, 2004), 68。
[12] 参考 Du Moulin, Esclaircissement, IX. i (232); 见本书第四章,关于加尔文自己的意思和亚目拉督(Amyraut)对加尔文的描述之间的区别。
[13] 关于Vermigli, 见Frank A. James III, Peter Martyr Vermigli and Predestination: The Augustinian Inheritance of an Italian Reform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14]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Macmillan, 1939; rep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93-97; John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vii-viii, ; et passim Philip Benedict, Christ’s Churches Purely Reformed: A Social History of Calvi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xxii-xxiii.
[15] Hall, “Calvin against the Calvinists,” 19-37.
[16] 例如Walter Kickel, Vernunft und Offenbarung bei Theodor Beza (Neukirchen: Neukirchner Verlag, 1967)。
[17] 因此,Brian G. Armstrong, Calvinism and the Amyraut Heresy: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and Humanism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18] 例如 M. Charles Bell, “Was Calvin a Calvinist?”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36/4 (1983): 535-40; M. Charles Bell,“Calvin and the Extent of Atonement,” Evangelical Quarterly 55 (April, 1983): 115-23; James B. Torrance, “The Incarnation and Limited Atonement,” Scottish Bulletin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2 (1984): 32-40; Kevin Dixon Kennedy, Union with Christ and the Extent of the Atonemen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19] 见Ken Stewart, “The Points of Calvinis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cottish Bulletin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26/2 (2008): 187-203. 当然,在改革宗和阿民念的争论中,很多早期文献中出现了“五要点”的用法,例如 Peter Heylin, Historia quinqu-articularis: or, A declaration of the judgement of the Western Churches, and more particularl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the five controverted points, repraoched in these last times by the name of Arminianism (London: E.C. for Thomas Johnson, 1660); 以及Daniel Whitby, A Discourse concerning I. The true Import of the Words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II. The Extent of Christ’s Redemption. III. The Grace of God…IV. The Liberty of the Will…V. The Perseverance or Defectibility of the Saints (London, 1710; 2nd ed., corrected, London: Aaron Ward, 1735),经常被称为“惠特比五要点”或“阿民念主义五要点”: 注意 George Hill, Heads of Lectures in Divinity (St. Andrews: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796), 78。像“加尔文主义富于区分力的五点”这样的短语也在较早时候出现,用于指代多特信经,但并没有说明这些要点本身:见, 例如:Daniel Neal, The History of the Puritans and Non-conformists…with an account of their principles (London: for J. Buckland, et al., 1754), I: 502; Ferdinando Warne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 vols. (London: s.n., 1756-1757), II: 509; 还要注意的是Daniel Waterland布道集的编辑将唯独因信称义作为“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之一:参Waterland, Sermons on Several Important Subjects of Religion and Morality, preface by Joseph Clarke, 2 vols. (London: for W. Innys, 1742), I: xviii。
[20] 留心加尔文的用词,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 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 Tracts and Letters, ed. Henry Beveridge and Jules Bonnet, 7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3), I: 133-34; III: 108-09。
[21] Canons of Dort, i.1, in Philip Schaff,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with a History and Critical Notes, 6th, ed., 3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31), III: 551.
[22] 注意,如果接受耶稣的偿付罪债只对选民有效,就是接受“限定的代赎”的教义,那么就应该认可各种形式的假设普救主义,承认它们是限定的代赎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尽管假设普救主义被十七世纪的改革宗教会的众多会议审判,但却与多特信经的教导一致。另外,Amyrant也教导限定的代赎。
[23]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本书第三、四、五章。
[24] 关于基督偿付罪债的范围的各种立场观点的详述见本书第三章,脚注22。
[25] Richard A. Muller, The Unaccommodated Calvin: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of a Theological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8-39.
[26] 参Richard A. Muller, “The Placement of Predestination in Reformed Theology: Issue or Non-Issue?” in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40/2 (2005): 184-210。
[27] 参,例如, Hall, “Calvin against the Calvinists,” 25-28; Johannes Dantine, “Les Tabelles sur la doctrine de la prédestination par Théodore de Bèze,” Revue de théologie et de philosophie, 16 (1966): 365-77; Kickel, Vernunft und Offenbarung bei Theodor Beza, 136-46。
[28] Parte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3、4、25、27、40-41; 参考Julie Canlis, “Calvin, Osiander, and Participation in G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Theology 6/2 (2004): 169-84. 本书第五章将详尽讨论这一问题。
[29] 注意有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加尔文的与基督联合的教义的,它结合历史处境,又明确避免了Partee和Canlis的错误解读,J. Todd Billings, Calvin, Participation, and the Gift: The Activity of Believers in Union with Chri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 以及Mark A. Garcia, Life in Christ: Union with Christ and Twofold Grace in Calvin’s Theology (Milton Keynes: Paternoster, 2008), 18。
[30] 参考Richard A. Muller, “A Note on ‘Christocentrism’ and the Imprudent Use of Such Terminology,”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68 (2006): 253-60。
[31] 正如Willem van Asselt所记载的。Willem J. van Asselt, J. Martin Bac, and Roelf T. te Velde, trans. and eds., Reformed Thought on Freedom: The Concept of Free Choice in the History of Early-Modern Reformed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2010)。
[32] David C. Steinmetz, “The Scholastic Calvin,” in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Essays in Reassessment, ed. Carl R. Trueman and R. Scott Clark (Carlisle: Paternoster Press, 1999), 16-30; 参考Muller, Unaccommodated Calvin, 36-61。
[33] 参Peter T. van Rooden, Theology, Biblical Scholarship and Rabbinical Stud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nstantijn L’Empereur (1591-1648), Professor of Hebrew and Theology at Leiden, trans. J. C. Grayson (Leiden: Brill, 1989); and Stephen G. Burnett, From Christian Hebraism to Jewish Studies: Johannes Buxtorf (1564-1629) and Hebrew Learn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eiden: E. J. Brill, 1996)。
[34] William J. Bouwsma, John Calvin: A Sixteenth-Century Portra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Philip C. Holtrop, The Bolsec Controversy on Predestination, from 1551 to 1555, 2 parts (Lewiston: Edwin Mellen, 1993).
[35] 参我对Bouusma解读加尔文的批评。The Unaccommodated Calvin, 79-98。
[36] 参,例如,Frank A. James III, “Peter Martyr Vermigli: At the Crossroads of Late Medieval Scholasticism, Christian Humanism and Resurgent Augustinianism,” in Trueman and Clark, Protestant Scholasticism, 62-78; and Scott Manetsch, “Psalms before Sonnets: Theodore Beza and the Studia humanitatis,”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Harvest of Late Medieval and Reformation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Heiko A. Oberman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Andrew C. Gow and Robert J. Bast (Leiden: E. J. Brill, 2000), 400-16。
[37] 参Willem J. van Asselt, “Cocceius Anti-Scholasticus?”in Reformation and Scholasticism: An Ecumenical Enterprise, ed. Willem J. van Asselt and and Eef Dekker (Grand Rapids: Baker, 2001), 227-51。
[38] 参James Mark Beach, Christ and the Covenant: Francis Turretin’s Federal Theology as a Defense of Divine Grac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7)。
[39] J. Wayne Baker, Heinrich Bullinger and the Covenant: The Other Reformed Tradition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d J. Wayne Baker, “Heinrich Bullinger, the Covenant,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in Retrospect,”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29/2 (1998): 359-76.
[40] 例如, James B. Torrance, “The Concept of Federal Theology—Was Calvin a Federal Theologian?” in Calvinus Sacrae Scripturae Professor, ed. Wilhelm H. Neuse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15-40; James B. Torrance, “Covenant or Contract? A Study of the Theological Background of Wo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Scotland,”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23 (1970): 51-76; and James B. Torrance, “The Incarnation and “Limited Atonement,” Evangelical Quarterly 55 (April, 1983): 83-94。
[41]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John Allen, 7th ed., 2 vols.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Christian Education, 1936), II: x. 2.
[42] 参Richard A. Muller对这些引用的讨论。Richard A. Muller, “Reception and Response: Referencing and Understanding Calvin in Post-Reformation Calvinism,” in Calvin and His Influence, 1509-2009, ed. Irena Backus and Philip Bened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2-201。
[43] 参Carl R. Trueman, “The Reception of Calvin: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s,” Church History and Religious Culture 91/1-2 (2011): 19-27。
[44] Williston Walker,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Scribner, 1918), 392.
[45] 参考Williston Walker, John Calvin: The Organizer of Reformed Protestantism (1509-1564), repr., with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by John T. McNeill (New York: Schocken, 1969), 1; Reinhold Seeberg, Text-book of the History of Doctrines, trans. Charles E. Hay, 2 vols. (Grand Rapids: Baker, 1977), II:394; George Park Fisher,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New York: Scribner’s, 1894), 318; McNeill,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3-4; Perry Miller, New England Mind,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