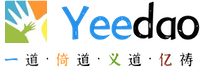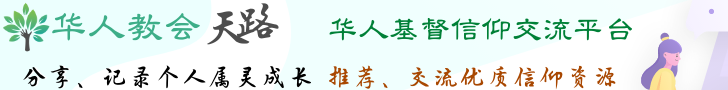從歐洲人的角度來看,所謂的“未知的中國”可能毫不誇張地佔據了中華帝國的四分之一。本書所涉及的旅程,穿行於中國一片與未被探索的廣袤無垠的土地,就如同蘭開夏郡與英格蘭其他地區的對比一樣。這片未被探索的區域,如果以種族親緣關係作為判斷標準的話,完全可以被稱為“諾蘇之地”。在1909年至1915年間的多次旅行中,我們遇到了至少四個不同的苗族部落、不同階層和群體的諾蘇人,以及其他種族身份尚未確定的部落人。如果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調查團隊,帶著充足的資金和足夠的時間,那麼一本對學者和普通讀者都極具吸引力的著作,就可以被添加到《金枝》的系列中。這將是一段多麼令人驚歎的記錄啊,它將帶我們回到西元前的許多世紀,回到人類種族的嬰兒時期!這是一個關於偉大的遷徙、激烈的部落戰爭和血腥的世仇、種族的碰撞與排斥、殘酷的奴隸制和頑強的獨立精神的故事。所有這些,以及更多,如今已被歲月的流逝所掩蓋,只剩下模糊的線索和零星的跡象,我們只能從中窺探過去的故事。——美論義
這是美論義(C.N.Mylne)在1921年2月的Missionary Echo上發表的一篇評論和介紹Samuel Pollard 所著的In Unknown China(漢文譯《在未知的中國》,英文初版1921年於英國發行)一書的文章的開頭。美倫義是聖道公會1908年差往中國西南地區去的教士,主要負責現今威寧一帶的彝族事工。追溯歷史,我們可知,1904年Pollard在昭通迎來了事工的巨大轉機,那时苗族人湧進了他的視野,抓住了此次的機會,他們的事工就會迎來新的局面。事實也是如此,Pollard贏得了此地苗族人的心,並成為宣 教 史上一個常被人紀念的人。
當我們談及這段歷史,目光若僅專注於苗族人身上的話,就只會看到精彩故事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奔赴昭通的這段時間裏,除了苗族人外,我們還可知道的是,有一些彝族人也來到了昭通,尋找Pollard。相比於1904年去昭通的苗族人來說,他們人數很少,但不可忽視的是,這部分彝族人此後也同樣在威寧形成了循道公會西南教區的一個彝族中心,成為了近代威寧彝族的一個開啟“現代化”進程的閃光點。如果說,威寧苗族從石門坎教育體系中出來了兩位博士的話,那麼,在威寧彝族四方井教育體系中,也同樣培養了兩位博士。
隨著威寧苗、彝Church的進一步發展,逐漸形成了石門坎和四方井兩個中心。Pollard主要負責石門坎,那麼,四方井,就自然需要另外一個人來負責。而選出來負責四方井事工的第一位教士,就是美論義。1907年他申請作為教士前往中國西南獲得批准,1908年到達雲南昭通,隨即專門負責新開闢不久的彝族事工,直至1917年回國修養。1921年,美論義重新回到雲南,此時他被安排在會澤(東川)一帶服侍,這裏有一支名為“葛潑”的彝族人。“葛潑”也成為了此時的美論義主要服侍的對象。1927年,美論義回到英國,因身體健康原因,不再返回中國。1970年逝世,享年86歲。關於他的故事,一定也是非常精彩的,待以後慢慢的瞭解更多。
美论义(Clement Noble Mylne)小传(1885-1970)
此前曾和一位前輩聊到中國西南民族相關歷史文化時,他說,這個地方,是可以產生像《金枝》一樣偉大的作品。《金枝》(The Golden Bough,1910)是英國人類學家費雷澤(J.G.Frazer)的集大成之作,是探討和研究人類世界的巫術、信仰、觀念等的一本人類學著作,在學術界可謂是家喻戶曉。
近日閱讀到有關美論義的資料時,筆者才注意到,此想法,原來早在一百多年前,那位曾在中國西南地區生活過的英國人,就已經想到了。美論義作為一個教士,長期在彝族人中生活,他對這片土地以及人民,都會產生好奇。作為一個英國人,他更知曉並閱讀了《金枝》這本著作,並在自身經歷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與該書所描繪的內容極其相似的人類文化習俗、信仰等。
《在未知的中國》一書是Pollard對“諾蘇”人及其生存環境描述的一本著作,是他旅行“諾蘇”之地後產生的遊記。該書中文版早已翻譯出版,很多人都已閱讀過,便不再多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