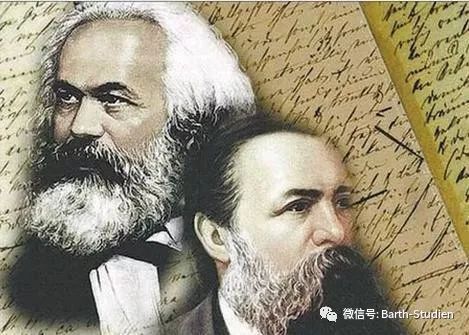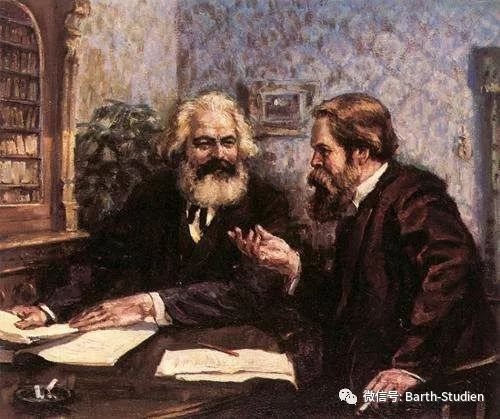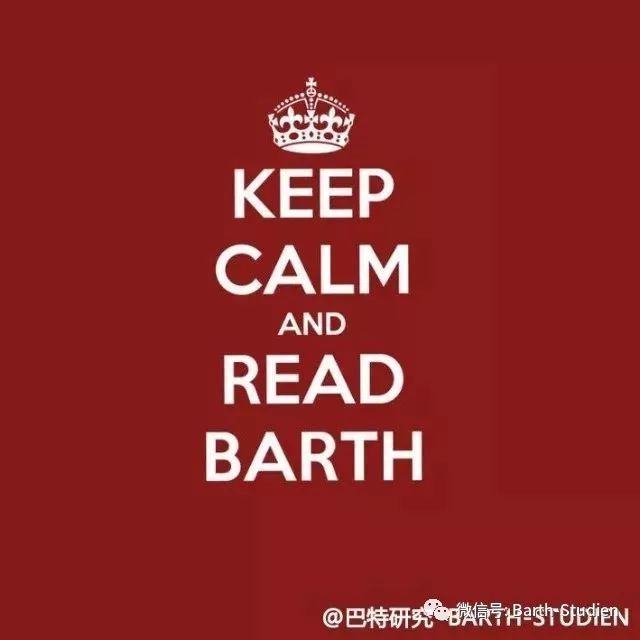作者 李志雄
编者按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依据巴特的言论论证马克思主义对巴特的影响。按照作者的说法,巴特神学反对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追求宗教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巴特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尽管出发点不一样,但他们针对现实社会处境的批判,都因具有相同的历史语境而能找到可对话的地方。巴特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一,在神学政治范畴上,巴特吸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常年以牧师的身份和工作,服务工人阶级和贫困人群。其二,在神学政治方法上,巴特模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人向资本家争取权益而斗争。其三,在神学政治理想上,巴特借鉴马克思主义革命世界观,推动认信教会反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独裁,为教会和信徒争取自由而战。在作者看来,通过论证巴特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神学的对话交流,也有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同基督教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总而观之,作者这篇文章主要承继的是巴特研究界中柏林学派的思路。这一学派强调,要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即社会主义,的维度来理解和解释巴特的神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神学思想。关于巴特研究的不同学派,我们将会有相关文章加以简要介绍。从不同的径路研究巴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解读巴特,这有助于我们在汉语处境中理解和对话巴特。我们期待,作者能够就此做出更进一步与深入的研究,为巴特思想在汉语处境中的生发与展开再作贡献。此外,据编者了解,原文提及的四十三篇手稿已于近期正式出版:Karl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09-1914, Karl Barth Gesamtausgabe, Band 48,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2012。这也将有助于我们关于巴特思想的研究。
此次推送原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六期。感谢出版方和作者本人授权巴特研究公众号进行推送,文章发布时略作修订。公众号期待和读者一道感受巴特神学思想的魅力,一同在且思且行的朝圣路上前行!
导言
马克思主义确实影响了卡尔·巴特及其神学,证据之一是巴特早期的言论。在未出版的四十三本早期手稿中,时间从1911年10月15日到1919年11月29日,记载了他“社会主义演讲(Socialist Speeches)”的讲稿或提纲,其中多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言论。在1915年8月16日一篇名为《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的讲稿中,巴特针对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人格可改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言论而指出:“马克思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仅仅具有经济进展的形式,而更多具有生活的人应对物质所显露的独立性。在这些处境中并超越它们,人类要提升。关系是相互关系。……不是先有更好的人类,后有更好的状况。不是先有更好的状况,后有更好的人类。它们两者共同交织在一起。我们需要人类掌握社会主义真理的超越影响力。”[1] 此处,体现了巴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辩证解读和对社会主义真理的超越意义的肯定,类似例子还很多。尽管巴特的四十三本原稿尚未出版,但他这类言论摘录于已出版的《神学的无畏:弗里德里希·威廉·马库尔德论文选》中。马库尔德(1928-2002)是巴特的得力弟子,而该文选编辑之一的安德鲁·潘格利茨(1954-)则又是马库尔德的弟子,从学术传承特别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学界来说,此史料的可靠性是没问题的。
证据之二是巴特后期的言论。在发表于1949年夏《东方和西方间的教会》的文章中,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相提并论,把约瑟夫·斯大林的人物形象与诸如骗子希特勒、戈林、赫斯、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罗森博格、施特莱彻等相提并论,这是十分荒谬的。”[2] 显然,巴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与纳粹主义相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暴政屠杀的政治人物。从他所列举的纳粹人物来看,他对其领袖、盖世太保首长、副元首、宣传头目、军团司令、外交家、理论家、出版家等无比痛恨。
证据之三是巴特弟子的评价。马库尔德曾撰文《卡尔·巴特神学中的社会主义》,该文收录在《卡尔·巴特与激进政治》一书中。他认为,“巴特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信条的炽煤(glowing coal)’所激励,即世界转变的革命目标。”[3] 马库尔德的此番断言仿佛是晴天霹雷,不但震惊了巴特神学营盘,也震惊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作为亲身经历纳粹战争苦难的德国人、直接受教于巴特的高徒、柏林城大学校区多年的学生牧师、一生致力于“神学和社会主义研究” 的系统神学家,马库尔德的断言是否可信?马库尔德以巴特神学左派的立场来捍卫巴特神学,并不是巴特神学的修正主义者。“仅就马库尔德直到临终反反复复强调他自己是左派巴特主义者(leftist Barth)的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问题。”[4] 基于以上证据,我们尚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何以且如何影响了巴特神学,进而反思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神学的辩证关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更好地指导中国当下的宗教工作。
1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这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弊病及社会矛盾的日益加重,其核心可归结为资本主义极具毁灭性所导致的“人的危机”。当整个德国乃至邻邦高呼“希特勒万岁”之时,巴特能勇敢地站出来说“不”,于是在1934年他被禁止在德国大学任教,之后被驱逐出德国。“巴特强调‘人的危机’,乃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绝妙的神学写照。当人们对自由派神学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进步、上帝内在于人生世界、天国即将在人间降临这类乐观说教感到幻灭时,巴特正从其对立面来重新开始现代神学的建构。”[5] 在巴特神学构建的历史背景中,既有他个人挑战危机的实行,也有时代危机的重压,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危机的创伤,因而人们习惯将他第一阶段的神学称为“危机神学”。危机神学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反霸权、反独裁、反战争。就此而言,巴特神学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神学政治特色,它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巴特的人生历程并不是陷在象牙塔里的神学玄思冥想,他的职业生涯是从牧师开始的。从1911年至1921年,他在瑞士阿尔高州的萨芬维尔(Safenwil)小镇做了十年乡村牧师。“……当我搬到工业镇萨芬维尔后,我的神学兴趣显然退居第二位了。……因我在自己社区里所发现的状况,我变得热衷于社会主义(socialism)和工联运动。”[6] 巴特在自己社区里发现的状况,直言之就是资本主义恶化状况的一个缩影。作为有正义感和良知的牧师,他不像有些牧师一样回避现实或虚谈神学,而是以行动来践行神学。可贵的是,他十年如一日地为监狱里犯人布道、走村访户、为孩子开办坚振礼辅导班、创建工会、研究工厂法规和保险、为工人向资方争取权益等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超出了一个牧师的应有之责。“村里的人们都称巴特为‘红色牧师’。正是在萨芬维尔做乡村牧师的实践,使得巴特越来越疏远学院的现代自由派神学而接近宗教社会主义运动。自由主义神学无助于牧师为小镇的人们争取各种权益的斗争实践,丰富的神学知识面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只能说出空洞的说教。”[7] 可见,巴特政治神学的形成,得益于他早年做牧师的社会实践,社会主义思想在他心中逐步形成。此外,参加党务活动和与资本家斗争,更坚定了他的社会主义立场。“尽管他对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参与深感不满,1915年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党政活动中活跃,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党的大会。在与资本家和工厂主的公开论争中立场鲜明,一贯站在工人一边,即使这会导致教堂会众中的严重冲突(serious conflict)。”[8] 这个社会民主党,据乔治·豪欣居(George Hunsinger)考证,“就是列宁在瑞士流亡期间的政党,是当时政治运动最激进的组织。巴特参加该党以显示他的同心同德,尽管他也公开尖锐批评该党。”[9] 可以理解的是,巴特的红色牧师职业生涯中,既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又有鲜明的独立意识,这种职业实践,使得他的神学政治逐步发展成熟。
时代危机也促使了巴特神学政治的发展成熟,特别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与违背比利时中立相比较,它给我带来了更恶劣的东西——九十三位德国知识分子的可怕宣言。他们在世界面前支持皇帝威廉二世和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战争方针。……神学经文、伦理、教义和布道的整个世界,迄今我所接受的根本可靠的(credible)东西,抖掉到了地面,连同那时从德国神学家笔端所流淌出的一切。”[10] 巴特以形象的语言描述了残酷战争对他以前所信奉的自由主义神学的冲击,迫使他反思教会在面对社会危机时的应有使命。最能反映其本色的是,他坚信来自教会的革命力量。在著名的《巴门宣言》中,也即创建认信教会的纲领中,他明确宣称,“我们否认错误的信条,除了全体牧师之外,教会应当或已经应当把自己或允许把自己交给被赋予统治权力(ruling authority)的特殊领袖(Führer)。”[11] 这个特殊领袖,等于是点了希特勒的名。巴特敢于摸老虎屁股,显示了一位正义神学家的勇气,在黑暗独裁时期为教会争取了独立和自由,也增添了他神学政治反霸权的革命色彩。“他的神学是反霸权(against hegemony)的,他把基督徒的生命理解为不断反霸权的斗争。然所以是反霸权的,因为他理解人类生命里的生动、欢快、庆祝和宽恕都许诺(promised)在基督之中。”[12] 因而,我们可理解巴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坚定的反纳粹立场,他把战争和资本主义视为两种最大的残暴行径,由此可理解为何他在神学政治中推崇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并不是他信仰的核心,他信仰的核心是上帝,是一切许诺在基督之中、启示在福音之中的。
关于社会主义,巴特把它和福音关联起来。“……信仰上帝是革命性的。……资本主义的罪恶(the evil)就是一个没有上帝世界的结果。……社会主义,……‘就是对福音的一种非常重要而必需的应用(application)。’”[13] 在他看来,福音与社会主义,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比只纯粹讲福音的那些神学要务实得多, 它加入了人的实际行动、落实检验和切实提升等具体的社会生活,因而神学的问题,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学的问题。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巴特指出:“由于否认一个从自然和人中分离出来的抽象的神的存在,他仅认定了上帝的本性就是人的真正本性。……他仅认定了人类学就是真正的神学。……宗教只是关于人自身的最深感受,……”[14] 在巴特的看来,人与上帝的关系不是个体性的而是总体性的(totality),人拥有(having)这些总汇形式的关系,形成社会性范畴,真正的神学是人的社会性范畴的总和。这正如马克思早就批判过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 鉴此,当我们分析巴特在实践层面对社会主义的坚守,却探究出他在神学上的人类本质论与马克思在社会学上的人类本质论结论一致的看法,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而无论是针对人类本性还是社会本性,它们都是历史形成的。由此,巴特在揭示人是身体与灵魂的统一的神学命题时,借用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来阐明。他分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个维度,即对整个人类以经济为核心的历史的断言、对凭此阐释以往历史进程的批判、对人类历史未来进程的预言及对人类的召唤。他批判陈旧的神学论辩——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是罪恶道德的产物即假冒科学唯物主义。“然则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能够利用身体和灵魂的信条,尽管这显然与它本有的意图相反,此缘于粗俗唯物主义的特定崇拜。它事实上确实利用了。它把自身与此信条相联系,形成了始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Marxist view of the world)东西。”[16] 因此,毫不奇怪巴特用马克思主义范畴来阐述神学命题,也不奇怪他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描述宗教现象。“当巴特以社会性范畴的术语来描述宗教时,他大部分继续做的是采用一种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方法(downright Marxist manner)。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如同对巴特也一样,宗教本身就是社会现象。”[17] 由此,巴特出台了他的神学政治,它是社会实践和神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既不是偏激的神学革命,也不是虚无的神学玄论,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战争磨难、种族灭绝和理性癫狂后的神学政治构建。
显然,我们不能将巴特的神学政治等同于政治神学,仿佛他的神学可简化为政治神学。“然神学是教会的职能。……神学作为科学(science),区别于对信仰和生命简单验证的‘神学’和对上帝服务的‘神学’,它是教会对其脆弱和责任话语的衡量(measure)。”[18] 神学在巴特看来其功能主体是教会,是超越于信仰体验、生命活动和宗教行为的科学。尽管政治也是科学,但就深刻性和真实性而言,它远非神学可比。“哲学、伦理和政治也是原罪和丧失的人的言语,不论它们多么深刻和真实,都不能认作为审判——以上帝之名向原罪和丧失的人说话的道(Word)。……为服务于上帝对人的话语,当它应当这样做时,神学(Theology)本身是人自身带有且关于人自身的诸多对话形式的唯一者。”[19] 巴特把神学放在很高的位置,缘于其内容是上帝的道,其目的是服务于上帝对人的话语,其化成是人的正当性。政治如同哲学、伦理等应置于神学之下成为其衍生品,而不是反过来。巴特神学最后发展为辩证神学,但不是政治神学。“把巴特说成是政治神学家或他拥有政治神学是不恰当的,巴特当然拥有关涉社会-政治现实的神学,但这不能使他成为政治神学家。”[20] 巴特是神学家,他的神学关涉政治,自有其道理。“巴特曾经将政治位列在神学之后,认为它是仅次于神学的一门伟大学科,这并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奠定下政治这门知识在西方的权威性与主宰性地位,而是因为神学与政治在人事上比其它任何知识都具有权威性,因为它们都要求统治整个人的生活:一个要凭借精神的权力,一个要凭借物质的权力。”[21] 就此,我们才可理解他所论断的社会主义。“耶稣和社会主义——并不如同是一者对另一者的绝然(diametrically)反对。……在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基督教。”[22] 他从理论辨析上将神学核心与政治理想辩证统一起来,从历史维度将政治运动与宗教发展融合起来,将神学与政治联结得紧密,但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启发了他的神学政治?如前所分析的,巴特的早年牧师职业生涯,伴随着他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在那时,我不得不读桑巴特(Sombart)和赫克勒(Herkner)的书,读瑞士商业联合报和纺织工人报。”[23] 桑巴特和赫克勒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前者还是宗教社会学家,他们都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巴特是工人的牧师,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逐渐上升到对其神学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4] 巴特也一直在实践层面上思考着上帝和人的关系,思考人如何获得真理。如他所言,“上帝对我们仁慈,这意味着:‘彼岸涉及我们的此岸,我们的此岸与‘彼岸’有关;因此我们不能承认隔离彼此两岸的封锁线。……恩典意味着:你的意志在地上实现,如在天上!”[25] 尽管巴特是从神学的层面来思考真理,就神学政治来说,他实质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巴特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最近切的理论含义是什么,却是社会主义的实践(praxis)。……巴特神学实际上根植于(如同他在理论层面上意识到的)他的政治参与(实践praxis)。”[26] 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仅因他悄然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而且是日复一日、亲身行动的结果。“巴特神学的真正起源是他在萨芬维尔的神学生存。如此,那种生存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保留的萨芬维尔期间超过500场的布道中,巴特发现了他信仰和行动的融合点。这些文献是他神学的肇始(genesis)。”[27] 所以,巴特神学所具有的实践特色,与他亲身社会实践和主动吸收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是分不开的,这构成了他神学政治中的能动因素。
在神学政治的方法上,巴特模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此作工具为工人向资本家争取权益而斗争。基督徒将圣经视为上帝的启示言录,而巴特将研究圣经与关心穷人联系起来。“圣经是站在穷人,不名一文的、赤贫的人一边的。圣经称为上帝者是站在穷人一边的。”[28] 他的穷人政治的神学立场是鲜明的,在将神学立场实践到其神学政治中时,他不断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批判资本主义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当涉及到穷人政治时,“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社会公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29]等词语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但巴特不是政治经济学家,他是神学家,他的出发点往往是圣经。“把圣经当作‘学识世界’,那就成为一个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和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功能,而不是作为一种简单现象。”[30]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和分析模式,巴特在此有效模仿,意在说明经文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表明意识形态本身就被包含在神学中,神学具有超越和批判世俗政治的本职。巴特作为牧师为什么能团结工人向资本家争取合法权益?作为在德国的外国人为什么敢放弃对希特勒效忠?“巴特的神学政治在于它捍卫上帝的启示不受任何政治权威的结构改变和功能利用的主权,批判宗教尤其是政治化的宗教(如‘日耳曼基督徒’)的敌基督本性,坚守上帝之国的公义就意味着必然要对世俗政治的不义进行批判。”[31] 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进行冷战时,西方的基督教会呼吁反对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他却能引导教会超越这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督教会既不要站在反对西方也不要站在反对东方的路上,只能走它们中间的路(walk between the two)。”[32] 遵循这条中间路,并不是折中主义的妥协,相反是一种不妥协,如同马克思主义强调要遵循社会存在来阐释意识形态问题,巴特强调基督教要遵循神学来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其神学政治的要义。
在神学政治的理想上,巴特借鉴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推动认信教会反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独裁,为教会和信徒争取自由而战。尽管借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不是他的神学终点,但对当时时局是迫切需要的。“基督教社团既能够也应当以最有益的形式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处境,支持这种或那种社会进步甚至是社会主义事业。但决定性言语不在社会进步或社会主义的宣言中,而在上帝革命(revolution of God)的宣言中,即反对人的一切亵神和不正义。”[33] 马克思主义并不让人亵神,也不让人不正义。在反纳粹暴政的特定时期,其革命观于基督教是最有益的。马库尔德分析巴特在此形势下而指出,“当务之急,却是改变的激进需要。……这样的情形使人明白,当马克思主义信条中的革命(revolution)绽放光芒时,自由将喷溢而爆炸。”[34] 在巴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将引导无产阶级去为解放和自由而战;在他所传道的认信教会中,无产阶级就是劳苦民众和穷人,而教会帮助其信众,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当时纳粹在德国进行恐怖独裁,以国家社会主义幌子来欺骗民众,此种时局很多教会都看不清。“巴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模式,把纳粹主义(fascism)评定为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必然和最终阶段,这对于常偏向德国国家主义的那些认信教会牧师来说,一定看起来特别奇怪。”[35] 其实,奇怪的不应该是那些倾向于德国国家主义的牧师,在那种高压和恐怖的历史处境中,一些教会和神职人员屈从于希特勒的淫威是事实。但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巴特铮铮铁骨中竟然活跃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激情,他的神学政治竟然采用马克思主义论证模式,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神学的作用,不得不探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我们当下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的指导意义。
2
承上所论,巴特从神学政治上吸收、模仿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事实,是促使巴特神学成为20世纪最深刻、最博大和最具影响的神学的原因之一。巴特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生活在冷战对立的冲突年代,而他敢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突破了传统神学的禁区,跨越了意识形态的樊篱,有一种非凡的勇气。其勇气根基于他的神学理论,突显其神学政治立场。“只有我们说称义为罪人(justified sinner)的理解上,我们才能说真正的宗教。”[36] 资本主义的剥削者甚至是偶像崇拜的基督徒,不称义为罪人,他们所宣扬的宗教就是假冒的宗教。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无神论者如马克思,猛烈批判资本主义拜物教偶像,却实质上捍卫了真正的宗教。就此,巴特用否定含义的虚拟语气句感叹到:“直面马克思(Marx),教会就会被促使展现在言语和行动中,就能展现:上帝的知识自动地和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从所有位格和偶像的自身解放中,它自身就能解放!”[37] 换言之,教会没有被促使展现在言语和行动中,也就没能展现基督教的真谛——上帝的知识,也就没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却获得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解放。敢如此论断是巴特的大勇,大勇之中有大谋。他的大谋,即他的大慧。可以说,巴特的神学智慧,汇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智慧,厚积薄发,成为了“它山攻玉”的典范。而我们今天身处和平时代,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我们如何借鉴当代西方神学的典范来深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让它发挥更大效应,来指导中国的宗教研究和宗教工作?
一是要扩大和深化与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巴特神学,的对话交流,使世界宗教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团结力量。有一种观点认为,基督教神学代表的只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要与之交流对话。从历史来说,基督教神学比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出现要早,它还经历了奴隶、封建社会的发展,说它仅仅代表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讲不通的。即使后来产生的一些基督教神学确实代表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正是这一形态上的交流更能增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实力。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无神论,就锯断了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应然联系。无神论和有神论,两者都是人类宗教思想认知的产物,没有有神论,便没有无神论,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应有这样的辩证理解:“‘神学’就广义而论是对‘神’这一问题的探究,无论‘有神’、‘无神’之论都是关涉对‘神’理解的‘神’论,是探究‘神’这一基本问题的‘学问’。”[38] 由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关于‘无神’的‘神’之解说和论述,尽管与基督教神学关于神的存在上有着相反的观点,但毕竟与基督教神学一样都是关于宗教这一人文知识的研究。如果我们纠结于“是否有神的存在”作为对话交流的前提,那么,就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简单化或僵化,将割断它与基督教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碰面与对话,这既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如同他之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基督教的继承者(inheritor)。……马克思主义注定体现了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革命,而基督教曾力图去实施,但失败了。”[39] 确实,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之中,这一点在过去中国学界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了。我们不能像在过去极左主义垄断下而形成这样片面的认识: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因而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是敌我对立。如果我们把两者关系当作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来思考,则这个问题更好理解,也是被历史所证实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科学是基督教世界分化造成的结果。宗教的相互容忍,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宽容的气氛,给科学成长带来了契机。”[40]
其实,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即使恩格斯也是花了五十多年的时间,直到晚年才彻底理清它们之间的合理关系。“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41] 恩格斯在这里分析出了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在压迫根源、斗争性、革命性和群众性等方面的共同,实质上指明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非必然的对抗性和矛盾性。“恩格斯对基督教有过系统研究,在批评基督教的同时,他对之亦有较为客观、积极、肯定的评价。其特点就在于恩格斯将基督教称为一种‘适应时势’的宗教,有其随着时代、历史的积极变化或变革的特点。”[42] 就此,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实质上可以对话交流,甚至可以联盟起来,因为它们本不是敌我关系,它们的真正敌人是资本主义。基督教作为能适应时势的宗教,其基本教义没变,何以能适应时势?关键是其神学,能顺应时代和历史而做出积极的构建。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历史选择和时代要求,尽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衰落。鉴此,我们应该对既适应时势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神学展开研究,特别是巴特神学。
巴特神学理论第一阶段被称为危机神学,在神学政治上借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反之,马克思主义可从政治宗教上审视巴特神学,它们共同目的就是反资本主义和战争独裁的军国主义。第二阶段所发展出的辩证神学,则精深奥妙,对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启发作用。此“辩证”所指并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它是指“人在迥然相异的上帝面前陷入不可避免且不可逾越之困境。”[43] 人难道不能通过心灵或经验到达对上帝的认识吗?“巴特描述上帝为完全的他者(Wholly Other),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期待和欲望。启示(Revelation)被理解为自上垂直而下,而不是从人类的宗教意识中出现。”[44] 巴特强调上帝与人之间有着无限的质的区别,因而人不能超越它。上帝的启示是上帝自身的行为,并不是人所自认为可把握的,以为人言可以理解上帝之道,这正是巴特要反对的。“巴特反对的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神学,同样也是主观主义(subjectivis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45] 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可借鉴巴特神学要义。虽然是人创造了宗教,但对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给予过度的乐观主义信赖,则会在处理宗教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上犯错误;从主观出发,不考虑西方宗教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则会在处理宗教的国际性问题上犯错误;从个人意志出发,不考虑中国宗教或民族文化的实情,则会在处理宗教的群众性和民族性问题上犯错误,凡此种种,均值我们警戒。
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指导中国的宗教工作,要永远服务于人民群众、服务于时代需要、服务于改革实践。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理论成果,并不是用来坐而论道的,我们对它的推行,关键是要培养服务意识和倡导实践行动。服务于人民群众,团结和帮助信教和非信教群众,这是巴特神学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后反馈给马克思主义宗教服务-实践观的。“积极地说,巴特很关心发展出一种社会性(social)和公众性(public)神学一般的神中心论(基督中心论和三位一体论)神学。从始至终,他的神学都是一种共享(communal)神学,神学和政治在他的思想中一直是密切联系的。”[46] 巴特神学的实践特色在于社会层面的服务,政治实践实质上是也就是神学实践,正如他所常说,“牧师就是为人民(the people)做事的人,……必须终止私有制(private property)!”[47] 借鉴于巴特神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根本上是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工作者,要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而不要只为当官的做事;要自觉抵制资本主义的诱惑侵蚀,从宗教的角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添彩增色。服务于时代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历史机遇和重任。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历史条件,解放前不同于解放后,文革前不同于文革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期,因而马克思主义宗教也就面临不同的历史机遇和重任,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当作一尘不变的教条,它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哲学指导思想,在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通过与巴特神学等基督教神学的交流对话,也应科学地看到人能力的有限性和理智的盲目性。在面对工业污染、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等棘手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拿起其批判的武器,从人文精神根脉上消除恶性变异的病因。要发挥其医护的功用,医治中国宗教及相关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标本都治,根叶皆护。当今中国信仰缺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宗教信仰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时,我们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信仰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怎样来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既然是信仰,那就应该是对人有终极关怀的,”[48] 确实,马克思主义信仰中的‘无私奉献’和‘理想正义’等,难道不可以激活我们时代的灵魂吗?服务于改革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今任务。中国的强大离不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服务于这场伟大的实践是应尽之责。概言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能指导中国改革实践中的宗教工作和研究,具体而言,我们的宗教工作和研究既能团结和凝聚各种积极的宗教力量,又能化解和清除各种消极的宗教力量。但问题还不仅是停留在一个层面,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宗教工作和宗教研究,如何破除我们自身的僵化和守旧的思想,以及如何防止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悄然引诱和侵蚀,这些都是改革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提出的严肃问题。常规来讲,主观思想往往滞后于客观实践,封建社会虽然早就被覆灭了,但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在一些人的灵魂中还是根深蒂固。鉴此,我们要长久不懈地破除僵化和守旧的思想意识以及防止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糖衣炮弹所击毙。大体上说,改革初期虽然有了破除极左宗教工作的实践,但极左宗教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例如把宗教看成反动势力和消极思想,把基督教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而在改革后期,虽然极左意识形态不太流行了,但真正的资本主义引诱和侵蚀却来了,表现为拜金主义、物质至上、唯利是图、享乐奢靡、权力寻租等。由此,马克思主义宗教工作者要极力防止这些糖衣炮弹,以实际行动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发展。
注释
[1]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Theological Audacities: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Andreas Pangritz and Paul S. Chung,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pp.115-116.
[2] Karl Barth, Against the Stream: Short Post-War Writings 1945-52. London: SCM Press Ltd 1954, p. 139.
[3]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Soci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unsinger,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p. 54.
[4]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Theological Audacities: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Andreas Pangritz and Paul S. Chung,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p. 243.
[5] 卓新平,《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4页。
[6] Karl Barth,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Lecture at Göttingen, Winter Semester of 1923/24. Edited by Dietrich Ritschl,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Limited 1982, p. 263.
[7]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8] 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Clifford Green (e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 14.
[9] Ibid., p. 329.
[10] Karl Barth,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Lecture at Göttingen, Winter Semester of 1923/24. Edited by Dietrich Ritschl,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Limited 1982, pp. 263-264.
[11] 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Clifford Green (e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 150.
[12] Timothy Gorringe, Karl Barth: Against Hegem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90.
[13] 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Clifford Green (e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 14.
[14] Ibid., p. 92.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页。
[1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ume Ⅲ,Part 2), H. Knight, G. W. Bromiley, J.K.S. Reid, R. H. Fuller (tr.); G. W. Bromiley, T. F. Torrance (ed.), Edinburgh: T & T Clark Ltd 1994, p. 389.
[17]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Theological Audacities: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Andreas Pangritz and Paul S. Chung,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p. 178.
[1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ume І), G. W. Bromiley (tr.); G. W. Bromiley, T. F. Torrance (ed.), Edinburgh: T & T Clark Ltd 1975, pp. 3-4.
[19] Ibid., p. 256.
[20] Gerald A, Butler, “Karl Barth and Political Theology” In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Volume 27, Issue 04, November 1974, p. 458.
[21]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
[22] 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Clifford Green (e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p. 104-114.
[23] Karl Barth,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Lecture at Göttingen, Winter Semester of 1923/24. Edited by Dietrich Ritschl,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Limited 1982, p. 263.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25] 巴特著,《罗马书释义》,魏育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5页。
[26]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Soci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unsinger,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p. 49.
[27] Ibid., pp. 58-59.
[28] Karl Barth, Against the Stream: Short Post-War Writings 1945-52. London: SCM Press Ltd 1954, pp. 244-245.
[29] 参见巴特的著作: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Church Dogmatics (Volume Ⅲ);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Lecture at Göttingen, Winter Semester of 1923/24; Against the Stream: Short Post-War Writings 1945-52.
[30]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Soci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unsinger,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p. 60.
[31]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
[32] 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Clifford Green(e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 317.
[33]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ume Ⅲ,Part 4), A.T. Mackay, T. H. L. Parker, H. Knight, H. A. Kennedy, J. Marks (tr.); G. W. Bromiley, T. F. Torrance (ed.), Edinburgh: T & T Clark Ltd 1996, p. 545.
[34]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Soci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unsinger,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p. 63.
[35] Ibid., p. 73.
[3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ume І,Part 2), G.T. Thomson, Harold Knight (tr.); G. W. Bromiley, T. F. Torrance (ed.), Edinburgh: T & T Clark Ltd 1994, p. 325.
[37] Karl Barth, “Ludwig Feuerbach” In Theology and Church: Shorter Writings 1920-1928, Louise Pettibone Smith (tr.), London: SCM, p. 234.
[38] 卓新平,《研究世界宗教 促进人类和平——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周年感言》,载《世界宗教研究》2014(3)第8页。
[39] David McLellan, Marxism and Religion: A Descrip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Christianity,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7, pp. 121-122.
[40] 赵立坤,《宗教文化与17世纪科学革命》,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第133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57-469页。
[42] 卓新平,《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宗教观》,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第2辑·201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
[43] 张旭,《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3页。
[44] 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Clifford Green (ed.),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p. 17.
[45] Ibid., p. 18.
[46] Ibid., p. 18.
[47]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Theological Audacities: Selected Essays, edited by Andreas Pangritz and Paul S. Chung,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pp. 142-151.
[48] 林学原,《高校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意识淡薄的现象与对策》,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第149页。
作者简介
李志雄,湖南湘潭人,文学博士,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理事。2004年至2007年在浙江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毕业,2006年雅典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西雅图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12年至2013年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就职于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已出版个人学术著作《亚里士多德古典叙事理论》一部,在Theology Today(A&HCI源刊)、 Utopian Studies、 Interfaith Insight、 Educational Journal、《外国文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学习与探索》和《基督教文化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多篇学术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共有著述九十多万字,翻译国外文艺理论著作二十万多字。主持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六项,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督教文化、比较文学和叙事学等方面的研究。
往期文章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巴特研究Barth-Studien
编辑:然而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Shooki、Lea等。
注: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