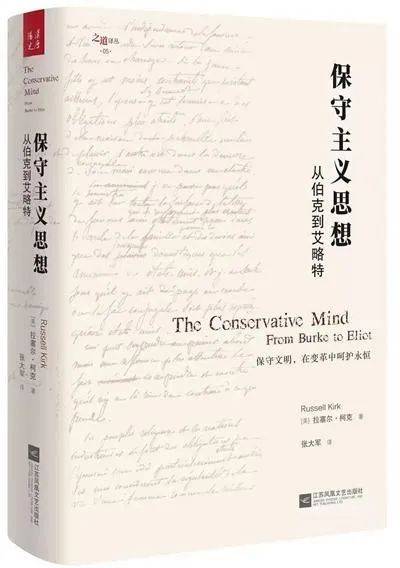
马洛克的目标是建立一套以科学为根据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声言对科学拥有独占权的激进分子们正捏造或扭曲统计数字以达到其目的;托利党人长时间以来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视通常会妨碍保守派人士以准确的统计数字回应错误的统计数字;在几乎得不到多数保守派领袖人物支持的情况下,马洛克自己着手纠正这一失衡问题。
几乎从一开始,保守派政党在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解上就差劲到可笑的地步。伯克熟悉这一问题的程度曾让人钦佩,皮特曾谙熟财政问题;不过,[除不适合做领袖人物的哈斯基森和海里斯(Herries)之外],从他们那个时代直到索尔兹伯里执政后期,经济学家一直都是自由派人士,而且自由派在这个领域多次让保守派一败涂地。
马洛克在1920年写道:“要系统陈述一种大众能够理解的、基于科学方法的真正的保守主义,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其中的难处。有系统阐释真正的普遍原则的难题。有的困难事关搜集并验证统计和历史事实,而且普遍原则必须与这些事实保持一致。有的困难在于将道德与社会情感和不可能被情感永久改变的客观环境协调起来。有的困难在于将许多事实分析从道德和理性上加以综合,而人类能够生存下去所凭据的就是这种综合;在慢慢地摸索到自己的道路以后,我现在试图说明这种综合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在这样做时,我感觉到,生活中的政治问题与通常所谓的宗教问题又重新合二为一了,而在我早年的时候,我的思想只关注后一类问题。”既然以前的自由派人士正败给社会主义理论,基于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就是人们所迫切需要的了。
马洛克说,保守主义以前的论证都过时了。其中的原因是,习俗性权利、传统的影响力、自古以来对财产和秩序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被卢梭之后的一波接一波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潮流破坏了。保守派无法再依赖那些古老的真理:我们的传统现在不得不被保护起来,不能再作为我们的屏障。意识形态、“科学”体系和统计方法被追求新花样者独占了。“所有与有条理的思想或体系沾点边的东西都属于攻击的那一方;而且除强力外,对它做出回应的唯有甚至都不能自圆其说的过时的教条主义。”坚称激进派的理论只会诉诸于嫉妒是没有用的,这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原因是,如果平等理论是对的,“我们必须将嫉妒视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正当合理的准则,正如虔信之人的敬畏被视为宗教生活中的正当合理的准则一样”。
因此,要解决的终极问题仅限于此:社会平等理论是对还是错?社会的完善需要平等——激进派人士这么说是对的吗?文明以及穷人会在平等实现时获益吗?进步与平等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马洛克在《社会平等》中给出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过,他的论证在《劳工与民众福利》(Labour and the Popular Welfare,1894年)一书中得到了强化。
当从科学的视角对其加以审视时——马洛克在所有政治论著中都是这么论证的,平等理论的谬误就显现出来了,因为平等意味着进步的死亡。通观历史,所有形式的进步——文化的和经济的——都是人们追求不平等的结果。如果取消了不平等的可能,一个民族只能一直处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惨淡凄凉的水平上,就像爱尔兰的农民;在认可了不平等之后,一小撮富有才干之人便将野蛮转化为文明。平等不利于任何人。它阻挠打击才智之士;它让穷人陷入更为可悲的贫困状态。在一个人口密集的文明国家,它意味着穷人几乎处于挨饿的状态。其中的缘由是,不平等会给文明共同体带来财富:它所提供的动因会引导具有超常才干之人竭尽全力为所有人谋利益。在当下这个时代,大约十六分之一的英国人带来了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
新集体主义者没能认识到超常才干的巨大价值,因为在社会平等的体制下,这些才干会受到抑制——这是为什么?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劳动财富理论(labor theory of wealth),而这种理论的基本原理又来自李嘉图。我们多数的财富并非源自劳动:仅仅劳动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人并非天生勤劳的动物:如果没有特别的刺激,他勤劳的程度仅限于能够让他维系生命。“劳动本身不是财富的源头,正如莎士比亚的笔不是其作品《哈姆雷特》的源头一样。源头在动因之中,而劳动是动因的外在指标。”首要的动因是不平等;而且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劳动,而是才干(Ability)。马洛克为杰出人才的重要性辩护,反对麦考利和斯宾塞。个人才华是一种惊人的社会力量;杰出人物的才干让穷人免于堕落到野蛮状态。以沉闷无聊的平等压制杰出人物或仅仅压制充满活力和才华横溢之人,就等于是在相应地压制普罗大众。
作为首屈一指的生产力要素,才干属于自然垄断之物:它不可能经由立法被重新分配,尽管它可能会被摧残。“才干是某种个体性的努力,而这种个体能够同时影响不定数量的个人的劳动,并因此加快或更好地完成不定数量的任务。”简言之,它是指挥劳动的能力;它会发明创造,设计方法,提供想象,组织生产、分配和防御,维系秩序。在文明国家,才干和劳动无法各自独立存在,因此人们无法十分精准地测算它们各自所创造的财富的比例;不过,在十三亿英镑的国民收入(1894年)中,劳动所创造的不超过五亿英镑,而至少有八亿英镑显然是才干的成果。没有才干的劳动不过是自然人为维持生存的原始劳作。由于认识到人类不可能单靠劳动繁荣昌盛,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便一直尽可能地通过保护其动因来鼓励才干。
被新集体主义者如此猛烈抨击的资本不过是所有社会的生产基金;它是智力(Intellect)对劳动的控制。为进步派人士所鄙视的财产继承权是才干最重要的动因之一,在满足遗赠财产的本能的同时,还储存积累了资本。借着承认才干应有的权利,社会便为劳工阶层争取到非常多的利益了,而仅凭劳动是绝无可能获得如此收益的。
在19世纪的前六十年间,劳工阶层的人均收入增幅非常之大,以至于到1860年时,它相当于1800年所有阶层的总收入——就好像英国1800年的全部财富都被劳工阶层瓜分了一样。而且这一进程一直在持续。1880年,仅劳工阶层的收入就等于所有阶层在1850年获得的收入。“这代表着一种进步,最想入非非的社会主义者连做梦都从来不敢如此许诺。”实际上,劳工阶层的财富不仅绝对值增加了,而且其所占比例也上升了;富人和中产阶级现在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以前低;这是因为劳动不再是简单的无技能的手工劳作,正获得专业能力并因此分享才干的报酬。
如果这一进程再持续三十年(马洛克说这话时是1894年),劳动者的收入最终将翻倍。然而,更为贫困阶层的一贯贪婪对进步构成了威胁。追求更大的繁荣符合人的天性,哪怕是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可是,如果这种想象中的繁荣是通过掠夺其他社会成员实现的,它会窒息才干,并很快导致普遍的贫困和最终的野蛮化。基于想象中的自然正义的绝对社会平等的诉求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具有类似毁灭性后果的是,通过废除君主制实现节约的目的,据说这样每年可节约一百万英镑——不过,这相当于每人只节约了不到六个半便士。“每个人为保留女王所花费的金钱少于为祝女王健康喝下的几杯黑啤酒的费用。”为了让劳动者节省六便士,新集体主义者准备废弃传统的英国政府体制,他们因此而犯下的错误的严重性不低于废掉才干的激励机制。
在《贵族与进化》(Aristocracy and Evolution,1898年)中,上述理论被用于管理事务之中。马洛克在开头部分写道,社会学家一般都忽略了天生不平等的事实。比以前更甚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相对来说很少的人掌控着经济的方向。我们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以及我们整个的生产体系需要由代表才干的少数人来引导。这既公正又得当。“进步派人士”愚蠢地贬低了坚强睿智之人在文明中的作用。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的大脑;作为大众自发产物的公共舆论从未存在过;我们所谓的公共舆论是围绕着杰出人物形成的。文明依赖于这些人士的鼓励与认可。普通人应被教导去改善他们的命运,而不是试图逃避命运。
民主体制展现出一种拒绝领导力的危险倾向——也即倾向于要求:管理重要事务的人应该“只在诸如实际行动能力和快速领悟其他人意图这些方面拥有与众不同的特质,此类特质将使得他们能够遵照他们的民众主人的命令去做事;不过,他们必须缺少思想或原创能力,这种能力可能诱使他们采取不合于他们主人当时脾性的行动或者他们主人理解不了的行动(这两者是一回事),即便此类行动可能是为了主人将来的利益”。如果废弃这种基于才干的、受到传统道德与政治体系约束的真正的领导力,那么,劳工阶层在经历过一个他们会像许许多多绵羊那样无能为力的恐怖间歇后,一定会屈从于新主子,而这些新主子的统治将比旧主子更加严厉,更加武断,更加残暴。
尽管我们的社会像所有文明的共同体一样,需要高尚的原则才能实现成功的管理,它依然是一个可以自由地结社和自愿行动的社会;对相对少数人的引领能力的需求并不会压制多数人。这是因为对才干的使用有充足的赏赐作为保障:在激励机制能够打动人的地方,强制是不必要的。费边主义者宣称他们已准备好取消这种自愿合作;相反,他们提到“公民义务的法则”,这一法则包含这样的内容:逃避责任者会受到惩罚。不过,尽管新集体主义也许能够靠工头的鞭子强迫人劳动,没有国家能够迫使才干发挥其天然的功能。受到胁迫的才干会沦落到简单劳动的水平;如果得不到奖赏,没有人会施展不同寻常的才干;西德尼•韦伯以经济上的奴隶制作为解决办法(费边主义者认为他们靠这种方法摆脱了匮乏的恐惧),实际上会导致所有人都永远处于匮乏状态。马洛克的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ism一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释,可能依旧是对集体主义问题的最透彻的剖析。
《纯粹民主的限度》(1919年)一书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综述了马洛克的社会理论。我们现代人的财富自19世纪初以来有大幅增加,创造这些财富的主要是引导性思维(Directive Mind);可是,引导性思维或才干拿到的报酬不超过这一财富增量的五分之一。人类不应抱怨引导性思维所得到的报酬,而应吃惊于那些报酬是如此节制。在政治和生产性事业中,少数人的权威并非源自任何单纯的法律上的认可,或者源自任何权利神圣的理论,而是源自造化(nature):现代的贵族或寡头体系是一种总体上有利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明国家,民众只有借助寡头们的合作才会有自知之明,……多数人能够兴旺发达的唯一途径是分享好处,而除非他们让自己屈从于超级能干的少数人的影响或权威,这些好处无论是物质享受、机会、教养或社会自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新集体主义先是摒弃这种正当合理的领袖人才,接着为应对它自己的失误,便会要求一位独裁者。在推行纯粹民主的俄罗斯会出现许多肮脏卑劣的新寡头,引领这些寡头的是一位暴君,那位暴君暗暗地否定了他借以崛起的那些理念,却仍继续向大众鼓吹“革命”和“民主”,与此同时,由于革命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无法忍受,必然会有针对新独裁统治的抗争,他进而又扑灭了这些抗争。
如果我们有勇气面对我们的难题,我们就有可能摆脱无神论和社会退化这双重威胁。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自己心里重新恢复那些并不真的有悖于、但超越于现代知识的宗教信念;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反击新集体主义者诉诸于嫉妒的做法,办法是说服普罗大众相信,社会的运行方式对他们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