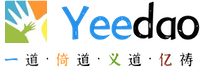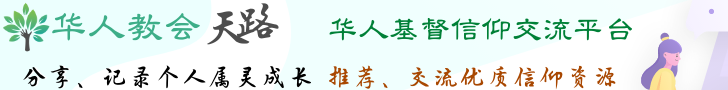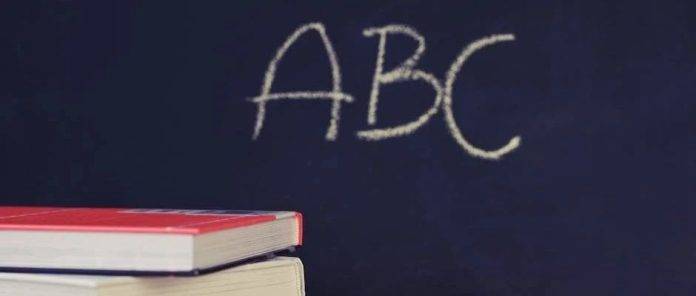最近,我在读一本教育学方面的书,其中有两段话让我很受提醒和触动:
“对于那些内心深藏‘称义靠信心,成圣靠行为’这种观念的学生而言,能够对‘称义’和‘成圣’稍有一些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我真的非常想赢得老师的称赞和同学的尊敬。就老师的称赞和同学的尊敬本身而言,这些都是美好的、值得追求的。然而对于我自己而言,我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却处在‘危险的悬崖边’。因为我想通过老师的称赞等这些东西告诉我自己——我是有价值的。结果就是,当我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时,就欢呼雀跃;而当没有好的成绩可言时,我开始怀疑是否有人在乎我,这其中也包括神。”
“……学生们需要一种无条件的爱,以帮助他们深知同时也深感他们在学校里是安全的,以至于在神的面前也是安全的。对于我而言,小时候这种不安的挣扎一直在我生命里持续,直到我进入一所基督教大学读书。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深深地相信我已蒙主救赎,是那被迁入‘爱子国度里的’。他给予了我归属感,而正是这归属感使我真正的得自由,使我全心地投入学习之中——并非为了能在这个世界中‘站立得住’,而是为了‘侍奉神’。”
这一章的标题是“由行为驱动的学生”,然而作为读者的我也深有同感。无论是学生时代还是参加工作,甚至现在的服侍,我的价值都建立在行为上,建立在社会、领导、朋友一层一层对我的评价上,于是如同文中所说,“我的自我身份认同感随时处在‘危险的悬崖边’”。行得好时,我会骄傲并轻看别人;行得不好时,我会焦虑难安,自我否定,生命实际活成了“靠行为”。
这样的我,在读到“学生们需要一种无条件的爱,以帮助他们深知同时也深感他们在学校里是安全的,以至于在神面前也是安全的”,不禁纳闷,我所面对的这一代——遇到困难习惯性躺平、自我要求不高、用舒适和玩乐包裹内心焦虑的孩子们,真的适合“无条件的爱”吗?
此刻我真的按捺不住想要挥起“律法主义”的大鞭,想要把这群“抱手躺卧”的孩子们抽醒,因为我就是如此对自己的。我不禁真的想问作者,你是否也观察到了新一代与我们的差别,并还能够坚持这无条件之爱、这安全感的主张呢?
我之前学过,也心里知道,反律法主义者与律法主义者,都出自“靠行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屡次失败,行为上做不到时,就如此定义自己,于是摆烂。实际上,躺平是最终的悖逆,摆烂是极致的任性。我与他们其实是“同路人”。
道理如此,但我却不理解孩子们,并且实际想不通:竟然不是律法的恐吓,而是恩典的托举,才能够叫醒躺卧的人。也许是因为,我仍然活在律法和行为深深的捆绑中,没有体会过恩典的大能。
行为的大鞭虽然好用,但却使人离神越来越远,我是否也处于遥远之中,看不清楚神了?求神拿去这深嵌入肤的捆绑,也不要让我去捆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