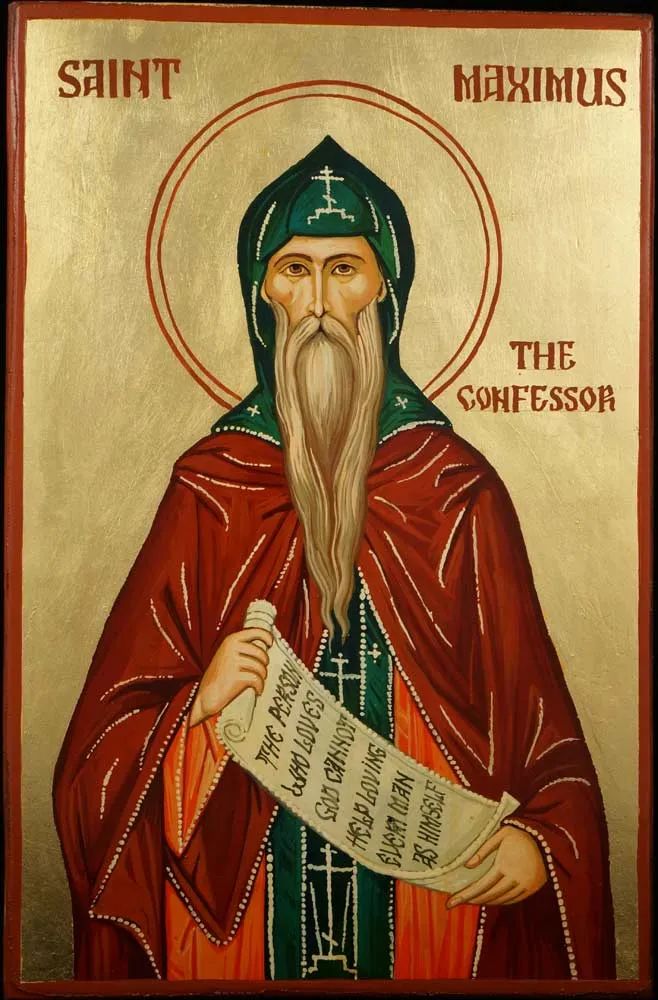如何理解罪的观念在巴特基督论中的作用?在本期推送的文章中,张少博老师认为,巴特在其神学论述中所要努力实现的就是彻底摆脱以现象中的人来定义人性的立场,从而将基督确定为定义人性的圭臬。巴特罪观的目的就在于对罪做出非实在性、非必然性的阐释。在巴特看来,罪所具有的仅仅是负面的特性,既欠缺必然性,又欠缺可能性;没有根据;不能被推论、被解释、或被解释为合理的;只不过是一件事实而已,但它仍是一件事实。巴特这样的罪观与东正教传统对于罪与堕落的理解恰恰相契合,他们的精神核心都是对罪的非实体性认定。
在张老师看来,这样的罪观将罪从人性中剥离出来,使其仅仅作为对人之存在的经验性判断,而非本体论判断。如此一来,这样的罪观可能为对人性做出积极论断留下充分的空间,并且可能会在基督教中国化以及中西文化会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原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3月,第48卷第2期,页75-83。推送时已获作者授权转载,并略有修订。特此感谢张少博老师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
摘要
巴特的罪观是其神学人论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其《教会教义学》中极为精彩的篇章。他从基督论视角出发,关注于罪的消除。对原罪做出异于西方神学传统的解释,剔除了罪的遗传性,将罪的本质归结为虚无,突出罪的非实体性。而这种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颇为独特的罪观却与东正教传统的罪观内在相通,并且由此推论出的人性论也迥异于为汉语世界所熟知的传统西方基督教所持的人性败坏说。
关键词:巴特 原罪 虚无 东正教
罪的概念在基督教神学以及信仰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在世人对基督教的了解中可算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为基督宗教作为一种救渡宗教,其根本宗旨就是对罪者的救赎。整个《圣经》叙事也把对人之罪的记叙安排于紧随“上帝创世”之后,亚当夏娃的犯罪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再加上在信仰实践中基督徒大多以罪者自居,以至于罪成为大众看待基督宗教信仰的重要标签。所以,关于罪的论述可以说是基督教教义学不可缺失的一环。历史上每一位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都会留下自己对罪的论述,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自然也不例外。
巴特对于罪的论述在其巨著《教会教义学》中毫无疑问具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与传统系统神学中罪[论]所扮演的结构角色一样,巴特对罪的论述使得在《教会教义学》第三卷展开的神学的人论(theological anthropology)与第四卷《和解论》中重点论述的救赎论能够有机地关联起来。第二,巴特本人对罪的论述采取了一条与传统西方神学大相径庭的进路,他并未为罪专门开辟章节进行论述,而是将其穿插在人论与救赎论当中。并且,巴特没有围绕《创世记》中亚当堕落故事展开论述,而是另寻着眼点,勾勒出一个与以往西方基督教神学迥然相异的罪的模式,使得罪论成为《教会教义学》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从基督论的视角出发,是巴特神学中罪论的基本导向,也是最大特点。巴特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以基督为起点来安排关于罪的论述颇显异类。但是,巴特相信,就是他这种异类的论述才最忠实于上帝在基督中的救赎事工。为此巴特说道:“如此要慎而又慎,因为我们所走的路是前人不曾走过的;但是我们异常坚决,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并无路可走。”[1](p. 397)
正如汤普森在其关于巴特基督论的研究专著《展望基督》一开篇所说的,巴特在其著作中从没像传统系统神学著作那样有独立章节专门论述基督论,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他的著作又处处皆是关于基督论的讨论,每一个神学论题当中都有基督论的影子,谈论每一论题都不能离开基督论的基础,并且要根据其与基督论的关系展开论述,这就是巴特神学中“基督中心论”的表现。
当然,这种“基督中心论”的表现也存在于巴特对罪的论述中,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巴特对各个神学论题的论述中基督论都具有基础性作用,还因为巴特的整个人学基调都是由基督论所决定的。正如赖品超所指出的“依巴特,耶稣基督是神学的人观(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的基础。”[5](198页)只有从基督那里,才能获得关于人之罪的知识。
具体分析基督论在巴特罪论中的所起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即:以基督论为坐标,巴特区分出了现象中的人与真正的人。所谓现象中的人,即是指在一般经验中所直接观察到、体验到的人;而真正的人即是从上帝的视角出发、从基督的人性出发所认识的人。巴特在其神学论述中所要努力实现的就是彻底摆脱以现象中的人来定义人性立场,确立以基督为定义人性的圭臬。由此类推,人之罪也是要由基督来定义,而其理由就在于,“只有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人是罪人,而罪又是什么、以及它对人的意义。”[1](p. 389)分析这一理由,其中包含了两方面含义:第一,只有对照着耶稣基督,人才能发现自己身上的罪;第二,也只有对照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清罪对于真正人性的无力。
关于第一个方面,巴特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对罪的论述是关于信仰的论述。而作为关于信仰的论述,我们就无法抛开上帝和基督来讨论罪。只从人自己出发,仅仅通过自我反思、以及与同伴的交流,我们无法获得对罪的认识,这就像通过同样的方式我们无法了解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一样。[1](p. 360)虽然,客观上讲,人是能够认识到人自身的有限、不足与不完善性,但是,此类认识还远不能构成对人作为罪人的认识;反之,正因为我们是罪人,才阻碍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罪。
而要想跳出罪人身份对我们关于罪的认识问题上设置的藩篱,在巴特看来就只有在圣言的关照下,人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那极端且彻底的自我矛盾,也只有在这一关照下人才能超出这种自我矛盾,看到他的受造本质及存在。因此,巴特没有如流俗的系统神学那样,从《创世记》中的亚当之罪开始展开对罪的论述,而是在《教会教义学》的第四卷《和解论》中,分别对照耶稣基督的三重职事,即祭司、君王、先知,分三大段来细述人之罪。它们分别是第四卷第一部第60章,“论骄傲”;第四卷第二部第65章,“论怠惰”;第四卷第三部第70章,“论虚假”。

巴特所论人的骄傲,是以上帝的俯就和谦卑为参照系来审视人类。在此关照下所展现出的人之罪就是骄傲。对此,巴特从四个角度来呈现人的骄傲:当神已成为人类中的一员时,人自己却还想成为神;当神已成为仆人时,人自己却还想成为主;当神使自己接受审判时,人自己却还想成为审判者;当神为了扶助人类而自我倾空时,人自己却还想一切全凭自力。
至于怠惰,则是对照在耶稣基督中与上帝实现和解并得到提升的人性,人类表现出的怯懦、庸碌之罪便是怠惰。与骄傲类似,巴特同样分四个方面阐述怠惰:愚昧,即无视在基督中启示出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冷酷,即自我孤立并对他人保有敌意;放纵,即忽视灵魂对身体的意义,只作为无灵之肉存在;焦虑,即抛却上帝的恩典,总要试图主宰自己生活所带来的烦恼。
最后,人的虚假则是对照耶稣作为先知的职事所犯之罪,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为上帝之言做真见证,而人总是回避那作为自己根基的真理。
由巴特对人的三种罪的分析可以看出,巴特不仅仅是分类厘清人具有之罪,而是将罪置于拯救论的脉络中来考察。从拯救论的视角来考察罪,我们的目的就不能停留于通过考察人之罪来认清人,而是要认清人何以能够得救。以此,我们所追问的就不再仅仅是“罪是什么?”,而是“罪对于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不特如此,还是针对“要获得拯救的人”来讲罪意味着什么。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只有对照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清罪对于真正人性的无力。
诚然,只有对照着基督的人性,人才能发现自己所犯之罪;而另一方面,也只有对照着基督的人性,我们才能在对罪有认识的情况下,将罪人的存在状态认作是人之所是。人不应首先被视为罪人,因为在创世中,上帝创造的是人而不是罪人。如果罪性就是人之本性,那人从上帝那里就只能得到诅咒,而没有恩典。因此,决不能以现象中的人之罪来定义人性,作为罪人的人类仍然首先是上帝的造物。
“我们不能忘记,即使作为罪人,人也仍然是上帝的造物。如果他的本性完全受堕落这一事件的影响,这影响也只能是在内在产生冲突,但其本性是不会因此被抹杀的,他无法摧毁自己的本性,让自己变得完全不真实。人在生存中的扭曲、堕落与人性的彻底湮灭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因此,我们不能说罪人不再作为上帝的造物而存在。”[2]( p. 27)
这就是巴特论罪的最大特色,“简言之,巴特对罪的关注是集中在罪的被除去”,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下面便进入巴特论罪的最为精彩的部分,即他关于原罪和罪之本质的论述。

原罪教义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体现西方基督教精神的代表性教义。但是在巴特的神学思想中,有关原罪的论述却展现出独特的风采,迥异于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为了说明巴特所论原罪的特殊性,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传统的原罪教义。
论及原罪这一教义不得不谈及奥古斯丁,因为神学史上奥古斯丁是最早系统论述原罪思想的神学大家。奥古斯丁的原罪教义是他在反驳英国教士佩拉纠(Pelagius, 390-418)的救赎学说过程中形成的。在其《论美德与罪之得恕》(De PeccatorumMeritis Et Remissione)中,奥古斯丁针对佩拉纠对原罪与给婴儿施洗的拒斥做出激烈回应。他指出,从对婴儿施洗可以得出两个关于事实的真命题:1、所有人都因罪获疚(all are guilty of sin);2、但是任何实际的罪都无法归于婴儿。根据这两个同时为真的命题,奥古斯丁进而推定出,人类是生而有罪的,而这个与生俱来罪就是原罪。关于原罪的具体性质,奥古斯丁的定义为邪欲(concupiscence)。这种邪欲并不会因受洗而去除,它仍然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需要受洗者予以抗争,因为它破坏了人之内在本有的正当秩序。尤为重要的是,当然也是原罪教义的最突出特征,奥古斯丁认为,这一邪欲是具有遗传性的,这是对人类最初的始祖所犯下罪行的惩罚,并且通过肉体行为将邪欲传递给后代的子孙,使得其在人类中蔓延、保留下来。虽然后世神学家关于这一教义的具体论述都略有差异,但基本没有背离奥古斯丁的经典论述。
 至于巴特对原罪的论述,首先从整体来看,有关原罪的讨论在巴特的整个《教会教义学》中并不占有十分突出和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已经为不少巴特研究者所指出,[①] 而究其原因,根据韦伯斯特(John B. Webster)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巴特主要关注的是所谓“基督之后”(post Christum)的罪,而对始祖之罪的讨论则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而处理的具体方式就是我们上面所论述的从基督论视角出发的方式。所以,只有与“第二亚当”相关时,原罪问题才会进入巴特的视野,只与“第一亚当”相关的方面巴特便不会多谈。其二,巴特在注意强调罪在基督中被摧毁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阐明罪对于人类的现实性。也正因为这一点,遗传之罪的概念使其颇感不适。他极为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不承认人的自我选择会招致人的毁灭。[6](p. 67) 在巴特看来,人的意志选择与行为都会对人造成实际的影响,“我们即是我们所意欲的;我们即是我们所行事的”[3](p. 793),这就是罪的现实性所要传达出的具体含义。但是,原罪的遗传性却会造成一种对罪的命定论的阐释方式,从而消除掉人的意志与行为这两个重要因素所具有的影响。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二个方面极为重要,因为这是造成原罪教义在巴特神学中不具有重要地位的关键因素,也应成为我们理解巴特有关原罪教义观点所需把握的主线。
巴特对原罪的讨论出现在《教会教义学》第四卷第一部六十五章第三节——“人的堕落”。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在这里并不是直接点明原罪这一概念,进而展开论述。巴特采取了一种迂回的论述方式,他的切入点就是本节的标题,人的堕落问题,而且具体化到“人的彻底堕落”(total corruption)这一概念:“我们正在处理的不仅仅是随意一种堕落,而是最为极端的堕落。而这最极端的堕落就是一个人出于对恶和自我骄傲的效命,从而将自己的本性和出于本性的一切行为都出卖掉,并使之被奴役。”[1](p. 497)
就是在这里,巴特将自己所论述的内容与古老的原罪概念联系起来。巴特明确指出,原罪“虽然与特殊的特别行为确实相关,但是其首先是相关于作为整体的人的生命,相关于其行动在时间的由始至终整个跨度中所具有的特性”[1](p. 499)。巴特对原罪的定义格外突出这种堕落和被恶所奴役的状态,他认为原罪这个概念“充分地向我们传达出一个讯息,即我们所应对的是人类原初的、极端的,同时也是全方位的、全部的行为;我们应对的是人之实存受困于邪恶存在与邪恶行为之间的相互循环。”[1](p. 500)这也可以被视作是巴特对传统原罪概念的解读。
除此之外,关于原罪概念巴特着重讨论了另一方面,即自奥古斯丁以来在原罪概念中一直保有的“遗传”属性。对此,巴特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明确批判“遗传之罪”的概念。巴特说道:“在早期教会,原罪……被称作为遗传之罪。这种观点认为,亚当的罪是极其严重的,并对其所有后继者有着完全的决定性,它通过生殖传递给后代,这就像一种属灵的疾病,并且成为他们存在的基本预设。……毫无疑问,关于一种通过生殖方式传递给人的遗传之罪的观念是极其可悲和错误的。……生殖如何能够成为罪在前人与后代之间传递的媒介呢?这样的一种媒介就没有任何问题吗?”[1](p. 500)由此可见,原罪与遗传之罪的纠缠不清和不可分割,是巴特对传统原罪教义最为不以为意指之处。而比照巴特这前后两种关于原罪一正一反的观点,我们就能看出,巴特之所以要极力摒弃遗传之罪的概念,主要原因就在于遗传的概念对罪与意志之间的联系造成了障碍。“我作为一个接受遗传者所做的事,并不是我所能拒绝的,因为我并没有被问询是否愿意接受。只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才可以说,这样所做的事是属于我自己的行为。我可以承认这是我的命运,但绝不承认或认为我对此负有责任”。[1](p. 500)很显然,在巴特的论述逻辑中,遗传性与罪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当遗传的概念被严肃对待时,罪的概念必然会被消解。反之,当罪的概念被严肃对待时,遗传的概念必然会以某种阐释方式隐匿起来,或明或暗地消解,抑或被其他概念替代。”[1](p. 500) 罪的归咎必须依循“是否故意”这一原则,即意志原则,因为罪归根结底是一种行为;而将罪与遗传的概念相联系,在实质上就是以“自然主义、决定论,甚至宿命论”来消解意志与罪之间的联系,使罪变为无责可究的事实。因此,巴特提出完全以德文Ursünde(原初的罪)来表述原罪这一概念,从而废除Erbsünde这个具有遗传含义的词对原罪的表述。
作为这一思路的延伸,巴特对亚当之罪的处理便不是将其视为一件史实,而是更多的视其为一个传说。传说不是虚构,它也是一种历史叙事,只不过这种叙事形式“是以直观和想象的手法,在所述之事不具有作为历史证据的敏感性时,做出的历史叙事。”[1](p. 508) 作为传说的亚当,他便不是将罪引入人间的先祖,不是现实中罪的开端,我们不能认为其“与历史考古学有任何正相关或负相关”,或将其“与我们所确知的历史上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生命形式相联系”。[1](p. 508) 他是一个原型,代表着一类犯罪的模式。用巴特的话讲就是,“上帝给世界-历史这一整体冠以犯罪者——亚当之名。”[1](p. 508) 作为历史的亚当虽然与作为传说的亚当对原罪都有解释的功用,但是,两者阐释的结果则完全不同。以作为历史的亚当来解释原罪,就如同根据线索查出了一桩案件的元凶,正是他发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导致我们所发现的“案发现场”,这种解释的本质是为了说明因果关系。而以作为传说的亚当来解释原罪,其本质是以亚当为具体模型,借用他的故事来阐明犯罪的原则,并通过这一基本原则去揭示罪的本质。
重视作为传说的亚当,从巴特思想的全局来看其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巴特的罪论与人论都是以基督论为基本导向的,所以,巴特的解释自然与传统西方神学中对待原罪的方式会有显著不同。传统上对原罪的处理“会很典型地将亚当在堕落之前的本性纳入思考的范畴,其基础是按字面解经法将亚当视为人之始祖”。[7](p. 458) 与此相对,在巴特的论述中,有关人性的讨论则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展开的,所以从亚当的堕落引出的关于人性变化的论题便不在巴特的论述议程中出现。正因为这样,亚当之罪才能够不以核心论题的身份出现在《教会教义学》涉及罪的篇幅中,巴特也才能放开手脚,以一种“唯意志论”(J.韦伯斯特语)的方式来解读原罪,从而抛弃传统由“遗传之罪”与“邪欲”确立的既定套路。
将原罪等同为意志的一种存在状态或行事状态,其实只是对罪的实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但巴特使用“唯意志论”解读方式的目的在于,凸显罪对于意志的依附性,这里关注的点在于“依附性”而不是“意志”。此外,凸显罪对意志的依附性也意味着,摆脱罪的束缚也取决于意志自身。正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罪的胜利不是靠别人实现的,不是被动消极的从上帝手中接过胜利的果实,而是要振作起来,重拾人自己的行动力与自由。”[6](p. 76)
巴特对原罪“意志论”式的解读可以视作是巴特从正面出发,针对罪的积极方面最初的阐释;而关于罪之“缺失”的[另]一面、消极一面的阐发则是通过罪之本质的论述完成的。相比于对罪做出骄傲、怠惰、虚假三方面分析、以及对人之原罪的解读这些极具特色的论述,巴特神学中“罪观的更大特色”,便“是对罪的本质的本体论分析”,而他的分析中核心的观点就是突显“罪的虚无性、偶然性及寄生性。”[5](201页)。
其实,对罪的积极方面的解读与对罪的消极方面的解读是紧密联系的,它是从另一个侧面服务于对罪之本质的揭示。将原罪做唯意志论的解释,否定其遗传性,认定罪是出于人的行为及意志,将罪剔除出人性,这就意在说明,罪是附着在人的行为及意志之中,是寄生性且并无自性的。而直接点明罪的虚无性,那便是直面罪的本质了。
至于巴特对原罪的论述,首先从整体来看,有关原罪的讨论在巴特的整个《教会教义学》中并不占有十分突出和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已经为不少巴特研究者所指出,[①] 而究其原因,根据韦伯斯特(John B. Webster)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巴特主要关注的是所谓“基督之后”(post Christum)的罪,而对始祖之罪的讨论则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而处理的具体方式就是我们上面所论述的从基督论视角出发的方式。所以,只有与“第二亚当”相关时,原罪问题才会进入巴特的视野,只与“第一亚当”相关的方面巴特便不会多谈。其二,巴特在注意强调罪在基督中被摧毁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阐明罪对于人类的现实性。也正因为这一点,遗传之罪的概念使其颇感不适。他极为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不承认人的自我选择会招致人的毁灭。[6](p. 67) 在巴特看来,人的意志选择与行为都会对人造成实际的影响,“我们即是我们所意欲的;我们即是我们所行事的”[3](p. 793),这就是罪的现实性所要传达出的具体含义。但是,原罪的遗传性却会造成一种对罪的命定论的阐释方式,从而消除掉人的意志与行为这两个重要因素所具有的影响。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二个方面极为重要,因为这是造成原罪教义在巴特神学中不具有重要地位的关键因素,也应成为我们理解巴特有关原罪教义观点所需把握的主线。
巴特对原罪的讨论出现在《教会教义学》第四卷第一部六十五章第三节——“人的堕落”。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在这里并不是直接点明原罪这一概念,进而展开论述。巴特采取了一种迂回的论述方式,他的切入点就是本节的标题,人的堕落问题,而且具体化到“人的彻底堕落”(total corruption)这一概念:“我们正在处理的不仅仅是随意一种堕落,而是最为极端的堕落。而这最极端的堕落就是一个人出于对恶和自我骄傲的效命,从而将自己的本性和出于本性的一切行为都出卖掉,并使之被奴役。”[1](p. 497)
就是在这里,巴特将自己所论述的内容与古老的原罪概念联系起来。巴特明确指出,原罪“虽然与特殊的特别行为确实相关,但是其首先是相关于作为整体的人的生命,相关于其行动在时间的由始至终整个跨度中所具有的特性”[1](p. 499)。巴特对原罪的定义格外突出这种堕落和被恶所奴役的状态,他认为原罪这个概念“充分地向我们传达出一个讯息,即我们所应对的是人类原初的、极端的,同时也是全方位的、全部的行为;我们应对的是人之实存受困于邪恶存在与邪恶行为之间的相互循环。”[1](p. 500)这也可以被视作是巴特对传统原罪概念的解读。
除此之外,关于原罪概念巴特着重讨论了另一方面,即自奥古斯丁以来在原罪概念中一直保有的“遗传”属性。对此,巴特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明确批判“遗传之罪”的概念。巴特说道:“在早期教会,原罪……被称作为遗传之罪。这种观点认为,亚当的罪是极其严重的,并对其所有后继者有着完全的决定性,它通过生殖传递给后代,这就像一种属灵的疾病,并且成为他们存在的基本预设。……毫无疑问,关于一种通过生殖方式传递给人的遗传之罪的观念是极其可悲和错误的。……生殖如何能够成为罪在前人与后代之间传递的媒介呢?这样的一种媒介就没有任何问题吗?”[1](p. 500)由此可见,原罪与遗传之罪的纠缠不清和不可分割,是巴特对传统原罪教义最为不以为意指之处。而比照巴特这前后两种关于原罪一正一反的观点,我们就能看出,巴特之所以要极力摒弃遗传之罪的概念,主要原因就在于遗传的概念对罪与意志之间的联系造成了障碍。“我作为一个接受遗传者所做的事,并不是我所能拒绝的,因为我并没有被问询是否愿意接受。只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才可以说,这样所做的事是属于我自己的行为。我可以承认这是我的命运,但绝不承认或认为我对此负有责任”。[1](p. 500)很显然,在巴特的论述逻辑中,遗传性与罪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当遗传的概念被严肃对待时,罪的概念必然会被消解。反之,当罪的概念被严肃对待时,遗传的概念必然会以某种阐释方式隐匿起来,或明或暗地消解,抑或被其他概念替代。”[1](p. 500) 罪的归咎必须依循“是否故意”这一原则,即意志原则,因为罪归根结底是一种行为;而将罪与遗传的概念相联系,在实质上就是以“自然主义、决定论,甚至宿命论”来消解意志与罪之间的联系,使罪变为无责可究的事实。因此,巴特提出完全以德文Ursünde(原初的罪)来表述原罪这一概念,从而废除Erbsünde这个具有遗传含义的词对原罪的表述。
作为这一思路的延伸,巴特对亚当之罪的处理便不是将其视为一件史实,而是更多的视其为一个传说。传说不是虚构,它也是一种历史叙事,只不过这种叙事形式“是以直观和想象的手法,在所述之事不具有作为历史证据的敏感性时,做出的历史叙事。”[1](p. 508) 作为传说的亚当,他便不是将罪引入人间的先祖,不是现实中罪的开端,我们不能认为其“与历史考古学有任何正相关或负相关”,或将其“与我们所确知的历史上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生命形式相联系”。[1](p. 508) 他是一个原型,代表着一类犯罪的模式。用巴特的话讲就是,“上帝给世界-历史这一整体冠以犯罪者——亚当之名。”[1](p. 508) 作为历史的亚当虽然与作为传说的亚当对原罪都有解释的功用,但是,两者阐释的结果则完全不同。以作为历史的亚当来解释原罪,就如同根据线索查出了一桩案件的元凶,正是他发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导致我们所发现的“案发现场”,这种解释的本质是为了说明因果关系。而以作为传说的亚当来解释原罪,其本质是以亚当为具体模型,借用他的故事来阐明犯罪的原则,并通过这一基本原则去揭示罪的本质。
重视作为传说的亚当,从巴特思想的全局来看其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巴特的罪论与人论都是以基督论为基本导向的,所以,巴特的解释自然与传统西方神学中对待原罪的方式会有显著不同。传统上对原罪的处理“会很典型地将亚当在堕落之前的本性纳入思考的范畴,其基础是按字面解经法将亚当视为人之始祖”。[7](p. 458) 与此相对,在巴特的论述中,有关人性的讨论则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展开的,所以从亚当的堕落引出的关于人性变化的论题便不在巴特的论述议程中出现。正因为这样,亚当之罪才能够不以核心论题的身份出现在《教会教义学》涉及罪的篇幅中,巴特也才能放开手脚,以一种“唯意志论”(J.韦伯斯特语)的方式来解读原罪,从而抛弃传统由“遗传之罪”与“邪欲”确立的既定套路。
将原罪等同为意志的一种存在状态或行事状态,其实只是对罪的实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但巴特使用“唯意志论”解读方式的目的在于,凸显罪对于意志的依附性,这里关注的点在于“依附性”而不是“意志”。此外,凸显罪对意志的依附性也意味着,摆脱罪的束缚也取决于意志自身。正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罪的胜利不是靠别人实现的,不是被动消极的从上帝手中接过胜利的果实,而是要振作起来,重拾人自己的行动力与自由。”[6](p. 76)
巴特对原罪“意志论”式的解读可以视作是巴特从正面出发,针对罪的积极方面最初的阐释;而关于罪之“缺失”的[另]一面、消极一面的阐发则是通过罪之本质的论述完成的。相比于对罪做出骄傲、怠惰、虚假三方面分析、以及对人之原罪的解读这些极具特色的论述,巴特神学中“罪观的更大特色”,便“是对罪的本质的本体论分析”,而他的分析中核心的观点就是突显“罪的虚无性、偶然性及寄生性。”[5](201页)。
其实,对罪的积极方面的解读与对罪的消极方面的解读是紧密联系的,它是从另一个侧面服务于对罪之本质的揭示。将原罪做唯意志论的解释,否定其遗传性,认定罪是出于人的行为及意志,将罪剔除出人性,这就意在说明,罪是附着在人的行为及意志之中,是寄生性且并无自性的。而直接点明罪的虚无性,那便是直面罪的本质了。

在巴特的论述中,罪是虚无(nothingness)的“具体形式”,虚无是罪的本质。不过,巴特所使用的“具体形式”需要给予解释。在巴特这里,说罪是虚无的具体形式,并不意味着虚无是罪的一般形式,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具体表现和抽象本质之间的关系,罪不是作为一个仅能体现其本质一部分性质的碎片存在着,两者间的关系并不像一个单个具体的人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根据科罗特克(Wolf Krötke)的总结,在巴特的论述中,虚无指的就是圣经中所提到的违逆上帝意志,并企图奴役人类,被称为“仇敌”的邪恶力量,而这个作为邪恶力量的虚无在产生作用时有一个特点:在它敌对上帝和上帝的造物时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即基于它所面对不同对象它会相应的具有不同的形式。死亡、恶、以及罪都是虚无产生作用时采取的具体形式。[8](p. 20)
虽然不同的形式所具有的作用会有不同,但是,每一个具体形式都是虚无的整体在场。所以,要想追问虚无的真相,就不能通过对罪的考察进而抽象出其本质的方式。相反,对罪的终极定性要以对虚无的认识为基础,因为罪就是虚无的一个化身,它所拥有的特性就是虚无所拥有的。
至于虚无的本质,巴特有专门的论述。对虚无的理解绝不能仅仅从字面出发,想当然地将其等同于非存在。巴特说过:“真实的邪恶,真实的死亡,与真实的罪一样存在着。”[4](p. 310) 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巴特的论述中,虚无所指即是对上帝的违逆和敌对。它不是上帝的造物,不属于存在,同时它也不是存在的简单对立面——非存在(non-being)。对于它的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存在(being)-非存在(non-being)构成的本体论结构中。要想正确把握虚无的本质,我们要领会巴特“不可能的可能性”(impossible possibility)[4](p. 351)这一命题的含义,并且要有效地区分非存在与虚无。
有效地区分非存在与虚无,首先要正确地理解非存在。非存在的含义并没有什么奥秘,它并不是指存在的湮灭,或某种对于存在的威胁,它仅仅是与存在这个“正项”相对应的“负项”,是完全中性的。相对于存在,非存在所指的即是不存在、没有存在者存在,同时它又是按照上帝意志可被存在充满的,是上帝“从无中创有”(creation ex nihilo)中的那个“无”。它与存在的关系,恰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句名言所说:“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两者是一种共存的关系,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并且共同构成了上帝创世的本体论结构的基底。正如巴特所说“一切源于上帝的存在者都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复合物。”[4](p. 332)
至于虚无,则既不能归于存在,也不能归于非存在,它是完全与这一切相对立的。借用科罗特克的话就是:“它全然抽身于一切本体论的辩证之外。”[8](p.48)所有受造物都是因上帝的恩典而获得各自的存在,而整个受造界获得存在的过程就肇始于上帝对此所言之“是!”(Yes!),而虚无所敌对的就是上帝发出的“是”,它并不仅仅否定具体受造物的存在,它是在整个受造界的本体论根基上威胁一切存在。“虚无就是那上帝将自己与之隔绝的,就是上帝在做出自我确认、发挥它的积极意愿是所针锋相对的……它绝不会作为神圣行为的对象而实存或被认知……而只能在上帝的左手边,处在上帝的‘不’之下,被上帝施予警戒、愤怒以及审判”,它排除在上帝建立的本体论结构之外,“作为一种内在矛盾,作为不可能的可能性,以它自己怪异的方式存在着。”[4](p. 351)
除了以虚无作为自己的本质外,罪的虚无性还体现在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当中。首先,在耶稣的死亡中,上帝的独子替代了罪人,与“那‘不’的力量”[1](p. 247)直接对峙。在这一对峙中,因为圣子之死,上帝将自己带入到了虚无的幻灭之中。不过,这一死亡是上帝可以承受的,不但如此,通过将自己交付给死亡,上帝使得虚无的意愿与自己的意愿合一,即“当撒旦的意愿成就时,上帝的意愿也得以成就。”[1](p. 268)
当然,虚无总是企图悖逆、僭越上帝的,但是,上帝完全掌控着与虚无的这场征战。在虚无将上帝拖进幻灭之前,上帝剥夺了这一可能性,抢先自行进入那幻灭之中。而就是通过这抢先一手,上帝釜底抽薪般将死亡的权柄剥夺。上帝对自己说出的“不!”,正是虚无想要对上帝说出的,而将上帝拖进幻灭则是虚无所渴求的最高目的。但是,上帝的自我弃绝使它永远无法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彻底摧毁了其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也正因虚无的否定力量被褫夺,人类才能够重新获得生命。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死亡中解除了人类的罪者身份,为人类获得全新的存在创造了空间,并使其有机会去兑现与神订立的[盟]约。“在耶稣的受难中所发生的即是神与人之间完全的和解,一切又都重新归于安宁。”[3](p. 290)
总结上述巴特所论述的罪的本质、罪在耶稣基督中的被克服、以及罪对于人的意志与行为依附,我们可以看出,巴特论罪的目的就在于对罪做出非实在性、非必然性的阐释,在巴特看来罪“所具有的仅仅是负面的特性。它既欠缺必然性,又欠缺可能性。它没有根据。它不能被推论或被解释或被解释为合理的。“它就只不过是一件事实而已。但它仍是一件事实。”[1](p. 419)虽然是一种不能被否认的存在,但在上帝面前,罪不过是一种没有力量的存在而已。
巴特对于罪的论述在西方神学传统中确实是独树一帜,他极大改变了以往神学中罪的概念给人的刻板印象,令人耳目一新。当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巴特在整个西方神学传统中,特别是新教传统中显得甚为异类。但正是这种在自身传统中的异类性使得巴特的罪论与东正教神学传统的罪观颇有灵犀,而这两者的比较则会使我们在更深、更高层面理解基督宗教的人性思想。首先,我们通过列举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东正教思想家的观点,对东正教的罪观做一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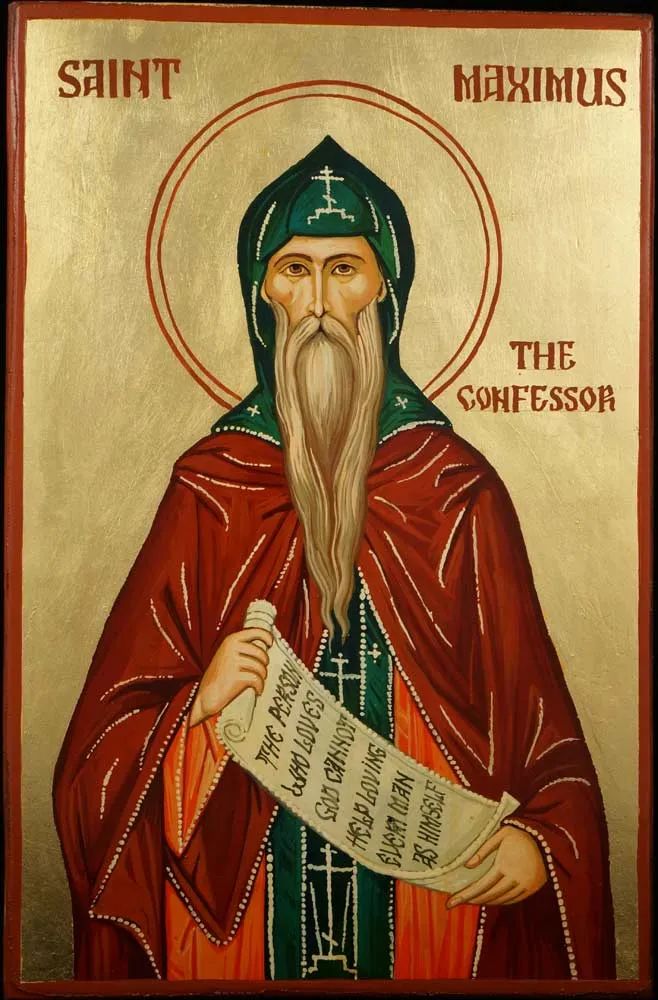
Maximus the Confessor
第一位是宣信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 580-662)。作为“拜占庭神学之父”,他的许多论述都为后世神学家所继承。在人的堕落与犯罪问题上,马克西姆认为,这是由魔鬼的引诱与人接受引诱两方面合力造成的。人放弃了本真的、神圣的快乐,转而去享受满足感官的快乐。而人之所以放弃永恒的目的,转向一个转瞬即逝的目的,则是因为沦为自我满足、自我沉迷的奴隶,同时还有意无视人本身的终极的神圣目的和神圣使命。这是马克西姆描述的有关人类堕落的基本境况。由这一境况可以看出,对于人类来说,罪进入其生命的根源还是人自己意志的作用,人的堕落应该归咎于人自身,是人自己错用了上帝赋予其的自决能力和自由意志。接着,他又做出了两种意志的区分,这是马克西姆对东正教传统的卓越贡献。根据马克西姆,人具有一种“本性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一种出自本性的力量,是上帝在造人时所赋予人的,它趋向于一切与本性相符的事物,是一种接受属于本性的任何本质属性的能力,是欲求善的能力,即使在人类堕落以后这种能力也不会完全失去,因为它属于人之为人的本质。马克西姆将这种欲求善的意志与“抉择的意志”相区分,后者是人作为位格所具有的一种特性,而非人之本性。在人类堕落之后,两者的运作模式是:本性发出意愿,并行动,位格则进行抉择,接受或是拒绝本性所意愿的。根据马克西姆,这种选择性自由的出现就已经是人不完善的体现,是对本真自由的一种限制。一个完善的本性根本无需选择,因其自然就明白何为善。而我们抉择的意志做出的所谓“自由选择”标志着人性受到了伤害,标志着我们失去了(或不具有)与上帝的相像。[9](pp. 226-228)

Gregory Palamas
在马克西姆之后,格里高利·帕拉玛(Gregory Palamas, 1296-1359)是另一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正教思想家。对于帕拉玛来说,人的受造是整个创世事工的目的,而且人在受造时被赐予了自由意志,这也使得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者与其他动物相区分。帕拉玛,认为在堕落前,人处在一种合乎本性的自然状态,人与上帝处在一种和谐的共契中,人的生命完全与其命运相契合。堕落之后,人性失去了原有的神圣生命,成为可朽的,同时其生命状态也与其命运相违背,完全被不整全性、破碎性控制着。[10](p. 122)但值得注意的是,帕拉玛对堕落与罪责的区分对待,他没有笼统地认为后世的人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原罪,而是认为我们只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堕落的人性,但并没有继承他的罪责。
现代东正教思想家们基本继承了马克西姆与帕拉玛对罪的看法。洛斯基(Vladimir Lossky, 1903-1958)关于人性的原初状态是这样描述的:人最初受造是颇为完美的,他与上帝之间的交流不存在任何障碍,并且向着与上帝合一的终极目的不断前进。人性在堕落这一事件中的转变是一个甚为棘手的神学问题,如何前后融贯的论述是极为关键的。洛斯基在明确说明原初完美的人性无需选择后,他指出堕落后的人性已然是违抗上帝意志,并选择了与上帝相疏离。人对上帝意志的违背,这一位格举动还造成了身体上的后果。因为与上帝疏离,神圣的恩典便于人相分离,而随着神圣恩典的消失,人处在了一种濒于破碎的非自然状态。这种破碎包括两方面。一是由扭曲的欲望带来的身体上的破碎,满足身体需求的“食物”代替了属灵的“食物”;二是由共同体变为个体之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碎。这种破碎状态的终结即是死亡。[11](pp. 123-126)
斯塔尼莱(Dumitru Stăniloae, 1903-1993)关于堕落与罪的问题的讨论始于一个问题:“人类的原初状态究竟持续了多久?”我们当然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人没能保持这种原初状态,对斯塔尼莱来说,亚当与夏娃最初虽然是无罪之身,但是也不是彻底的完美。他们在日臻完美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属灵实践,因为正是上帝的意愿使人在与神的合力中不断累积善业。罪是在这一过程早期就出现的,但罪的出现并不是来自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出于人的懵懂无知,带有粗心和迟钝的因素。但这之后人开始出于怨意而犯罪,因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而中断了与上帝之间本无障碍的交流。于是,人便不再对上帝负责,转而寻求自由与自主性。当然,堕落并没有将人所具有的上帝形象彻底抹杀。但人所具有的善已不再仅仅用于善的目的了,因为有时它甚至成为恶的垫脚石。斯塔尼莱指出,恶就其本身而言并无任何吸引力,它会造成的破坏性结果显而易见,只有当其以美善为伪装时才具有欺骗性,而人类那已经受到损伤的对于善的直观能力便容易落入圈套。这样的状态若持续下去,人类就会因其已然扭曲了的欲望,一直承受恶的折磨。更进一步的后果,即是除人之外的整个世界,在人看来也就不再具有属灵的意义,也不再能反映神的荣耀,表达神的奥秘;人只能从世界获得物质性、身体性的知识,而不会再获得属灵的知识。人对上帝意志的违背,使得人变得自我中心,并进一步导致他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不再以世界本身为主体,不再关心其来自上帝的受造本质,而是将一切变为从自身出发进行处置的客体。而随着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种种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人在堕落前那种日益精进,不断整合自我,整合受造界各个部分,向着与上帝合一这一终极目的前进状态被迫中止了,只有待耶稣基督恢复一切应有秩序,人以及整个受造界才会继续那向着与上帝合一的属灵历程。[12](pp. 179-180)
梅延多夫(John Meyendorff, 1926-1992)则主要关注对原罪的解释。他指出奥古斯丁提出原罪这一概念的圣经根据是《罗马书》5:12。但是,根据东正教所依据的希腊文《新约》,从这一节经文中并不能解释出“继承之罪”的概念[13](p. 144)。没有“本性之罪”与“继承之罪”的概念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此一来,在人之成神之路上就不存在来自自身内部的结构性障碍,拯救对于人来说也就不会只是消极的静待上帝的恩典,而是有可为的。那么,在东正教传统中亚当的堕落就没有任何后果吗?当然不是。在东正教传统中,“堕落的遗传是等同于可朽的遗传,而非罪性的遗传”[13](p. 145)。人成为可朽的,就使得诸如食物、饮水的等身体的需要成为了必需,这些属身体、属物质的因素一旦成为必需就会吸引人大量的精力于其上,将人引向激情,就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由于可朽是遗传自人之始祖亚当,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事实,因此每个人的在世生存都面临着罪的可能,时时警惕,克服犯罪的冲动就成了每个人得救必修的功夫。所以,对于人类来讲,是因为可朽而犯了罪,而并非所有人都死于罪中。
虽然不同思想家的论述各有侧重,论述方式也迥然相异,但是,从上述总结我们不难看出,东正教传统关于罪及堕落问题的观点可以集中归纳为两点:一、罪的出现完全是意志带来的;二、并没有作为继承之罪的原罪。而通过对巴特罪论的考察,我们知道这两点是作为关键要素被包含在巴特对罪的论述体系中的,因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关于罪的问题,巴特同东正教传统具有相同的立场,这一立场的核心精神便是对罪的非实体性认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体现出巴特与东正教对罪的思考并没有将人性之本体的论述抛在脑后,而是与之紧密相关、通盘考虑的;另一方面,由于对罪的定性有共同的立场,这便意味着两者在论述人摆脱罪的束缚,走向最终拯救的问题时也会采取相似的进路,而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比较,则会展现出巴特拯救观与东正教成神论之间深层的渊源。
长久以来基督宗教因其异域背景,一直被汉语世界视为一种完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两者对人性的看法相互冲突”这一观点几乎成了汉语学界的共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署发表于1958年元旦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是表达这一观点的代表性文献。文中曾说道:
“……基督教要先说人有原罪,其教徒是本上帝之意旨,而由上至下,以救人。儒家则多信人之性善,人自身可成圣,而与天合德。此是一冲突。……基督教有天堂观念,亦有地狱观念,异端与不信者,是可入地狱的。……如此,则基督教对人之爱虽以一无条件,仍可以有一条件,即信我的教。此处实有一极大之问题。照儒家的意思,则只要是人,同有能成圣而与天合德之性。儒家并无教会之组织,亦不必要人皆崇拜孔子,因人本皆可成圣而同于孔子……”
追溯这种刻板印象形成的根源,主要是由于汉语世界对基督宗教的认识长期以来主要受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华人教会的建立多是基督新教各宗派及罗马天主教传教的结果。西方基督教传统长期秉持原罪论,而由此产生的人性败坏说在汉语世界的观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而上文所论述的巴特以及东正教传统的罪观则与传统西方基督教的罪观迥然相异。这种罪观在神学上最为本质的作用就是将罪从人性中剥离出来,使其仅仅作为对人之存在的经验性判断,而非本体论判断,如此一来也就为对人性做出积极的论断留下充分的空间。巴特与东正教传统就正是沿着此一路向在本体论层面对人性之美善予以肯定,为人之蒙恩得救提供了内在依据,此种理路恰与强调人性本善、内在超越的中国传统宗教—哲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正是基督宗教中为汉语世界所忽视的一面,随着对此一面向研究的深入,其必然会在基督教中国化以及中西文化会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①] 关于此可参见John B. Webster, “The Firmest Grasp of the Real: Barth on Original Sin”, in Barth’s Moral Theology: Human Action in Barth’s Thought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04), pp. 65-76 以及Allen Jorgenson, “Karl Barth’s Christological Treatment of Sin”, in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54(2001), pp. 439-462。
[1]Barth, Church DogmaticsIV/1, trans. G. W. Bromiley[M].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1
[2]Barth, Church DogmaticsIII/2, trans. H. Knight, G. W. Bromiley, J. K. S. Reid, and R. H. Fuller [M].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0
[3]Barth,Church DogmaticsIV/2, trans. G. W. Bromiley[M].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7
[4]Barth, Church DogmaticsIII/3, trans. G. W. Bromiley and R. J. Ehrlich[M]. Edinburgh: T. & T. Clark, 1961
[5]赖品超:《大乘基督教神学》[M]。香港:道风书社,2011年
[6]John B. Webster, “The Firmest Grasp of the Real: Barth on Original Sin”, in Barth’s Moral Theology: Human Action in Barth’s Thought[M].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04
[7]Allen Jorgenson, “Karl Barth’s Christological Treatment of Sin”[J].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54(2001)
[8]Wolf Krötke, Sin and Nothingnes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M]. Princeton: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2006
[9]L. Thunberg, Microcosm and Mediator. The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of Maximus the Confessor[M]. Chicago, IL: Open Court, 1995
[10]Meyendorff, A Study of Gregory Palamas[M].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 Bedfordshire: Faith Press, 1974
[11] Lossky,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M].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76
[12]Staniloae, The Experience of Godvol 2, trans. Ioan Ioniță, Robert Barringer[M]. Brookline, MA: 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 2000
[13]Meyendorff,Byzantine Theology: Historical Trends And Doctrinal Themes[M].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2
校订:巴特研究、Cheung、Kimeikei、Imaginist、伶俐、语石、Vanc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