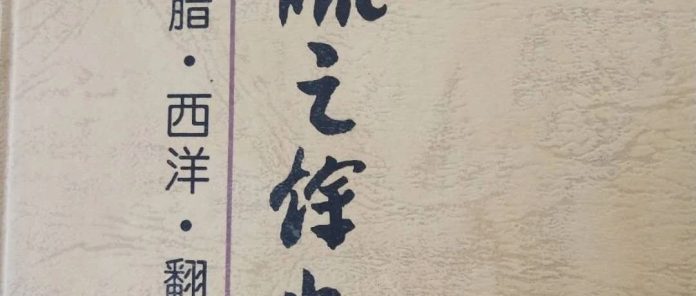本文最初刊于1921年1月《小说月报》12卷1号,署名周作人·收入《艺术与生活》
我对于宗教从来没有什么研究,现在要讲这个题目,觉得实在不大适当。但我的意思只偏重在文学的一方面,不是教义上的批评,如改换一个更为明瞭的标题,可以说是古代希伯来文学的精神及形式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四书五经相似,在教义上是经典,一面也是国民的文学;中国现在虽然还没有将经书作文学研究的专书,《圣书》之文学的研究在欧洲却很普通,英国《万人丛书》——“ Every man’s Library”里的一部《旧约》,便题作《古代希伯来文学》。我现在便想在这方面,将我的意见略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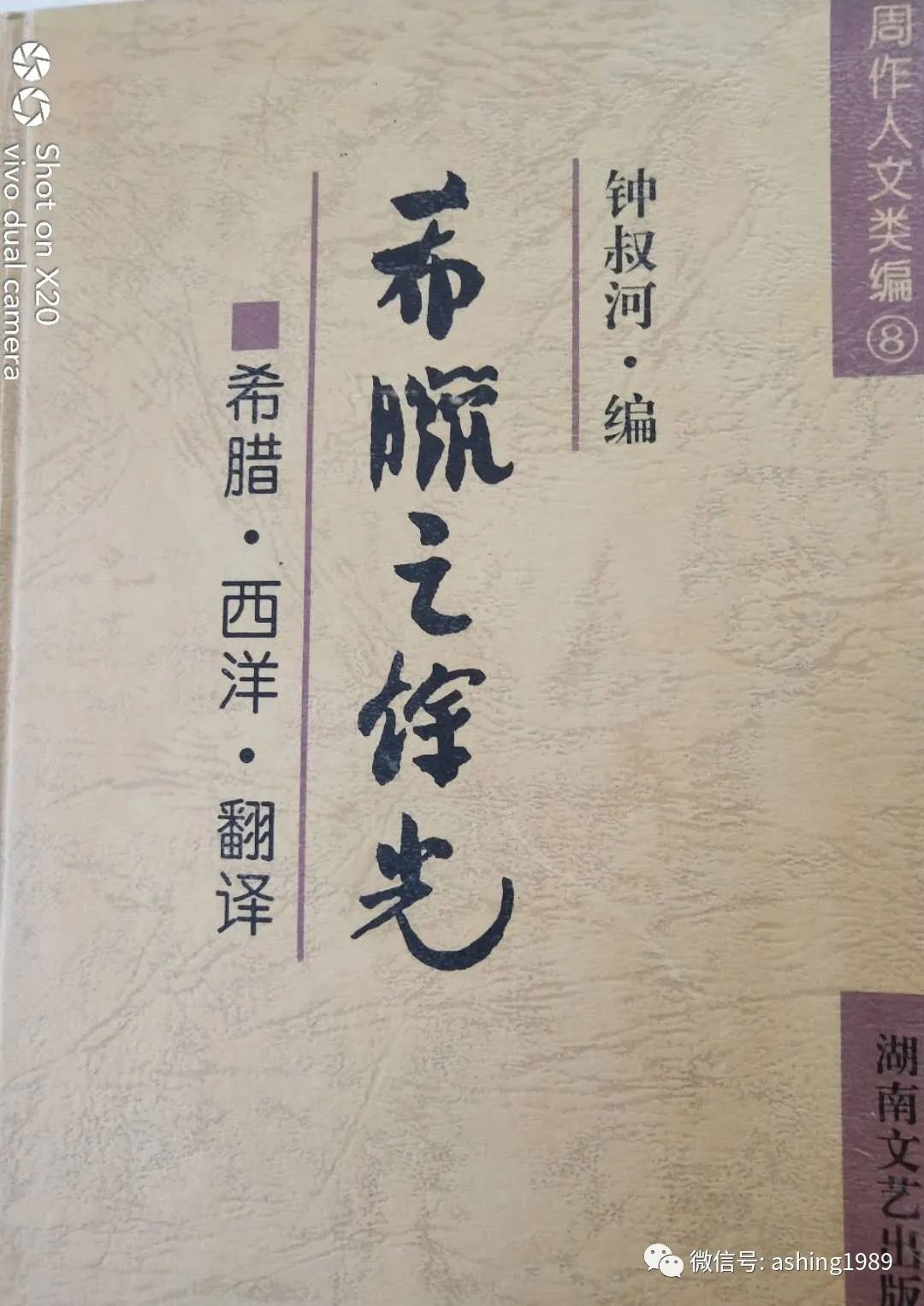
我们说《旧约》是希伯来的文学,但我们一面也承认希伯来人是宗教的国民,他的文学里多含宗教的气味,这是当然的事实。我想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本来很是密切,不过希伯来思想里宗教分子比别国更多一点罢了。我们知道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如希腊的诗(Mele= Songs)、赋(Epe=Epics)、戏曲都可以证明这个变化,就是雕刻绘画上也可以看出许多踪迹。一切艺术都是表现各人或一团体的感情的东西;《诗序》里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所说虽然止于歌舞,引申起来,也可以作雕刻绘画的起源的说明。原始社会的人,唱歌,跳舞,雕刻绘画,都为什么呢?他们因为情动于中,不能自已,所以用了种种形式将他表现出来,仿佛也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最初的时候,表现感情并不就此完事;他是怀着一种期望,想因了言动将他传达于超自然的或物,能够得到满足:这不但是歌舞的目的如此,便是别的艺术也是一样,与祠墓祭祀相关的美术可以不必说了,即如野蛮人刀柄上的大鹿与杖头上的女人象征,也是一种符咒作用的,他的希求的具体的表现。后来这祈祷的意义逐渐淡薄,作者一样的表现感情,但是并不期望有什么感应,这便变了艺术,与仪式分离了。又凡举行仪式的时候,全部落全宗派的人都加在里边,专心赞助,没有赏鉴的馀暇;后来有旁观的人用了赏鉴的态度来看他,并不夹在仪式中间去发表同一的期望,只是看看接受仪式的印象,分享举行仪式者的感情;于是仪式也便转为艺术了。从表面上看来,变成艺术之后便与仪式完全不同,但是根本上有一个共通点,永久没有改变的,这是神人合一,物
我无间的体验。
原始仪式里的入神( Enthousiasmos)、忘我(Eksass),就是这个境地;此外如希腊的新柏拉图派,印度的婆罗门教,波斯的“毛衣外道”(Sufi)等的求神者,目的也在于此;基督教的《福音书》内便说的明白,“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8章27节)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托尔斯泰著的《什么是艺术》,专说明这个道理,虽然也有不免稍偏的地方,经克鲁泡特金加以修正,(见《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内第二章《文学观》)但根本上很是正确。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合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
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相互的合一,如《福音书》上所说。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但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一切的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非基督教的艺术虽然一面联合了几个人,但这联合却成了合一的人们与别人中间的分离的原因;这不但是分离,而且还是对于别人的敌视的原因。(《什么是艺术》第十六章)
同样的话,在近代文学家里面也可以寻到不少。俄国安特来夫( Leonid- Andrejev)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英国康剌特( Joseph–Conrad,本波兰人)说,“对于同类的存在的强固的认知,自然的具备了想像的形质,比事实更要明瞭,这便是小说。”福勒忒解说道,小说的比事实更要明瞭的美,是他的艺术价值。但有更重要的地方,人道主义派所据以判断他的价值的,却是他的能使人认知同类的存在的那种力量。总之,艺术之所以可贵,因为他是一切骄傲偏见憎恨的否定,因为他是社会化的。”这几节话都可以说明宗教与文学的共通的所在,《圣书》与文学的第一层的关系,差不多也可以明瞭了。宗教上的《圣书》即使不当作文学看待,但与真正的文学里的宗教的感情,根本上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第一层的关系
以上单就文学与宗教的普通的关系略略一说,现在想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特别的关系上,再略加说明。我们所注意在原在新的一方面,便是说《圣书》的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及创造上,可以有如何的影响;但旧的一方面,现今欧洲的《圣书》之文学的考据的研究,也有许多地方可以作中国整理国故的方法的参考,所以顺便也将他说及。
我刚才提及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经书相似:《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书经》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但欧洲对于《圣书》,不仅是神学的,还有史学与文学的研究,成了实证的有统系的批评,不像是中国的经学不大能够离开了微言大义的。即如《家庭大学丛书》( Home University Library)里的《旧约之文学》,便是美国的神学博士谟尔( George F. Moore)做的。他在第二章里说明《旧约》当作国民文学的价值,曾说道:“这《旧约》在犹太及基督教会的宗教的价值之外,又便是国民文学的残馀,尽有独立研究的价值。这里边的杰作,即使不管著作的年代与情状,随便取读,也很是愉快而且有益;但如明瞭了他的时代与在全体文学中的位置,我们将更能赏鉴与理解他了。希伯来人民的政治史,他们文明及宗教史的资源,也都在这文学里面。”他便照现代的分类,将《创世记》等列为史传,《预言书》等列为抒情诗,《路得记》《以斯帖记》及《约拿书》列为故事,《约伯记》——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学的伟大的诗之一,——差不多是希腊爱斯吉洛思( Aiskhylos)式的一篇悲剧了。对于《雅歌》,他这样说:“世俗的歌大约在当时与颂歌同样的流行,但是我们几乎不能得到他的样本了,倘若没有一部恋爱歌集题了所罗门王的名字,因了神秘的解释,将他归入宗教,得以保存。”又说:
这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题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在一世纪时,这书虽然题着所罗门的名字,在严正的宗派看起来不是圣经;后来等到他们发见——或者不如说加上——了一个譬喻的意义,说他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才将他收到正经里去。古代的神甫们将这譬喻取了过来,不过把爱人指基督,所爱指教会(钦定译本的节目上还是如此)或灵魂。中古的
教会却是在新妇里看出处女马理亚。……譬喻的恋爱诗——普通说神与灵魂之爱一一在各种教义与神秘派里并非少见的事;极端的精神诗人时常喜用情欲及会合之感觉的比喻,但在《雅歌》里看不出这样的起源,而且在那几世纪中,我们也不曾知道犹太有这样的恋爱派的神秘主义。
所以他归结说:“那些歌是民间歌谣的好例,带着传统的题材、形式及想象。这歌自然不是一人的著作,我们相信当是一部恋爱歌集,不必都是为嫁娶的宴会而作,但都适用于这样的情景。”这《雅歌》的性质正与希腊的催妆诗( Epithalamia)之类接近。在托尔斯泰派的严正批评里,即使算不到宗教的艺术,也不愧为普遍的艺术了。我们从《雅歌》间题上,便可以看出欧州关于圣书研究的历史批评如何发达与完成。中国的经学却是怎样?我们单以《诗经》为例;《雅》、《颂》的性质约略与《哀歌》及《诗篇》相似,现在也暂且不论,只就《国风》里的恋爱诗拿来比较,觉得这一方面的研究没有什么满足的结果。这个最大原因大抵便由于尊守古训,没有独立实证的批判;譬如近代龚橙的《诗本谊》(1889出版,但系1840年作)反对毛传,但一面又尊守三家遗说,便是一例。他说,“古者劳人思妇,怨女旷夫,贞淫邪正,好恶是非,自达其情而已,不问他人也。”又说,“有作诗之谊,有读诗之谊,有太师采诗瞽矇讽诵之谊,”都很正确,但他自己的解说还不能全然独立。他说,“《关睢》,思得淑女配君子也”;《郑风》里“《女曰鸡鸣》,淫女思有家也”。实际上这两篇诗的性质相差不很远,大约只是一种恋爱诗,分不出什么“美刺”,著者却据了《易林》的“鸡鸣同兴,思配无家”这几句话,说他“为淫女之思明甚”,仍不免拘于“郑声淫”这类的成见。我们现在并不是要非难龚氏的议论,不过说明便是他这样大胆的人,也还不能完全摆脱束缚;倘若离开了正经古说训这些观念,用纯粹的历史批评的方法,将他当作国民文学去研究,一定可以得到更为满足的结果。这是圣书研究可以给予中国治理旧文学的一个极大的教训与帮助。
说到《圣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可以分作精神和形式的两面。近代欧洲文明的源泉,大家都知道是起于“两希”就是希腊和希伯来思想,实在只是一物的两面,但普通称作“人性的二元”,将他对立起来;这个区别,便是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希腊以人体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神便是完全具足的人,神性便是理想的充实的人生。希伯来以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成,所以偏重人类所分得的神性,要将他扩充起来,与神接近以至合一。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互相撑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现象。其实希腊的现世主义里仍重中和( Sophrosyne),希伯来也有热烈的恋爱诗,我们所说两派的名称,不过各代表其特殊的一面,并非真是完全隔绝,所
以在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及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已有了融合的端绪,只是在现今更为显明罢了。我们要知道文艺思想的变迁的情形,这《圣书》便是一种极重要的参考书,因为希伯来思想的基本可以说都在这里边了。
其次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旧约》里古代的几种纪事及预言书,思想还稍严厉;略迟的著作如《约拿书》便更明瞭的显出高大宽博的精神;这篇故事虽然集中于巨鱼吞约拿,但篇末耶和华所说,“这蓖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一节才是本意的所在。谟尔说,“他不但《以西结书》中神所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的话,推广到全人类,而且更表明神的拥抱一切的慈悲。这神是以色列及异邦人的同一的创造者,他的慈惠在一切所造者之上。”在《新约》里这思想更加显著,《马太福音》中登山训众的话,便是适切的例。耶稣说明是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所以他对于古训加以多少修正,使神的对于选民的约变成对于各个人的约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人作对,”(5章38-39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章43-44节)这是何等博大的精神!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奇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约翰福音》第8章7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事,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的这两种言行上的表现,便是爱的福音的基调。“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第23章8节)“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约壹4章16节)这是说明爱之所以最大的理由,希伯来思想的精神大抵完成了;但是“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约壹4章20节)正同柏拉图派所说不爱美形就无由爱美之自体( Autoto kalon)一样;再进一步,便可以归结说,不知道爱他自己,就不能爱他的兄弟:这样又和希腊思想相接触,可以归入人道主义的那一半的源泉里去了。

其次讲到形式的一方面,《圣书》与中国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便因他有中国语译本的缘故。本来两国文学的接触,形质上自然的发生多少变化,不但思想丰富起来,就是文体也大受响,譬如现在的新诗及短篇小说,都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倘照中国文学的自然发达的程序,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呢。希伯来古文学里的那些优美的牧歌(Eidyllia= Idylls,)及恋爱诗等,在中国本很少见,当然可以希望他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预言书》派的抒情诗,虽然在现今未必有发达的机会,但拿来和《离骚》等比较,也有许多可以参照发明的地方。这是从外国文学可以得来的共通的利益,并不限于《圣书》;至于中国语的全文译本,是他所独有的,因此便发生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了。我们看出欧洲《圣书》的翻译,都于他本国文艺的发展很有关系,如英国的微克列夫( Wyclif)、德国的路得 Luther)的译本皆是。所以现今在中国也有同一的希望。
欧洲《圣书》的译本助成各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这动因原是宗教的,也是无意的。《圣书》在中国,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所深信的不疑的,这个动因当是文学的,又是有意的。
两三年来文学革命的主张在社会上已经占了优势,破坏之后应该建设了;但是这一方面成绩几乎没有;这是什么原故呢?思想未成熟,固然是一个原因,没有适当的言词可以表现思想,也是一个重大的障害。前代虽有几种语录说部杂剧流传到今,也可以备参考,但想用了来表现稍为优美精密的思想,还是不足。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就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的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许多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十四五年前复古思想的时候,我对于《新约》的文言译本觉得不大满足,曾想将《四福音》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抗衡,这才适当。但是这件事终于还未着手;过了几年,看看文言及白话的译本,觉得也就可以适用了,不过想照《百喻经》的例,将耶稣的譬喻从新翻译,提出来单行,在四五年前还有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到得现在,又觉得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说怎样是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模范,但可以说在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的注意,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我们且随便引几个例:
《何西阿书》第14章5-6节: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他必如百合花开放,
如利巴嫩的树本扎根;
他的枝条必延长,
他的荣华如橄榄树,
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
《雅歌》第2章15节: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启示录》第17章7-8节:
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希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
这几节都不是用了纯粹的说部的白话可以译得好的,现在能够译成这样信达的文章,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一件,是标点符号的应用:人地名的单复线,句读的尖点圆点及小圈,在中国总算是原有的东西;引证话前后的双钩的引号,申明话前后的括弓的解号,都是新加入的记号。至于字旁小点的用法,那便更可佩服;他的用处据《圣书》的凡例上说,“是指明原文没有此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更显明。”我们译书的时候,原不必同经典考释的那样的严密,使艺术的自由发展太受拘束,但是不可没有这样的慎重诚实的精神;在这点上,我们可以从《圣书》译本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以上将我对于《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意见,约略一说。实在据理讲来,凡是各国的思想,在中国都应该介绍研究;与希伯来对立的希腊思想,与中国关系极深的印度思想等,尤为重要。现在因为有《圣书》译本的一层关系,所以我先将他提出来讲,希望引起研究的兴味,并不是因为看轻别种的思想。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希伯来思想与文艺,便是这多种思想中间,我们所期望的一种主要坚实的改造的势力。
(一九二0年)
阿信注:我好几年前就看到周作人先生《圣书与中文文学》的片段,遂处处留心,寻找这篇文章全文。去年12月在广西希望高中西乡书馆看到钟叔河主编《周作人文类编》,在其中第八册《希腊之余光》内找到这篇文章。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心中喜悦。于是整理成电子版,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阿信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