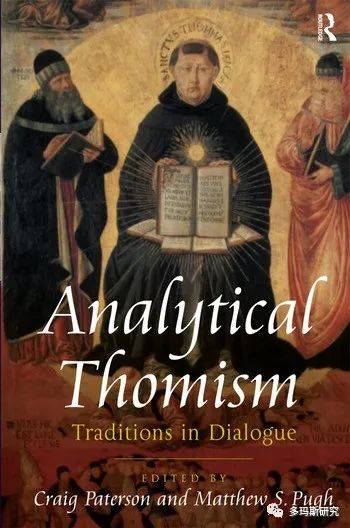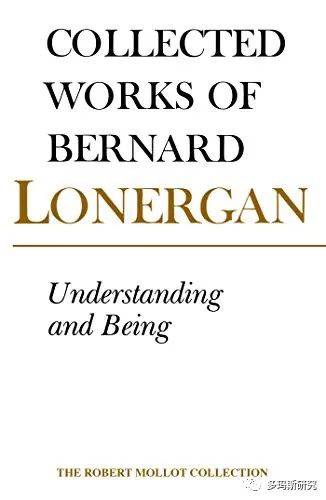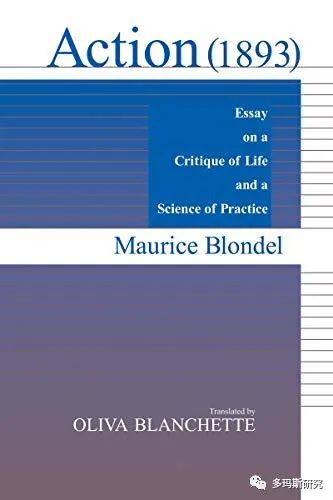著:克雷格•帕特森(Craig Paterson)
[ 这篇文章是《分析多玛斯主义:对话中的传统》(Analytical Thomism : Traditions in Dialogue)一书编者所写的导言。这本书所辑录的讨论,或是在方法上与分析哲学相关;或是在论题上与多玛斯主义相关,其中涉及到形而上学/存有论、元伦理学、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自然神学、哲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等话题。而这篇导言分别从多玛斯主义的历史和分析哲学的历史中带出了分析多玛斯主义兴起的过程,并介绍了其中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主要思想。——译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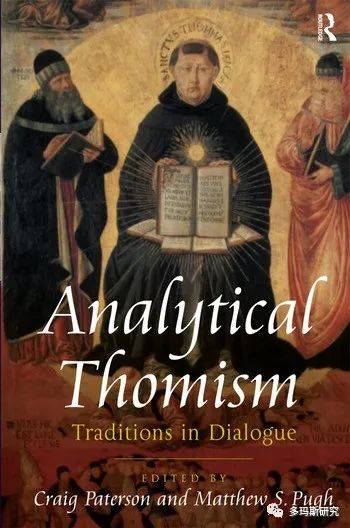
首次拿到当前这本书的人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分析多玛斯主义”(Analytical Thomism)?这个问题很好,但却难以回答。该术语的第二部分也许比第一部分更容易(得到)回答,因为“多玛斯主义”可以很轻易地被视为指涉某特定思想的文献集,即多玛斯•阿奎那的思想以及后世对其思想的解释。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家对于“分析哲学”中的“分析”是什么,以及这与多玛斯主义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则相对来说还不是很清楚。例如,分析哲学是否信奉一套特定的学说或信念?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会回答“否”。他们会坚持认为,无论分析哲学是什么,无论其历史渊源如何,当今的哲学家都在使用分析哲学去论证贯穿哲学谱系的诸立场——从形而上学的各种实在论和观念论,到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甚至到伦理学中的非认知主义和功利主义。那么,分析哲学是否主要是一种哲学方法,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确实都会说,除了高度重视严格的论证和清晰的表述之外,没有其他做分析哲学的方法。但是,许多通常不被称为分析哲学家的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希望大多数哲学家都如此)也将论证的合理性和表达的清晰性放在首位。
对于多玛斯主义者来说,阿奎那肯定是具有严谨性和纪律性的神哲学思想家的卓越榜样。那么,分析哲学对多玛斯主义者的吸引力会是什么呢?多玛斯主义者转向分析哲学是否只是为了“捡”一些有用的技术,以帮助他们对阿奎那思想的特殊领域进行分析性澄清?或者是因为,分析哲学能比传统的新多玛斯主义更有效地阐明我们对阿奎那思想中最深邃的概念性基础的批判性理解,所以才更深深地被分析哲学的源泉所吸引?
分析哲学与多玛斯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人的心里生出了以下的疑问:是否分析多玛斯主义者一定要坚持传统框架下多玛斯主义思想的理论?例如,他们是否必须对天主的存有,特别是基督宗教的天主的存有,承认哲学上某种合理的证明(或至少捍卫天主存在的可能性)?又或者,分析多玛斯主义者是否至少要支持某种形式的形质论(hylomorphism)?
这些问题都是合乎情理的,任何自称分析多玛斯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在适当时候对之做出回应,因为他或她肯定会被推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即在学术交流的各种渠道中参与辩论。我们则认为《分析多玛斯主义:对话中的传统》这本书就是这样一种渠道,它邀请欧美的新老学者来反思分析哲学与多玛斯主义之间,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错综影响。读者很快会发现,本书的内容,包含着那些将对话视为分析哲学与多玛斯主义之调和的人,以及那些对二者之间是否有可能存在真正具成效的思想交流,持冷淡或怀疑态度的人。
我们意识到需要一篇导言,特别是在汇编中,有必要为读者提供一些关于该领域的概述;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概述(尽管是非常简短的)多玛斯主义的发展历史,然后简要地阐述如何看待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与这一历史的关系,最后再根据这一简短的历史叙述进一步考虑“分析多玛斯主义”这词的含义。
多玛斯主义的历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阿奎那在1274年去世后,其哲学的部分内容几乎立即遭到了谴责,首先是来自1277年巴黎的唐皮耶主教(Bishop Tempier),然后是道明会会士基尔沃德拜(Robert Kilwardby),后来是马雷(William de la Mare)。然而,阿奎那的一些道明会同事为他进行了辩护,如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威廉(William of Macclesfield)和巴黎的若望(John of Paris);这促成了五十年后,1323年阿奎那被封为圣人。到了15世纪若望•卡普鲁如斯(John Capreolus)的时代,阿奎那成为了道明会会士中最受喜爱的哲学家,他们开始对《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进行评注。这些评注不仅是为了传播阿奎那的教导,而且还是为了与“竞争对手”司各都和奥卡姆的哲学相抗颉。多玛斯主义的第一阶段由此开始。
脱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的成果之一是创立了新的修会,例如耶稣会,该修会在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的影响下拥护阿奎那的哲学。随着后脱利腾时代的道明会士(Post-Tridentine Domincans)作品的出现,反过来又引发了多玛斯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该阶段由卡耶坦(Cajetan),圣多玛斯的若望(John of St Thomas),以及耶稣会士多明戈•德索托(Domingo de Soto),刘易斯•德莫利纳 (Luis de Molina)和方济各•苏亚雷斯(Francesco Suarez)的评注所主导。到了16世纪,阿奎那被封为教会圣师(Doctor of the Church)时,多玛斯主义思想的两个主要流派是意大利的道明会士和西班牙的耶稣会士。不幸的是,多玛斯主义这充满希望的第二阶段结束于这两派之间关于恩宠和自由意志这一棘手问题的激烈争论中。
在17、18世纪,多玛斯主义可以说是陷入了“艰难时期”,这两个世纪的多玛斯主义者并没有真正产出任何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不过,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托马索•泽利亚拉(Tommaso Zigliar)和若瑟•克鲁特根(Joseph Kleutgen)等思想家的工作,多玛斯主义开始革新和复苏,并在1879年良十三世的通谕《永恒之父》( Aeterni Patris)中达到高潮。正如霍尔丹(John Haldane)在《多玛斯主义和天主教哲学的未来》一文所指出的,《永恒之父》所复兴的多玛斯主义哲学有两个方向:(i)一个是“问题式的”,试图利用阿奎那的哲学来应对当时的哲学挑战,例如源自笛卡尔和康德的观念论,或休谟的经验论;(ii)另一个是“历史式的”,使用文本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最新技法,通过剥离后来解释者[2](例如卡耶坦和圣多玛斯的若望)新增的解释来发现“真正的”阿奎那。

( 良十三世:1810年3月2日-1903年7月20日 )
当然,这两种方法都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那些希望利用阿奎那的见解来应对当时的哲学挑战的人身上。一方面,这些多玛斯主义者很难不受他们欲求抗衡的哲学的影响。尽管他们坚信阿奎那的许多基本哲学论断的本质正确性,但也会欣赏那些来自最终要遭到他们反驳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的洞见。换句话说,他们可能认为,其中一些思想实际上可以用来支持、澄清和进一步推进阿奎那的一些基本哲学和神学立场。因此,例如在波兰,胡塞尔及其诠释者的现象学(例如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与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著作,都以各种方式融入进了阿奎那哲学中,并常常取得丰硕的成果。这种联姻中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例子当然是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的《行动中的人》(The Acting Person)。[3]
试图在不同的哲学之间实现和解甚至综合,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而且很有可能(被指控)扭曲那要被综合的哲学,就象在二十世纪发展而出的“先验多玛斯主义”在许多人眼里那样。康德对许多多玛斯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大多数人倾向于拒绝康德的观念论,但有些人,如皮埃尔•卢塞洛(Pierre Rousselot)和若瑟•马雷夏尔(Joseph Marechal),却接受了康德式的主体转向。特别是马雷夏尔,他在主体中找到了形而上学的起点。但是,他声称康德没有看到只有无限存有才能奠基或保证现象对象的存有。 换句话说,康德未能看到,在意识对象的综合形成过程中,主动理智的内在动力需要一个绝对的终际(terminus)。实际上,马雷夏尔认为,阿奎那关于对象的形而上学批判可以成功地移植到康德关于对象的先验批判中。 尽管马雷夏尔的多玛斯主义的先验版本确实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追随者,例如伯尔纳铎•罗纳根(Bernard Lonergan),但大多数多玛斯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都拒绝将阿奎那和康德进行这种融合,并认为该做法是对这两种哲学的不切实际的扭曲。[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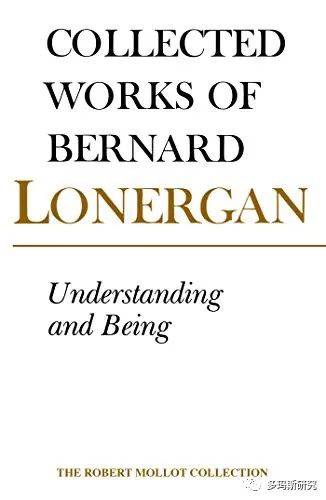
(Bernard Lonergan的名著《洞见》)
其他多玛斯主义者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或许在多玛斯主义和另一些思想传统之间的交流中会更加成功。在此,立即被我们想到的名字是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和埃蒂安•吉尔松(Étienne Gilson)。这两位思想家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世俗哲学(尤其是法国存在主义)中引生了一个多玛斯主义学派,它被称为“存在多玛斯主义”(Existential Thomism)。
最初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博朗德(Maurice Blondel)的影响下,马利坦皈依天主教,随后在法国道明会导师拉格朗日(Reginald Garrigou-Lagrange)的指导下对阿奎那文本进行研究,这导致他接受了一种基于圣多玛斯的若望和卡耶坦的评注的多玛斯主义。马利坦的许多著作反映了(那些)被他所认定的阿奎那哲学的永恒主题,如将存在(esse)理解为存在活动(actus essendi)的形而上学的首要性;将对形而上学存有的直觉作为多玛斯主义形而上学的适当起点的必要性;以及在认识论中,将真理概念理解为符合[5](adequation)的重要性。例如,在他的《知识的限度》[6]中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他在其中反复讨论了诸如埃米尔•梅森(Emile Meyerson),埃米尔•皮卡德 (Emile Picard)、 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亚瑟•爱丁顿(Artur Eddington)、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等科学哲学家的工具主义观点,以支持他在知识秩序上的经验/理论(perinoetic/dianoetic)区分。马利坦毫不犹豫地运用他关于法国存在主义的知识,来支撑他对阿奎那的一些重要形而上学立场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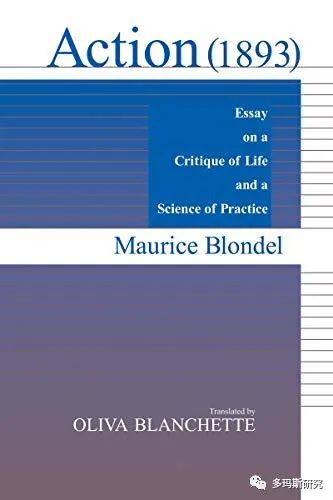
(Maurice Blondel的名著《行动》)
一些批评者(其中包括吉尔松)坚持认为,马利坦对亚圭那形而上学的解释,因为受累于道明会评注家,而口吻过于本质主义,因此错过了阿奎那关于存有的形而上学的存有论主旨。对于吉尔松而言(他相信自己忠实于阿奎那的文本),不仅马利坦对评注家的运用令人十分困扰,而且马利坦对(吉尔松所谓的)倒置的柏格森直觉主义的依赖也令人不满。对于吉尔松来说,没有对形而上学存在的直觉,在阿奎那的著作中也找不到类似的东西。正如他在《存在与某些哲学家》中尽力争辩的那样,[7] 阿奎那的形而上学建基于这样的理解:存有(being)首要地意味存在(esse)或实存(existence)[8],即一个存在者的实存活动,这不能与本质相混淆。因此,存在无法通过简单的理解来把握,也无法通过概念来认识。存在只能在对实存的判断中被把握或认识。为了从概念上进行思考,并将其提升到形而上学的水平,必须将存有和本质(essence)重新结合在一起,然后如此操作之:(i)抽象和(ii)以特殊否定判断的形式进行分离。对于吉尔松来说,我们认识存有的能力取决于并基于前–概念(pre-conceptual)的感官经验。然而,尽管吉尔松坚持阿奎那文本的权威,但毫无疑问,在撰写《存在与某些哲学家》时,他着眼于日益盛行的法国存在主义,并且也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
因此,到二十世纪中期,至少有三个发展良好的多玛斯主义流派,他们试图通过与阿奎那的思想建立联系,或与多玛斯的思想进行综合来解决当时的哲学挑战,其中有(i)波兰的卢布林学派,(ii)先验多玛斯主义,和(iii)存在多玛斯主义。
在那些于二十世纪公开选择的历史式路径的人中,我们在此只能提到到加拿大的若翰•欧文斯(Joseph Owens),美国的若望•威珀尔(John Wippel)和欧洲评注学中著名“参与式多玛斯主义者”——科尔内略•法布罗(Cornelio Fabro)和路易斯•盖格(Louis Geiger)。
虽然重燃的对阿奎那哲学的兴趣产生了多玛斯主义新的流派,并开创了大量的一流历史式研究;然而,良十三世的通喻《永恒之父》也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即强化了以手册式的方法呈现阿奎那思想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在脱利腾会议之后的几十年里初萌。在那时,面对新教日益严峻的挑战,天主教会非常需要将教义系统化。出于该目的,并由于阿奎那哲学在天主教会对路德和加尔文的回应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天主教神学家发明了这类手册以总结阿奎那的论证和结论,使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更容易吸收,并在护教学中进行运用。这些手册也许是有益的,以其自身有限的方式成为了后–脱利腾教会中表达阿奎那思想的标准方法。
当良十三世于1879年将阿奎那作为天主教的“官方”哲学家(当时被用来作为对抗现代主义挑战的智性力量)时,他无意间增加了多玛斯教导手册的需求。无论这些手册对神学院学生有什么价值,二十世纪天主教神学院和大学继续使用手册,和手册式的教学方式,而这一方式,却使多玛斯主义和阿奎那在非天主教哲学家中声名狼藉。这些手册通常是武断教条式的、非批判性的,并且鄙视其他不同的观点。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灌输,所以在哲学价值方面充其量只有微乎其微的意义。
因此,尽管在《永恒之父》之后产生了融合性的多玛斯主义新流派,但是总体上来说,多玛斯主义还是很容易被等同于缺乏引证的手册式风格论说。非天主教哲学家认为,如果这就是阿奎那的想法,那么确实没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它。
所以在二十世纪的非天主教哲学家中,存在着普遍的对多玛斯主义和多玛斯主义者的不信任。如果在欧陆哲学家中对多玛斯主义者的不信任是强烈的,那么在分析哲学家中就更胜一筹了。分析哲学很早就以其强硬的思想、严谨的哲学方法而闻名,其实践者往往出自逻辑学、数学和硬科学背景。它在早期还因不屑于形而上学(至少是某些“坏”的形而上学),以及对宗教和价值的敌视而赢得了名声。
尽管当今的分析哲学家会立即指出,这种声誉只有部分是名副其实的,但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和罗素都展开了这类哲学,其主要任务是将日常语言还原为所谓的真逻辑内容,而这种内容往往被日常语言所遮蔽。现在,日常语言的真正逻辑内容由复合的命题和基本的事实陈述组成。因为后者被认为表征了世界真实的样子。日常语言所声称的无法被还原或重写的东西,即“形而上学”(坏的意义上)或“价值–负荷”的主张,就被简单地摒弃了。当然,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无疑也有自己的本体论,但正是这些哲学的还原论的方面,对他们的实证主义后继者最具吸引力,他们最终将这种还原论以意义的证实原则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1930年代,分析哲学并不倾向于同情地倾听阿奎那的声音,因为它依赖于“坏的”形而上学。无论他们有多么地不赞同所谓的弗雷格的柏拉图主义,但该时期几乎所有的分析哲学家都同意弗雷格对实存的评价,即“事实上对实存的断言无非是对数字零的否定。”[9]因此,当时任何有自尊的分析哲学家都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象阿奎那这样的哲学,这种哲学一再犯这样的错误——把实存当作一种真实的属性,而不是概念的二阶属性。当然,多玛斯主义者也不倾向于对分析哲学进行任何有分量的思考,因为他们确信(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分析哲学具有无可救药的反形而上学的偏见。
然而,当分析哲学从对逻辑实证主义短暂的迷恋中解脱出来,它很快就会受到其它的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导致它成为今天这样包罗万象的哲学话语共同体。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转变也许是维特根斯坦本人所做出的,当时他放弃了先前语言作为实在的镜子的观念,而转而接受了一种多功能主义的语言理论,其中,使用决定了意义。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的任务不再是通过对语言逻辑结构的还原分析来揭示世界的结构,而是去描述语言使用的历史。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以及意义证实主义原则的崩溃,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逻辑实证主义衰落之后,许多分析哲学家从这种特殊的哲学束缚中得以解放,并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甚至阿奎那等思想家,以寻求新的哲学灵感和见解。于是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些情况奠定了后来被称为“分析多玛斯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基础。
当然,正如分析哲学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10]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受到阿奎那可能会赞同的思想所启发。例如,弗雷格(尽管他关注于实存)捍卫了知识的客观性,而布伦塔诺(以某种方式成为分析哲学之父)捍卫了心灵状态的意向性,这是一种可追溯到阿奎那本人的经院思想。因此,对于分析哲学的中心争论之一的理论支撑,即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则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一位具有经院和亚里士多德背景的中世纪哲学家。
随着分析哲学在1950年代开始“转型”,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和奥斯丁(J. L. Austin)的共同努力下,其运动中心开始从剑桥转移到牛津。尽管他们通常与阿奎那没有任何联系,但他们都以亚里士多德的精神践行着哲学,考虑一下赖尔在他的《心的概念》[11]中对笛卡尔主义的批判, 和奥斯丁在他的《为辩解进一言》[12]中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这无疑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两个思想家以各自的方式,促使分析哲学家更加仔细地研究古代资源。
迫切需要通过重新研究古代资源来进行更新的最紧迫的领域之一是伦理学。逻辑实证主义使伦理学依赖于情感主义、非认知主义和功利主义。他们唯一的反对者是各种迂腐版的康德式道义论的支持者。像伊丽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这样的哲学家打破了僵局。她通过将美德伦理重新纳入主流伦理讨论做到了这一点。安斯康姆1958年发表的文章“当代道德哲学”[13],标志着分析哲学中规模较小但颇具影响力的运动开始了,该运动使美德伦理学再次受到尊重。安斯康姆认为,要克服情感主义、行为主义、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的局限性的唯一方法是寻求对整个美德概念的恢复。
如果安斯康姆试图挑战二十世纪中叶伦理学讨论所面临的一般条件,以促使人们开始对亚里士多德–多玛斯伦理学重新产生兴趣,那么安斯康姆的丈夫彼得•吉奇(Peter Geach),同样为分析哲学转向对阿奎那的兴趣产生了影响。与许多分析哲学家一样,吉奇主要是逻辑学家,他的《心灵行为》(Mental Acts,1958年)[14]抨击了当时统治着心灵行为结构的、被认为可靠的抽象主义(abstractionism)和倾向主义(dispositionalism)。吉奇特别批判了赖尔的 《心的概念》。在此,吉奇出于逻辑理由反对赖尔看似行为主义的心灵事件。吉奇说,心灵行为在逻辑上与心灵事件是不同的。他同时也拒绝了他所认为的对阿奎那关于抽象主义的标准解读,在吉奇看来,抽象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心理学——心灵拥有一种 “感觉”,这种感觉使它能够参考自己的内在经验;心灵概念便是从这种“感觉”中抽象而来。根据吉奇的观点,心灵并不是简单地抽象出一些符合事物的或完全相同的副本。在某种意义上,心灵产生概念。换句话说,心灵利用其概念形成能力来认识可知者,但是它所认识的可知者部分是得益于心灵中认识它们的能力。[15]就心灵哲学中的重要基础概念而言,《心灵行为》(按照分析哲学的思路)可以被视为对其多玛斯解读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还不能完全概括吉奇对分析多玛斯主义兴起的开创性贡献,因为他与安斯康姆共同撰写的《三位哲学家》中的“阿奎那”一章[16]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章代表了对阿奎那哲学核心主题的选择性研究,并试图澄清对阿奎那思想的错误解释,其精神与《心灵行为》大致相同。其中,将成为其他分析多玛斯主义者的关注重点(继吉奇之后)的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区分,也即阿奎那对存在或存有和实存(existence或某个est)的区分。吉奇认为,将两者混淆会导致将天主的本质存有等同于天主的实存这般观念上的混乱。
在分析哲学中,转向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尤其是阿奎那)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肯尼曾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于1950年代在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Gregorian University)学习。肯尼说到,在他的教授中,彼得•霍能(Peter Hoenen)和伯尔纳铎•罗纳根(Bernard Lonergan)都激发起了他对阿奎那哲学的兴趣。当他在牛津大学与吉奇和麦凯布(Herbert McCabe)一起学习时,他对阿奎那的兴趣进一步增强。他研究的一些最初成果有《行动、情感和意志》(Action, Emotion, and Will,1963)[17],《阿奎那:批判论文集》(Aquina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69)[18]和《意志、自由和能力》(Will,Freedom and Power,1975),[19] 这些都以各种方式表明肯尼受惠于阿奎那思想。在肯尼的《心灵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Mind ,1989)[20]中,阿奎那的影响尤为明显。在这项工作中,肯尼借鉴了许多在阿奎那的心灵哲学中具有智性渊源的要素。例如,肯尼巧妙地展示了,阿奎纳对理智与意志、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何以为当代分析哲学家们解决同样的问题提供了很多帮助。[21]他晚期的作品《阿奎那论存有》(Aquinas on Being)[22],用弗雷格的哲学并通过现代语言分析的视角审视了阿奎那的存有论。在此,肯尼试图站在反对方着力,因为在他看来,当代分析哲学显示了,阿奎那的存有论在其基本的形而上学基础上是如何从根本上不融贯的。

(伯尔纳铎•罗纳根 Bernard Lonergan SJ)
最后,在安斯康姆、吉奇和肯尼之后,少数分析哲学家对阿奎那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导致若望•霍尔丹(John Haldane)将这种哲学方法标签为“分析多玛斯主义”。而他自己既是英国分析思想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对阿奎那感兴趣的天主教哲学家。在安斯康姆、吉奇和肯尼的劳动成果的刺激下,霍尔丹实际上是在呼吁对多玛斯主义进行第四次复兴,而这次复兴将从与分析哲学的方法和关切的彻底对话中重新获得生机。对于霍尔丹而言,这样的复兴是能挽救多玛斯主义于如下两个不利处境的唯一途径:(i)有用但仅限于对阿奎那哲学的历史阐释,以及(ii)从中世纪的继承者到吉尔松、马利坦和先验主义者的不太严格的新多玛斯主义哲学。霍尔丹相信分析哲学可以为多玛斯主义提供很多东西,而若阿奎那今天仍然活着,他实际上将会是分析哲学家。为此,霍尔丹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论文,以襄引起一些哲学家(包括非天主教徒)推进对这一议程重要性的兴趣。《一元论者》(The Monist) [23]杂志1997年出版的那一期,对这项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整期都献给了有关分析多玛斯主义的话题。在这一期的序言中,霍尔丹给出了一个“分析多玛斯主义”的有效定义,这至少让我们终于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广泛的定义,“分析多玛斯主义”一词指:
分析多玛斯主义并不旨在用圣多玛斯来推进任何特定的学说。同样,这也不是一场虔诚的释经运动。相反,它试图将20世纪哲学的方法和思想——在英语世界内占主导地位的那哲学——与阿奎那所引入和发展的那种广泛思想框架产生联系。[24]
那期《一元论者》之后,霍尔丹的另一篇文章也推动了在多玛斯主义与分析哲学之间进行对话的呼吁,它发表在《新黑衣修士》(New Blackfriars, vol. 80, 1999)上,名为“多玛斯主义与天主教哲学的未来”[25]。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霍尔丹对分析哲学与多玛斯主义之间的交叉融合的呼吁,随之而来的是十二位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回应,这些哲学家和神学家大多对霍尔丹所呼吁的大旨表示有共鸣。

(《新黑袍修士》New Blackfriars)
我们这一本《分析多玛斯主义:对话中的传统》,试图通过在这一相对较新的、仅发表了少量论文的哲学领域中增添新薪,以进一步推动这一对话的趋势。编辑们认为霍尔丹的工作有相当大的价值,分析哲学可以为多玛斯主义者和其他对阿奎那的思想感兴趣的人提供很多东西,而多玛斯主义者如果忽视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则也将面临危险。我们还坚持认为,霍尔丹对经院哲学的当前状态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它需要再次更新。当然,这种更新不一定只来自分析哲学,但作为这几十年来世界哲学的主流方法之一,分析哲学肯定要在这种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本书各章所示,接下来的关于“未来前景”的对话是充满生气和活力的。许多作者把活跃在分析哲学中的各种概念,应用于分析哲学家和多玛斯主义者都深为关注的问题之上。因此出现了形而上学/存有论、元伦理学、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自然神学、哲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自然法理论等章节。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多玛斯主义不与当时的哲学对话,而多玛斯主义者总是(甚至是历史学家)通过他们自己的哲学和文化环境的解释透镜来看阿奎那。在多玛斯主义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如此:在最早与司各都和奥卡姆论战的评注家时期,在卡耶坦和若望•品索特时期,以及脱利腾之后阿奎那的耶稣会运用者时期,在十八世纪的传统主义者和存有论者时期,在十九世纪的齐格利亚拉(Zigliara)和克鲁特根(Kluetgen)时期,当然也包括《永恒之父》之后。然而,我们坚信,这种“交融”远没有摧毁多玛斯主义,实际上它们总是会带来多玛斯主义思想的复兴,更新其语境上的相关性,以及进一步推动其观念上的进步。对话如果是真诚的话,就应该不遗余力地把那些不同意见包括进来,即那些可能不同意需要与分析哲学的接触,来积极理解第四次多玛斯主义复兴的人的意见。本书中的另一些文章反映了一些新多玛斯主义者对分析多玛斯主义者的工作的回应。不用说,并非所有新多玛斯主义者都相信这两种哲学方法是兼容的。迄今为止,鲜有传统的新多玛斯主义者赞同霍尔丹的使命,正如我们在布莱恩•香利(Brian Shanley),史蒂芬•塞隆(Stephen Theron)和约翰•克纳萨斯(John Knasas)的章节中所见。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分析多玛斯主义”的大部分兴趣来自分析哲学方面,而不是“多玛斯主义”方面。如它那短暂的历史所表明的,该领域的大多数人已经从分析哲学进入到了分析多玛斯主义。但很少有人能从新多玛斯主义进入分析多玛斯主义。鉴于对话仍处于早期阶段,假以时日,这种人员结构或许会有所改变。
尽管如此,也许这样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至少让新多玛斯主义者注意到了分析哲学家的工作,他们用分析哲学来论证阿奎那所捍卫的许多立场,而最后可能会使新多玛斯主义者决定更仔细地审视分析哲学本身的许多财富。显然,前者在阿奎那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我们希望,“分析多玛斯主义者”也将更仔细地考虑新多玛斯主义者对“分析多玛斯主义”提出的反对意见,并于将来尝试更全面地解决它们。
[1] 原文为Paterson, Craig & Pugh, Matthew (2006). Introduction to Analytical Thomism. In Craig Paterson & Matthew Pugh (eds.), Analytical Thomism: Traditions in Dialogue. Ashgate.
[2] John Haldane, “Thomism and the Future of Catholic Philosophy,” New Blackfriars 80 (April 1999), 164.
[3] Haldane, “Thomism,” 164.
[4] 关于先验多玛斯主义发展历史的出色概述,请参见Gerald McCool, From Unity to Pluralism (New York, N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5] 尽管在一般意义上都被翻译为“符合”,我们还是应当在多玛斯主义的adaequare与当代知识论的correspondence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具体来说,adaequare乃是一个现实性的、理智活动的结果,而非correspondence所指的在对象与命题之间的非现实性的同一关系。—校对者注
[6] Jacques Maritain, The Degrees of Knowledge, Gerald B. Phelan, trans.(New York, 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9).
[7] Étienne Gilson, Being and Some Philosophers (Toronto: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Medieval Studies, 1952).
[8] 老实说,不论我们是阅读还是翻译这样的句子都是极其具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句子里,西方哲学最令人胆寒的几个长时间以来一直为汉语学界–甚至西方学界–所混淆与误解的概念:being、esse、existence、existing,反复出现。看起来译者有必要在此处澄清这几组概念并对为什么如此翻译提供说明。我们不妨将这些概念分为三组。第一组,由einai的现在分词连缀的一系列概念:einai>ens(entitas)-being(entity);第二组,由einai的现在时不定式连缀的一系列概念:einai>esse(essentia)>to be(essence);第三组,由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非正式术语ti esti与晚期希腊哲学所使用的hyparkein连缀的一系列概念:ti esti(hyparkein)>existentia(exsistere)-existence(exist)。我们首先将给出一个翻译的结论,ens-being存有(entitas-entity 存有体)、esse-to be 存在(essentia-essence 本质)、existentia-existence 实存(exitare-exist 实存)。
倘若我们熟悉现代哲学的进路,那么很明确的是,实际上这部分概念已经为最优秀的欧陆哲学家与分析哲学家们所讨论了。大体而言,欧陆哲学沿着海德格尔的进路将ens与esse区分为存在者与存在;而分析哲学则或沿着罗素的进路成为不大加以区分的现实主义者(actualist)、或沿着迈农的进路成为可能主义者、又或者沿着刘易斯的进路成为模态现实主义者。
不过在梳理了现代哲学的讨论脉络之后,仍应当说,如此讨论皆未深刻理解经院哲学思辨之本义—尽管他们都脱胎于此思辨。根据学界掌握的情况,吉尔松不是在所谓“现代哲学”的脉络里进行讨论的。也正借着吉尔松的这句断言,我们可以略谈这三组概念的希腊—中世纪渊源。Ens和esse是一对相辅成的概念,ens是sum的现在分词,很直接的指涉id quod est,也即是那存在着的东西,这一层面的ens应当被我们理解为存在者,或用中世纪的术语说是ens primus cognitum(有关这一部分的研究,参见Kemple的著作Ens Primum Cognitum in Thomas Aquinas and in Tradition)。不过ens并不仅止于此,这也是这个词被处理为存有的原因,ens同时被广泛用作是“可以被理解的”义,即ens supertranscedentale(有关这一部分的研究,参见Doyle的著作On the Borders of Being and Knowing)。假设我们像海德格尔一样只关注ens primus cognitum,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esse作为存在,是这世界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ens的原则或者原因,ens自然就是存在者了。他们二者的关系就是esse在某种意义上引起ens罢了。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ens拥有ens primus cognitum和ens supertranscedentale两个层次的话,不难得到另一个结论:ens supertranscedentale必将导致一个最完满的存在–天主,而ens则是分有了那最完满的存在的。其他的事物也通过类比的方式是如此,他们的ens分有了他们的esse。也就是说,ens一方面是那由esse引起的、在自身有esse作为原因的实体;另一方面也是对esse的分有与实现。因而将ens翻译为存在者是不全面的,翻译为存有则考虑到了海德格尔的翻译者们在语言上所忽略的、海德格尔本人在哲学上所忽略又或者否定的“分有”的层次,相较更为妥当。由此entitas与essentia的意义与翻译也会比较明确。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句话的后面一部分里又出现了“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乃是因上下文我们得知在此处应单单考虑ens primus cognitum时作出的权衡。
再到existentia的处理。实际上,通过对古希腊哲学鼎盛时期文本的观察,并没有所谓“出离”的存在,而只有最终被理解为sum样态的einai(有关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参见Kahn的文章“Why Existence Does Not Emerge as a Distinct Concept in Greek Philosophy?”)实际上,尽管有“ti esti”与“hyparkein”这样的词来对应exsistere,真正成熟的existentia概念还是出现在伊斯兰哲学中。在伊斯兰哲学与随后的经院哲学里,existentia被认为指具体事物的存在样态(what it is)。因而把existentia理解为“实存”—实际存在,乃是恰切的。进一步来说将天主与一般的存有区分开来,也是依靠于实存概念的。在天主这个“ipsum esse subsistens”里,其存在与实存乃是同一的;而在一般的ens中,其之存在与实存则并非同一。—校对者注
[9] Gottlob Freg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J. L. Austin, trans.(Oxford: Blackwell, 1953), 51.弗雷格在对象与符号的角度区分了实存与存在的运用。—校对者注
[10] 关于分析多玛斯主义的历史背景,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概述,请参见Fergus Kerr,“Aquinas and Analytic Philosophy:Natural Allies?” in Modern Theology 20:1 (2004), 123–39.
[11] Gilbert Ryle,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Hutchinson, 1949).
[12] J. L. 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 J. O. Urmson & G. J. Warnock,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13] Elizabeth Anscombe,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I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14] Peter Geach, Mental Acts: Their Content and Their Object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15] Kerr, “Aquinas,” 134–35.
[16] Peter Geach, “Aquinas,” in G. E. M. Anscombe & P. T. Geach, Three Philosophers (Oxford: Blackwell, 1961).
[17] Anthony Kenny, Action, Emotion and Will (London: Routledge, 1963).
[18] Kenny, ed. Aquina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6).
[19] Kenny, Will, Freedom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75).
[20] Kenny, Metaphysics of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 另请参阅 Kenny’s Aquinas On Mi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93).
[22] Kenny, Aquinas On Be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John Haldane, ed. “Analytical Thomism,” The Monist 80:4 (1997).
[24] Haldane, Prefatory Note.
[25] Haldane, “Thomism,”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