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众所周知,巴特不仅是一位大学神学院教授,而且还是一位有着十二年牧会经历的教会牧师,巴特对教会的思考与当时德国教会的处境和教会牧养的难题不无关联。这一点在巴特的《<罗马书 >释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李骏康老师认为,巴特早期在《<罗马书>释义》中的教会论侧重对教会的批判,但同时又表现其辩证神学的特质。通过“以扫的教会”与“雅各的教会”这对观念,巴特表达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教会纵然在上帝中仍有希望,但教会与上帝国之间仍然有无限的对立。在后来的《教会教义学》中,巴特的教会论论述相对分散,李老师试图分析总结蕴含其中的要点,从巴特对教会的构建与批判两个方面阐述了一种“基督论的教会论”。进一步地,围绕“教会合一”和“政治与公共事务”问题,李老师指出,巴特认为教会的多元性并不具有合法性;至于公共事务,巴特认为教会一方面对于公民社会有不可忽视的共同责任,另一方面也要坚守基督国度的内圈。最后,结合本地教会的具体处境,李老师强调,面对复杂的公共议题,巴特的教会论对于当代仍具有毫不过时的警醒意义。
本文原发表于歐力仁、鄧紹光編,《巴特與漢語神學II——巴特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文集》,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8,頁339-364。特此感谢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对“巴特研究”微信公众号的大力支持!本文推送前略有删订。
巴特的教會論及其對香港教會的提醒1
李骏康
一、
導言
若要在二十世紀的神學界中,選出一位對教會最具批判性的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肯定會是其中呼聲最高的一位。然而,相比起無數的巴特研究,專論巴特的教會論之著作則顯得不算很多,2 華人學界對這問題的專論更可以說是非常缺乏。3 故此,本文欲整理出巴特的教會論,並希望以此為借鏡,檢視一下現今香港教會的境況,作為在這位二十世紀神學巨人逝世四十周年和香港回歸祖國經過十個年頭之後的一點反思。
二、
《<羅馬書>釋義》中的教會論
誠如韋伯斯特(John Webster)所言,巴特全然是一位教會神學家,而且,所有巴特的著述都是向着基督徒群體而非學術群體而寫,是圍繞着教會的信仰和實踐這個主題。4 巴特的生平和思想是不能分開的,他的著作定必要在其生平的亮光中被閱讀,反之亦然。5 眾所周知,巴特早期在《<羅馬書>釋義》(The Epistle of Romans)中曾經對教會作出過深刻的批判,這與當時德國教會的處境,以及巴特所言的「危機神學」(theology of crisis)有關。6 巴特在寫作《<羅馬書>釋義》時於薩芬維(Safenwil)的教會出任牧職,其間要面對教會牧養的難題,發現過去所受的神學訓練都不能「學以致用」,再加上一九一三年不少當時德國著名的神學家,包括其師赫爾曼(Wilhelm Herrmann)等人,都公開支持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的戰爭政策,促使了他與自由神學(liberal theology)決裂、以及日後不斷的對之批判。7
《<羅馬書>釋義》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寫成。不少學者都指出,前期巴特和後期巴特的思想是有明顯的不同,例如,就教會觀方面,巴特前期的教會觀比較着重批判,而後期的則較着重建構。8 然而,這不能使我們忽略巴特前期,尤其《<羅馬書>釋義》的思想,因為在《<羅馬書>釋義》中,不論是他的教會觀、上帝的道(Word of God)、人觀、倫理學等,都已見出其思想的雛型和系統。正如巴特本人在《<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序言>中所說:「如果我有某種『體系』,那麼這體系就是承認基爾克果(S∅ren Kierkegaard,另譯祈克果)提到的時間與永恆之間『本質上無限的差異』,堅持考察這種區別的負面意義和正面意義。」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1
在《<羅馬書>釋義》中,巴特以「教會的困境」(the tribulation of the Church)、10「教會的過失」(the guilt of the Church)11 和「教會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Church)12為題,處理《羅馬書》第九至十一章的內容,闡述他早期的教會觀。巴特強調上帝和人之間存在本質上無限的差異,認為教會與以色列、人的律法、宗教一樣,都是與耶穌基督的福音之對立,是人的可能性與上帝不可能的可能性(impossible possibility)的對立。13 教會作為與上帝分隔的此世存在,是永恆的啟示進入短暫的時間之中,是彼世對此世的伸延,故此教會對上帝的所知和所有,正正是其對上帝的一無所知和一無所有。14 然而,巴特又指出,縱然福音與教會是如此的對立,但上帝國確立教會作為宣講福音的中介,我們不得不承認教會,不得脫離教會,而是共同參與在其中,共同承擔她的不足之處,因為這是源於福音對教會的態度。15 正如巴特的名言:「福音揚棄了教會,同時教會亦揚棄了福音」。16
巴特指出,不論教會這組織完美與否,但她總是關涉人與上帝的關係,17 而教會的根本困境在於,教會是賴以聽到上帝的道而組成的團體,但人總是會失效,這道由人的耳所聽、由人的口所言便不再是上帝的道,所以教會的真理是永不可能實現的。18 因此,巴特便提出了「以掃的教會」(the Church of Esau)和「雅各的教會」(the Church of Jacob)這對觀念。19 巴特認為,以掃的教會和雅各的教會兩者並不是兩個互相對立的東西,以掃的教會是指可見的(observable)、可知的(knowable)和可能的(possible)教會,她可見於耶路撒冷、羅馬、威登堡、日內瓦,以及所有古往今來的教會,但以掃的教會同時是敗壞和墮落的,以及發生分裂和革命的教會。20 而雅各的教會則是不可見的(unobservable)、不可知的(unknowable)和不可能的(impossible)教會,她不可擴張或萎縮;沒有位置,沒有名稱,也沒有歷史;人不能與之契通,也不能被她逐出。她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感召和揀選;也是始,是終。21 我們人所能談及的,都只是以掃的教會而不是雅各的教會,但談及以掃的教會之同時是不能夠忘記雅各的教會,因為前者是賴於後者,正如以掃的生是賴於雅各的生。22 關於這種揀選,巴特認為這是一種預定論(predestination)的奧秘,如同上帝的啟示一樣,但重要的是上帝要完成他的事業,完成其教會的事業,23 教會的揀選是僅僅由於信仰,唯有教會在聖靈中聆聽和傳講上帝的道,這一切都是出於上帝、在上帝之中。24 基於這種吊詭性,上帝的知識不是人和教會的知識,人所面對的上帝是未認識的上帝,這正是教會的困境。25
巴特反復強調,教會必須謹記神人之間本質上無限的差異,因為教會亦必須知道,人不能以任何的方法去追求上帝的義,以任何的手段昭示上帝的臨在和上帝的真實。26 故此,除了在信仰這神蹟中人可以獲得上帝的啟示、上帝的義,否則這便不是信仰。27 同樣地,教會亦唯有在這神跡出現之時才會成為雅各的教會,否[則,]她只能僅僅為以掃的教會,然而這神跡是不可追求,不可獲得,和不可擁有的,它是在人當中不可預見的、全新的和神聖的出現。28 因此,巴特指出,教會唯有抓緊以不可知的上帝為起始點的信仰,聆聽和宣講上帝的道,並謙恭地視聖徒的相通為靠賴寬恕的罪人之群體,並專注其宣講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教會才會是雅各的教會、信仰的教會和上帝之義的教會。29巴特指出這是古往今來不變的法則,他更引用路德的說法,認為教會若然要成為如此,便要勇於在這信仰的黑暗(darkness of faith)中起航。30 然而,古往今來教會也不曾如此,都是像《羅馬書》所說的,「靠行為」去尋求人所能見之物,這不是僅僅因為教會是以掃,而不是雅各,卻是全因她自己的過失。31 正如巴特嚴厲的指出,若教會讚揚其成就、裝潢、被受歡迎、現代化,和作為人有求必應的教會的話,那麼她只是在追求自己的滿足,這樣的教會是永不能成功,永遠不會是上帝的教會。32 巴特一再強調「教會的困境是其過失」,這過失正是她不承認其過失,並長久以來不正視上帝的奧秘所產生的困境。33 這困境不應被任何的方法減至最低,反之教會必須徹底地肯定它,並持續謹記它的嚴重性。34 巴特甚至斷言,「是教會把基督釘在十架上,而非這個世界。」35 面對這個對教會不可再嚴厲的批判,雅各的教會又如何可能?這一可能性的基礎是甚麼?
雅各的教會之可能性對巴特而言,是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性」(impossible possibility),巴特所指的就是一個所有人類行為可能的新方向,它與所有人的可能性截然相反,是「全然的他者」(Wholly Other),因為這個「全然的他者」是何時何地都開放着的可能性:永存的和未認識的上帝成為他所是的可能性。36 這種開放的可能性能使無論如何敗壞或由神職人員所支配的以掃的教會,其上、其後和其中都是雅各的教會,成為「荒漠中的教會」(Church in the desert)。37 巴特認為,這不可能的可能性比一切我們所認為可能的更加可能,有如光明在黑暗中照耀,而這不可能的可能性之條件,便是人要躍進無人可躍進的深淵:主耶穌、復活、以及信靠,這三者標誌着無條件的指令、全然的陌生、和上帝的義在絕對的時刻自主的行動。38
這裏我們看到巴特的辯證神學(dialectic theology)或稱「上帝的道的神學」(Theology of the Word of God)的特式,肯定上帝的道和一種辯證關係中更大的「是」(yes)。39 巴特指出,由於教會在其困境和過失中,就人而言是毫無希望可言,但教會之所以有希望,是因為在上帝中有希望,40 縱然教會是屬於耶洗別(Jezebel)和「巴力」(Baal)的教會,有屬巴力的特性,但她同樣也有屬於耶和華的特性。41 巴特指出,只要這樣,所有的教會,每一間教會,都未至被上帝所棄絕,雅各的教會在當下(at this present moment)已在以掃的教會之中,42 因為上帝對人的揀選是出於恩典,是一個福音,這福音在當下於教會的困苦和過失中如同光明照耀着,是教會唯一的希望。43 故此巴特指出,教會體現出一種含糊性,就是人的本性和人的文明之含糊性,這同時體現出基督福音與人手所作的工之對立,44 但在教會唯一的希望底下,盛載上帝的道的教會不致與基督的福音互相對立,因為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揀選,教會就成了一切尋求寬恕的聖徒團契,一切失落但被拯救、死去但得以再生之人的團契。45
雖然如此,巴特卻提醒教會縱然是有希望的團契,但教會與上帝國之間仍然是有無限的對立,在這對立之中,無人可以站在有理的一方,人只能誠惶誠恐地思念這位對立中的有理者。46 因此巴特進而指出,無人不需要希望,故當我們面對教會的奧秘時,就是面對上帝的奧秘,所以我們唯有都面向着希望。47 至於教會和現世的關係,巴特就認為兩者不應被理解為歷史的關係,而是辯證的關係,因為人不能被分成為被選和被棄的,教會亦不能和現世分開,因為上帝的可能是對人的不可能性的接納(receiving),而非拒絕(rejection)。48 所以巴特反對教會站在倫理的高地,勸勉教會不要「看自己過於自已所當看的」,並且要擔當軟弱者的軟弱,否則雅各的教會會結束這些站在高地的教會。49 能夠做到這樣,教會才能做到巴特所言的「那裏有希望,都是對於教會的希望。」50
三、
《教會教義學》中的教會論
巴特在《<羅馬書>釋義》中闡述了其深具批判性的教會觀,天主教神學家卡爾·亞當(Karl Adam)認為《<羅馬書>釋義》就像「一枚投在眾神學家園地的炸彈」,51 事實上,它同樣也是「一枚投在眾教會園地上的炸彈」。但要全面了解巴特的教會觀,我們需要進入巴特的另一代表作《教會教義學》(Church Dogmatic)。《教會教義學》共長達八千多頁,是巴特從一九年起至一九六八年離世時,歷時三十七年仍未完全寫成的神學巨著。在深入探討《教會教義學》以先,有兩點我們需要先交代一下。
首先,從《教會教義學》的書名我們已可見出,巴特寫作教義學的目的是為着教會而寫的,對比起他於一九二四完成的《哥廷根教義學:基督宗教的指導》(The Gottingen Dogmatics: Instruction in the Christian Religion)52,和一九二七出版的《基督教教義學大鋼》(Die christliche Dogmatik im Entwurf)53,巴特選取的字眼和用意是明顯不過的,正如施沃貝爾(Christoph Schwöbel)指出,巴特對教義學的理解已不再是集中在基督教的論述,而是教會。54這 誠如巴特本人所言:「教義學是基督教教會其獨特的上帝論述之科學性自我檢視」。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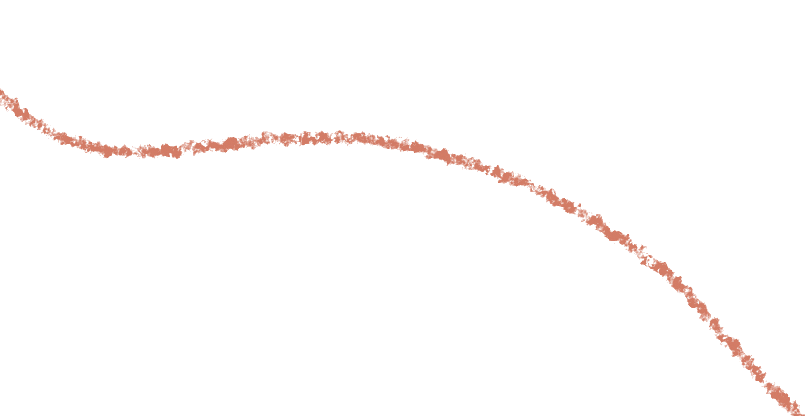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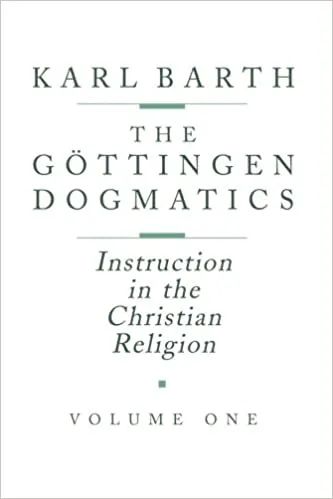

其次是在《教會教義學》中,巴特表面上並沒有一章專門闡述「教會論」(ecclesiology)的教義,但事情上巴特處理其教會論是主要連同《教會教義學》中的揀選論(doctrine of election)和復和論(reconciliation)一併討論的,以及見於在不同的章節之中,所涉及的範圍包括上帝的啟示、基督、聖靈、揀選、複和等。正如希利(Nicholas M. Healy)就指出,雖然巴特在《教會教義學》中沒有明確地說明教會論的原則,但他是清楚不過地寫下了其教會論關鍵的和形式的方針。56
現在我們正式進入探討《教會教義學》中的教會論。巴特在《教會教義學》第一部的開首便指出,神學是教會的功能,是基督教教會獨特的上帝論述,並指出教會就是「耶穌基督:是上帝在其自己的啟示,以及與人的複和。」57 巴特在這裏批評自由神學和羅馬天主教會都欠缺了這種上帝的啟示,上帝的道的神學;前者漠視了上帝的道,而後者則把聖禮放置在上帝的道之上。58 巴特強調,教會是上帝的純粹的行為(actus purus),是神聖行動的自我起源,這行動唯有在上帝自己才能被理解,而並非一種「人學」(anthropology)。59
由於巴特認為,教會是「耶穌基督:是上帝在其自己的啟示,以及與人的復和」,故此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他將教會論與基督、揀選以及複和等一併討論。這點正如他的教義學是被公認為「基督中心的」(Christo-centric),也是他本人所承認的,60 然而巴特亦同時強調,他所認為的這種基督論並不是一種狹義的基督論,就如他在《教會教義學》中指出,「教義學必須實際上是基督論的,並且只屬基督論,但並不是一種狹義的基督論。」61 故此,說巴特的教會論是「基督論的教會論」(Christological Ecclesiology)也是明顯不過的。62
巴特指出,教會是耶穌基督自己在地上歷史的(earthly-historical)存在形式,是耶穌基督的身體(body of Jesus Christ),並透過聖靈發出的能力而創造和持續更新。63 他又指出,這是人類歷史上獨特的元素,耶穌基督成為了基督徒的群體,成為了這個身體,這個群體的頭。64 因此教會屬於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亦屬於她;因為他在,所以她在,反之亦然。65 對巴特來說,這甚至是第三度空間的奧秘,是唯有在信仰之內才可以得見的奧秘。66
巴克利(James J. Buckley)指出,巴特論耶穌基督的揀選表明了一種基督教群體永恆和持續的揀選,是一個「居間和居間的」(mediate and mediating)群體,並且這群體不能與以色列和教會區別出來的。67 巴特引用大量《聖經》有關「基督的身體」的經文作為其教會觀的定義,68 並且他不止一次強調,有關於教會的論述都是基督論的,並唯有其本身是教會論的。69 希利就指出,巴特採用「身體」一字的意思,並不是指教會是一種作為「社會的身體」(social body)。70相反他指出,巴特所指的是教會是衍生自基督自己的身體,而非指肉身上的身體,因為基督肉身上的身體已在各各他山上被釘死了。71 假如教會是指這個肉身上的身體的話,教會就只是一個「死的身體」(dead body),並且沒有聖靈的參與的話,基督的身體以及在其中的人,都只是死的。72 因此巴特認為,唯有基督透過聖靈從死裏復活,我們才能「合法地等同基督的身體與基督徒群體,這個有形的(visible)人類群體之無形的(invisible)真實」。73
巴特以「聖靈與基督徒群體的建立」(the Holy Spirit and upbuilding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為題,說明教會與基督及聖靈的關係。他指出,聖靈作為賦予教會生命的能力,是耶穌的自我證明(self-attestation),在這自我證明中,耶穌啟示和彰顯他自己予地上存活的世人,並且與世人聯合,也給予世人與他聯合的知識。74 有了這個知識,世人發現他們無論在此時此地,他們都可以與耶穌聯合,也因此得以和其他世人聯合。75 這樣,透過這種自我證明、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和自我分與(self-impartation),耶穌透過聖靈的大能建立起教會這個群體。76 教會在此世的存活和成長預表着與上帝復和了新人,因此教會與社會團體,縱然是宗教的團體都不一樣,他們唯獨與耶穌並透過耶穌得以聯合,並和其他人聯合,成為耶穌的心意和目的之實現。77 巴特強調教會的存在是唯獨作為耶穌在地上所完成的工作,這工作在教會中得以進行,並透過教會在世界中進行,這一切都是唯獨因為耶穌,並且唯有他才能使教會成為真正的實有。78 故此巴特說:「在他(耶穌)不是的,她(教會)也不是,在他(耶穌)之中所不是的,她(教會)也不是他(耶穌)的群體」。79
對於耶穌基督是教會這一論述,巴特強調它的次序是不可顛倒的,因為教會並不是耶穌基督,但耶穌基督卻是教會。80 同樣地,上帝國也一樣,上帝國是教會,但教會並不是上帝國。81 此外,巴特指出,教會不單不是上帝國,也不會在上帝國於歷史的終末來臨以先成為上帝國,但教會因着祈求上帝國的來臨,在歷史終結的一端,上帝國是已經真正在世上、時間和歷史之中。82 這裏可見,巴特不單把教會與基督、揀選、聖靈及複和的教義串連起來,而且也與終末論(eschatology)連上。
這裏要留意的是,每當巴特談到教會或基督徒群體時,都是指向每一個基督徒而言的,並不是一個純粹抽象的觀念或個別的信徒及教會機構,都是整體教會的每一個體。83 巴特強調聖靈在教會的工作,是以人類活動的形式在人間出現,因此它不單單是歷史的活動,更是發生在特定的歷史之中,是教會從永活的耶穌基督透過聖靈而得以聚集。84 基於這個理解,巴特提出了五個他認為教會的所是:
從以上五點我們可見出,巴特的教會觀非常強調人的活動,兩者是不能分開來理解的。他認為,這群體毫無疑問地不是存在的狀態或制度,而是存在的事件和工作,是關於人的活動的。86 巴特借用宗教改革家茨溫利(Ulrich Zwingli)和路德的講法來說明他對這個群體的看法,他指出哪裏有這個意識,哪裏就有上帝的道所誕生的教會(茨溫利),又指出上帝的道孕育出每一個基督徒,並啟迪每位信徒的心靈,讓信徒能抓緊、接受和持守上帝的道(路德)。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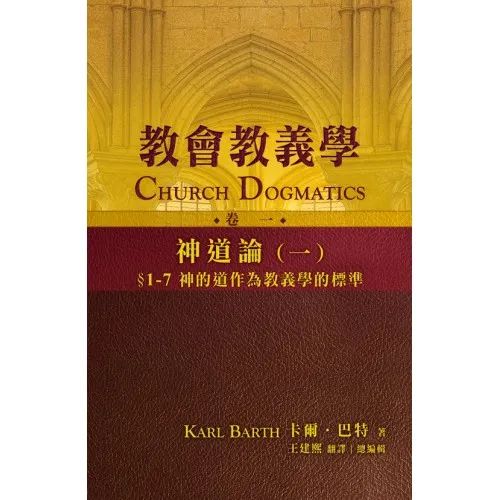
此外,巴特上承宗教改革家們,反對把教會視為「柏拉圖式的理想國」(civitas platonica),指出教會從來不曾亦不會是「無形的教會」(invisible church)。88 巴特認為,這種無形的教會觀是一種「教會幻影說」(ecclesiastical docetism),忽視教會在地上歷史的可見性,如同基督幻影說一樣是不可能的。89 他又強調,如果無形沒有成為有形的(visible),又或者基督徒群體沒有成為地上歷史的形式的話,那麼聖靈透過耶穌基督的工作都不會發生。90 因此他認為,每一個基督徒唯有在時間和歷史之中才可以成為道的實踐者,並因此成為對所有人的具體和可見的人之形式。91 是故對巴特來說,教會並不可能是一個純粹抽象的觀念或形式,而是在歷史時空之中,教會內每一個成員的個體關係,透過道的共同行動使他們融為一體,成為一個具體的形式,讓世人得見。92 這點正如巴特在《〈羅馬書〉釋義》中指出,古往今來所有地上可見的、可知的和可能的教會,包括耶路撒冷的、羅馬的、威登堡的、日內瓦的,以及當時的德國教會,都只是以掃的教會,是有形可見的教會。93
巴特繼而指出,有形的教會不能忽略真實和整體的人,包括他們的魂靈和肉身,教會不能因為復活的應許未臨到他們而忽略他們的希望。94 因為教會所認信的是無形信仰,是有形的信仰之秘,若然教會不能做到這點,教會只會是純粹理論上和抽象的教會。95 巴特這裏的意思並不是指,有形教會就是真正或完美的教會,這點從他對教會的批判已清楚不過,他所要反對是「教會幻影說」,是理論和抽象的教會論。事實上,巴特就同樣在《教會教義學》中指出,真正的教會是從未曾在歷史中得到完滿的,她只是暫時性地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代表基督在世的工作。96 這點與他早年對雅各的教會的論述相同。
說巴特前期教會論的重點是批判,而後期的重點則落在建構上,這一說法大致而言是合理的,但我們卻不能否定巴特後期的教會論也同樣具備批判的精神和元素。對巴特來說,以掃的教會仍然是以掃的教會,並不是雅各的教會。事實上,巴特後期仍然堅持教會要在社會上作基督的見證,勇於對不公義的事情,以至對教會提出批評。正如他本人就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公開反對核武擴散,寫成了〈原子戰爭的立場宣言〉(Atomic War as Status Confessionis),97 又於六零年代公開反對越戰,指出當時教會「只說『耶穌復活了』,但對越戰卻默不作聲,這是不夠的」。98 此外,巴特在《教會教義學》中的教會論也具備一定的批判性,仍然與他前期的教會觀一樣具批判色彩,多次指出教會作為人的實體,是連串罪人的活動,並且沒有比這更多一點,認為「地上的眾聖徒群體,也同樣都只是眾罪人的群體」。99
而對巴特來說,教會的角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上帝和自己的鄰舍作見證。他指出教會不是要謀求自己的滿足,或追求自我的發展,同樣地,作基督徒也不是為自己去謀求福祉,而是為全世界和人類的救恩。100 巴特又指出,教會的任務不是別的工作,而只是見證上帝藉基督與人複和。101 他認為,耶穌基督呼召門徒作他的跟隨者,他們便沒有選擇的餘地,唯有以行動作為回應去跟隨他,與他一同作宣告者,就是宣告上帝藉基督與人複和的訊息。102 因此巴特也指出,成功不是教會追求的目標,而是作忠心的見證者,103 又提醒教會接受一個事實,就是教會永遠都只會是小眾(small minority)。104
四、
教會合一與政治公共問題
在交待過巴特前後期的教會論後,我們再看一下兩點相關的問題,好使對巴特的教會論有更全面的理解,這兩方面分別是他如何看教會合一問題,以及對政治和公共事務的態度。要說明巴特對這兩點的看法,都不是用三言兩語就可交待完的,由於本文的篇幅所限,我們只能作一個簡略的說明。在教會合一方面,巴特本人與普世合一運動的參與者之評價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巴特認為自己只算是個合一神學(ecumenical theology)的邊緣角色(Randfigur),然而德國教會合一運動領袖卻認為他是「二十世紀普世合一運動的先鋒」(Wegbereiter de Okumene des20. Jahrhunderts)。105
在巴特兩本最重要的著作《〈羅馬書〉釋義》和《教會教義學》中,我們可看出巴特都一直視自由神學和羅馬天主教作為批判的對象,除了上文已經提到,巴特認為兩者都漠視上帝的道以外,另一個巴特的批判是兩者都對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的肯定。巴特開始與天主教的神學家和普世合一運動的領袖交往是始於哥廷根大學,期間他認識了耶穌會的神學家普日瓦拉(Erich Przywara)和普世合一運動的領袖胡夫特(Visser’t Hooft)及莫裏(Pierre Maury),並且聯合普世合一運動的組織對抗納粹主義,可是後來巴特對這種無力的反抗表示失望。106及至二十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巴特與多位年青的天主教神學家如巴爾塔隆(Hans Urs von Balthasar)、107 漢斯•昆(Hans Küng)108等交往,又多次與教宗保祿六世(Pope Paul VI)的書信往來,交換對越戰和冷戰的看法,可見巴特雖然對羅馬天主教會時有批評,但其實雙方的關係並不是想像中的對立。109


更重要的是,巴特的教會論對普世合一運動的確非常有影響力,巴特指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認為假如教會聚集在一起是透過聖靈的話,世上理應只有一個單一的教會,一個單一的存有。110 巴特指出,聖靈應許過會與教會在一起,並因着他和他的名而使所有教會都聚集在一起,他治理教會(church),也治理眾教會(churches),並且他是眾教會合一的基礎和確據。111 故此巴特認為,我們不能稱眾教會的多元現象有任何合法性,這種眾教會的多元性更是違反了《以弗所書》中合而為一的精神,也違反了「至一教會的信條」(credo unam ecclesiam)。112 巴特認為,沒有任何一個神學上、靈性上或《聖經》上合理的理由,去解釋教會分裂成如此多元的現象,以及教會彼此之間對內及對外的排斥。113 巴特甚至斷言,眾教會的多元現象是意味着有眾多個主、眾多個靈和眾多個上帝的多元性。114 巴特指出,世間可以有好的羅馬天主教徒、好的改革宗信徒、好的正教會信徒或好的浸信會信徒,但不能相信他們都是好的基督徒,因為他們都沒有誠實認真地相信、知道、認識和認信「至一的教會」。115 他認為,假如教會之間仍然有小圈子和互相的排斥,「至一的教會」是不可能存在的,因為她不可能排斥其他教會,也不可能是眾多教會之中的一。116
至於巴特對政治及公共事務的看法,巴特曾經在〈基督徒群體與公民社會〉(Christian Community and Civil Community)中有這樣的看法:「教會並不相信和服從任何政治體制或現實,而是相信和服從道(Word)的權能,就是上帝堅固萬有,包括一切與政治有關的事情」。117 要談巴特如何看待這問題,先要知道巴特的用意何在,否則很容易做出片面的誤解。118 巴特固然一生中多次參與過不同的政治社會運動,無論是早年參加宗教社會主義(Religious Socialism)和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到後來成為反對納粹主義的〈巴門宣言〉(Barmen Confession)之起草人、到後來反對共產主義、越戰等,都顯示出巴特對政治社會的關心,甚至作為教會的領袖公開反對極權政治。但另一方面,巴特又多番強調教會只是上帝的群體,並無一套既定的政治理論,119 甚至在《〈羅馬書〉釋義》中認同要「順服在上的」,反對一切形式的革命,顯露出一種與政治不相干涉或保守的政治立場。120 然而,當我們了解到巴特的真正用心所在,我們便會更明白他對這問題的看法。
在〈基督徒群體與公民社會〉一文中,巴特一開始便表明他之所以關心教會與政府,並不是關心政府的制度和部門的問題,而是當中的人以及個體的關係並相關的公共事務。121 他指出,教會在世上本身就已經屬公民社會,並且基督徒在世上作為鹽和光。無論是因為教會已認識真理或無論教會為在上者祈求,教會的存在就已經是政治的。122 巴特認為,對於教會來說,一方面教會知道上帝的國和恩典,也知道人的罪和人的可怕,123 另一方面教會與公民社會處於同一個世界,分享着共同的益處,教會雖然作為內圈,而公民社會作為外圈,但對教會來說兩者的中心都同樣是耶穌基督,所以教會自我順從(Subordination,《羅馬書》13∶1)於公民社會。巴特指出順從在這裏的意思是教會與公民社會和非信徒一樣,都對社會有必須的共同責任。124
然而,巴特強調教會必須仍然是教會,必須堅守着基督國度的內圈,縱然她與公民社會有不能置之不顧的共同責任,但同時這責任也不可成為教會追求的目標。125 巴特這觀點其實早見於《〈羅馬書〉釋義》中,這正是他如何看待政治社會的用意所在。他強調基督教的倫理就是「上帝是上帝」,126 上帝是一切秩序的揚棄,包括國家、教會、權利、社會、家庭,127 所以一切的權柄是出於上帝,要順服的也是順服上帝,上帝才是真正的革命、秩序、權力的源頭。128 教會既是出於上帝,順服上帝的倫理,故此巴特認為教會自身並不是其目的,信徒也不是統治者,而是要成為服侍者,服侍上帝和人。129 此外巴特亦強調,教會不能簡單地把上帝國視為政治的領域,而是提醒人們甚麼是上帝國,提醒人們那位已來了並且將會再來的耶穌基督。130 教會並不是上帝國,只是她認識、盼望和相信上帝國,並以基督的名祈求,又傳揚他的名。131 故此教會並不是中立的,也不是無力的,教會若然負起她的政治責任,就要背負起政府所不能背負的,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並提醒政府他不能提醒自己的。132 所以教會在政治領域上,必須保護弱勢,堅持社會公義,並選擇最能維持社會公義的制度;133 教會永遠不能站在強權或暴政的一方,並且透過尋求和建立法例既限制又維護人。134 真正的教會必須是真正的國家的模範和原型。135 就政治制度而言,巴特強調民主制度並不必然就等同基督教的觀點,因為民主制度亦有犯錯的可能,但他同時承認民主政制是最接近基督教的觀點,因而教會與公民社會在這方面有明顯的親和。136 此外巴特亦語重心長地提醒教會,每當要表達任何公告時要非常謹慎和清楚地選擇言詞,尤其不要讓人一個印象教會只關心一些非政治的倫理議題,例如賭博、醉酒或褻瀆安息日等狹義的宗教性和倫理性議題。137
五、
對香港教會的提醒
香港教會大部分都深受福音主義(evangelism)和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影響,甚至以此為正統信仰的指標。這種信仰形態導致信仰的個人化,強調耶穌作為「個人心裏的救主」、「個人與上帝的關係」。無可否認這形態對教會增長和個人佈道非常見效,然而對巴特而言,這種忽略群體和社會的信仰並不是真正的「福音」,因為福音永遠是上帝國的提醒,是「上帝不可能的可能性」,是「與人手所做的對立」,是揚棄教會的福音。138 事實上,近年部分福音派教會也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在社會公共事務方面也開始變得積極的投入,然而她們部分的做法和關注的議題,都是巴特強烈批判或帶有保留的。正如上文指出,巴特反對教會站在道德的高地,「看自己過於自己所當看的」,總要接納,而非拒絕,這樣教會才會有希望。139 然而,近年香港教會最積極關心的社會議題都是巴特所告誡的非政治的倫理議題,如足球搏彩活動規範化、同性戀議題(如反對制定「反性傾向歧視條例」)、色情及不雅資訊氾濫等,但對其他的政治問題,如政治發展、司法的問題(兩次的人大釋法、公安條例、人權法的訂定、制定最低工資等)則顯得異常冷淡。這不單未能真正完成教會的社會負任,提醒人們甚麼是上帝國,往往有更大的反效果,使福音對社會變得無力和失效,甚至令教外人士反感。140
其次,香港教會普遍不注重和理解教會合一的重要性,更動輒出現分裂和內部的爭端,這現象從八十年代以後堂會的數目不斷增加,而信徒的人數卻未有顯著的遞增而得知。141 姑勿論很多教會對天主教和正教會都視為異教或異端,就連很多更正教的不同教會,都有互相排斥的情況,近年最明顯不過的如對五旬宗教會、疑似靈恩或有靈恩傾向的教會,又或部分教會不承認其他宗派的洗禮,使本來象徽合一的聖餐結果成為互相拒絕的武器,甚至更有因着某些社會議題的分歧看法而彼此咒罵!142 這都不是「至一的教會」應有的表現,相反這現象更如同巴特所斷言,是「有眾多個主、眾多個靈,和眾多個上帝的多元性」。143
此外,近年香港教會出現了不少超大型教會(mega-church),這現象不知是喜是愛,因為她們增長之快,一方面是佈道和培訓的成效,但另一方面很重要的是從其他大小堂會中吸納過來的信徒。144 至於其他小堂會便紛紛學效這些超大型教會的模式,不少教會機構相繼邀請這些超大型教會的領袖分享成功之道,甚至出版了專門的研究和分析她們的成功法門。145 姑勿論小堂會是否能學效甚至複製這些成功之道,但教會的目標是否追求這些「成功」?從以上的分析可見,就巴特而言這明顯是否定的。香港某些超大型教會往往只集中在某幾類重點的事工,然而就一些「沒有回報」的工作上,例如老人、社關、照護低下階層或殘疾人士,以至文化塑造、神學教育等都不見得有相應的影響力和貢獻,有的甚至從不沾手。巴特認為,教會真正的目的是服侍,是讓人們知道甚麼是上帝國;教會不是要謀求自己的滿足,或追求自我的發展,又提醒教會接受一個事實,就是教會永遠都只會是小眾(small minority)。146 假如這些超大型教會和其他小教會都能做到巴特所說的話,都絕對是一件美事,然而香港的教會在這方面卻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仍有很多需改善的地方。盲目的追求教會的增長、數位化的管理、迎合大眾的口味,卻不是以上帝國為準則,忽視社會公義和文化的塑/改造,只會造成教會的「麥當奴化」(McDonaldization)。147
最後,巴特在寫作《〈羅馬書〉釋義》和《教會教義學》第一部之時,他處身於國家民族主義最高漲的年頭,巴特勇於聯同當時的認信教會(Confessional Church)提出批判,向政權以及被民族主義沖昏了頭腦的教會說「不」。……而且的確,香港教會要處理問題是極不容易的,這也是巴特,以及過去無數聖徒也都同樣面對過的,面對這問題最重要的正如巴特再三地提醒我們:「上帝是上帝,教會是教會」。
六、
結論
總結而言,巴特全然是一位教會的神學家,他的教會觀與其整個神學體系都非常緊扣,是了解他整體思想不可或缺的鑰匙。就巴特前期和後期的教會論,無論對教會還是對社會都是具有深切的批判性,並且對當代,尤其香港的教會處境都一點也不過時,是我們不能忽略的部分。


李駿康博士(Dr LI Chun Hong),PhD, M.Phil, BA (CUHK),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學術興趣为基督教神學、宗教研究方法(宗教社會學、宗教哲學等)、宗教與當代社會、世界宗教、宗教/派對話、通識為本的經典教學等。出版書籍(2016)【中文翻譯】史葛.萊特。《羅梅洛:與受壓者同行的牧者》。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中文翻譯】保羅.愛華士。《多元與共融:普世合一神學的重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如果我告訴你,你還會愛我嗎》。香港:CUP出版。(2013)【合著】《社會企業:信仰實踐與反思》。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2)《在家不好:與流浪兒童在一起》。香港:CUP出版。(2011)《現代教會論類型學:自由、認信與顛覆》。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等。
——摘自香港中文大学官网
#往期相关阅读#
关注我们
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