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朋友向我推荐了刘擎教授的大作《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朋友高度认可这篇文章,认为此文对自由主义的辩护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我认真拜读了刘擎教授的大作,也认为此文可以算是自由主义的辩护词。我也很喜欢此文的文风:言之有物,针对性强;文笔简练,留有余地;不急不躁,平和冷静。
我能感受到刘擎教授的一片苦心,但我又不得不说,此文对自由主义的辩护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刘教授立论的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他既然承认甚至主张价值多元主义这个现实的大前提(虽然这种承认和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可奈何的),他试图为自由主义建立价值根基的努力就注定是无谓的,因为他的大前提已经消解了他建构的努力。简言之,刘教授是在自己否定自己,至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任何共同体的存在和有效运作都有赖于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包括对何为良好生活的理解),后者是前者的根基;自由主义既然标榜“价值中立”和“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让人们自由选择自己认可的价值观,所以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无根的自由,它只具有游戏规则的意义。
对此,刘教授的辩护是:“声称‘只要自己愿意,随便怎么选择都行’,这是类似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宣言,而不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自主性。”
“那么,又如何解释所谓‘价值中立’和‘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呢?‘中立’难道不是对所有价值立场都抱有‘不置可否’的相对主义态度吗?正当的优先性难道不是表明了对于‘善的观念’(the conception of the good)无话可说或(至少)漠不关心吗?这两个原则(或近似的说法)是一些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张,但它们非常容易引起(尤其是草率读者的)误解。
“首先,‘中立性’(neutrality)这个术语必须放置在特定的问题与脉络中理解。正如罗纳德·德沃金和拉莫尔反复阐明的那样,‘中立性’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一项原则,针对这样一个特定的问题:如何在政治上应对公民在各种宗教或整全性学说之间的‘合理分歧’或‘多元主义的事实’。政治自由主义主张,首先要在政治上以‘平等的’或‘不偏袒’(impartial)的方式来对待‘合理的分歧’。如果‘价值判断’意味着肯认什么和否定什么价值,那么中立性原则本身就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断言(moral assertion)——它肯认了‘平等的尊重’这项价值,并要求在政治领域的价值排序中将此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其次,平等尊重的中立性原则只适用于具有“合理分歧”的善的观念,这意味着它会以否定的(而不是‘中立’的)态度去对待某些不合理的关于善的主张(比如,‘美好的生活必须让别人做自己的奴隶’之类)。再次,‘平等尊重’是在政治原则的意义上才具有优先性,因为政治原则不同于其他一般的道德原则,它具有明确的强制性,因此需要最低限度的共识。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人可能信奉一套自由主义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原则,并认为这比其他宗教和学说更为合理,但他同时相信,将这套自认为正确的价值原则(作为政治原则)强加给其他思想异己的公民同胞是错误的。这究竟是自由主义的谦逊还是傲慢?而这在什么意义上又涉嫌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
“同样,所谓‘正当优先于善’指的是在特定意义上——针对政治制度基本结构而言——正当具有优先性。首先,政治生活是共同的生活,现代政体应当尽力维护各种具有合理争议的人生理想能够和平共存。我们大概都会同意‘基本的温饱’对于人的生存具有优先性,但这绝不意味着温饱问题就是人类经济学中唯一的问题或总是最重要的问题。类似的,正当之优先性是作为维持共同政治生活之必要条件的优先性,这绝不意味(即便在政治领域中)‘好坏’(善的)问题可以被置之不顾或其重要性总是次于‘对错’(正当)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罗尔斯等人提出的)正当的优先性:各种善的观念总是会,并且应该在政治领域出场,正当的优先性不是取消或藐视善的价值,不是消除善的观念具有的政治内涵,也不是否认善对于政治生活的激发和指导作用。正如只有基本温饱的人类生活就不是真正的人类生活,同样,只有正当的政治生活也不再是政治生活。正当的优先性只是对所有基于善的政治主张施加了一种限制——服从公共理性要求的‘所有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与基本自由’。换言之,它是作为必要条件来限制各种善的观念在政治领域中的力量。限制似乎是一个‘消极’的语词,但它同时具有积极的面向。因为正是由于这种限制,才允容了许许多多善的观念得以获得政治表达,否则它们会被处于霸权地位的整全性学说——在当代就是整全性的自由主义本身——压制和排斥。这正是罗尔斯从早期的‘正义论’转向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动机。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正当的优先性:恰恰是由于‘何为善,何为有意义的人生’之类的问题对于每个人的政治、道德和精神生活都极为重要,所以我们才不能(在合理分歧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轻率地给出一个武断的‘标准答案’,并将这个答案强加给所有人。所以,‘正当优先于善’体现出对善的价值的重视而不是藐视。
“让各种(合理的)善的观念在政治领域中和平共存,这当然不错。但这并没有解决‘我们应当依据何种善的观念来生活’这一问题。如何来对待这一重要问题?可以想象一种‘自由主义’的方式,认为‘这个问题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必须完全交给个人自己去选择和决定’。当然,也可以想象另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方式,认为‘这个问题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我们绝对无法交给个人去选择,而要由贤人、传统或宗教教义来决定’。……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主性,这是因为个人的生活不得不是他自己所过的生活,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因此人生问题首先要交给个人来选择。但这里‘首先’的含义既不是‘完全’也不是‘任意’,而是一种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要求:个人的选择是必要的、不可缺失的、无可替代的。但与此同时,这种必要的个人选择不可能完全由个人单独做出,也不应该是任意的。自由主义在主张自主性的同时,完全承认人是文化、历史、语言和社会之中的个人,而并非主张所谓‘原子化的’个人。实际上没有任何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可所谓‘原子化个人’的观念,这种误解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已经得到了澄清。但(不幸的是)这种不实之词仍然在流传。
“选择总是依据某种标准的选择。选择的标准可能是多元的、可争议的,但绝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个人可以独自创造的。自由主义相信‘我愿意’是一个重要且必要的标准,但不承认‘只要我愿意’就足以构成标准本身。即便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因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倾向于强调没有‘我愿意’是不行的(必要条件),但并没有声称‘只要我愿意’就够了(充分条件)。这正是自由多元主义区别于虚无主义的要点所在。前者相信,对于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可能有多种(彼此可能冲突,也可能兼容),但一定会有些答案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判断正误的标准是什么);而对后者而言,所有答案都一样正确有效(或错误无效),一切都无所谓对错。”

刘教授力图证明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主义不是存在主义,不是虚无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个庞大的、也是庞杂的思想体系,所以与其说刘教授的上述观点是代表整个自由主义,不如说他阐述的只是他自己认可的那一种自由主义(当然也没有人能代表所谓整个自由主义)。
那么,仅就刘教授所认可的这种自由主义,我想提出两个问题,请刘教授思考:
1. 如刘教授所言,“平等尊重的中立性原则只适用于具有‘合理分歧’的善的观念,这意味着它会以否定的(而不是‘中立’的)态度去对待某些不合理的关于善的主张(比如,‘美好的生活必须让别人做自己的奴隶’之类)”;问题在于,为什么“平等尊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为什么奴隶制在现代社会是不合理的?换言之,什么叫合理不合理?理从何来?如果理不存在神圣的源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为什么要守理?
2. 刘教授承认“正当优先于善”,那什么是正当?谁来定义正当?你认为正当的秩序别人认为不正当怎么办?大多数人认为正当就必然正当吗?那又如何理解“多数人的暴政”?希特勒是通过“正当”的选举程序当选的,纳粹党认为屠杀犹太人正是正当行为,事实已经多次证明,抛开“善”的“正当”其实不就是邪恶吗?既然如此,怎么还存在“正当优先于善”?老实说,正当与善根本就是、只是同一个存在——上帝,因为上帝既是公义本身,又是善本身。抛开上帝,谁能定义正当?
事实上,刘教授并不认为仅有自由就够了,自由主义也应该有价值标准,他也“尝试”为自由主义列举一个明确的价值清单:
“(1)自由主义有理由反对纵欲(比如酗酒、吸毒),因为这会使人陷入“不由自主”的奴役状态,因此支持审慎节制地对待生物本能欲望(自主性原则,理性反思原则);
“(2)自由主义有理由反对欺诈、利用和伤害他人,因而支持真诚、平等与互惠互利(密尔的“伤害原则”,康德的“人是目的”原则);
“(3)自由主义有理由反对迫害与压制异己信念,支持理解、宽容和商谈(洛克的“宽容原则”,当代自由主义的理性对话原则);
“(4)自由主义可以有理由反对平庸和蒙昧无知,而鼓励卓越和追求真理(密尔的幸福论);
“(5)自由主义甚至可以有理由支持为共同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边沁的“功利主义”及其当代发展的精致版本)……”
自由既然成为一种主义,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其他价值就应该与自由之间存在某种逻辑关联,否则这种列举就是单一的自由主义者的个人喜好而已。但显然,刘教授所列举的上述价值并不是都与自由这一价值之间存在较强的逻辑关联。至少,他没有论证上述价值与自由之间存在这种较强的逻辑关联。
或许是因其如此,刘教授对他所罗列的这个清单并不自信,他说:“当然,并不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在生活实践中都能达到所有这些标准,正如不是每个教徒都能达到宗教教义所期待的道德水平。但这份不完整的清单多少揭示了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具有明确的价值标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道德主张在自由主义内部是有争议的,因为自由主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传统。所谓‘消极的自由主义’对于‘何为美好的生活’提供的指南非常有限,着眼于强调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积极的自由主义’则对人生意义提出了更为实质性的原则”。
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刘教授所罗列的价值标准,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标准,只是他这个自由主义者的标准。换言之,如果它有意义,也只有某种理论建构或个人憧憬的意义。仅就他所罗列的这五个标准而言,我也想依次提出五个追问:
1. 理性反思就能阻止人纵欲吗?
2. 为什么“人是目的”?
3. 宽容来自理性对话吗?狼和羊通过理性对话,就决定不吃掉羊了吗?
4. 什么叫“蒙昧无知”?什么叫“真理”?
5. 既然为了共同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如何通过功利计算来决定谁该为共同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谁有资格下此决定?又是多数人来决定吗?那又如何确保个人自由?
在我看来,刘教授的上述标准是支离的,因为自由主义确实是“无根”的。
其实,在《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一文的第二部分,刘教授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由主义是无根的。
他说:“直白地说,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即便承认它是某种标准,似乎总是让人感觉过于单薄,过于脆弱,过于松散,过于不稳定,以至于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称不上是一种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不会用‘无根的’(rootless)这个词来形容基督教、儒家或伊斯兰文明,而以此来形容自由主义似乎是恰当的,至少并不让人感到荒谬。”
他还从历史和哲学两个方面证明了自由主义何以无根:“自由主义兴起于欧洲的世俗化时代,不仅历史不够久远(至多不过四百年),而且明确地源自基督教文明传统,因此就历史渊源来说,自由主义是派生性的(derivative)而非源生性的(original),似乎无法成为一种‘根基’。再次,在哲学层面上,自由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实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是一种泰勒所说的‘自足的人本主义’(self-sufficing humanism),甚至是‘独占性的人本主义’(exclusive humanism)——‘不接受任何超越人类繁荣的终极目标,也不拥戴任何外在于这种繁荣的事物’。这是一种内在的(immanent)而非超越的(transcendent)哲学,诉诸人的理性以及基于理性的自主性原则。简言之,自由主义的历史过短,而且具有明确的派生性,其哲学放弃(若非完全否定)任何外在于人的超越性存在基础。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容易被视为‘无根的’。”
根基重要吗?刘教授也承认根基重要。既然根基重要,为自由主义打牢超验的根基不就行了吗?逻辑推进到这一步,刘教授却退缩了,他开始怀疑起重建超验根基如何可能的问题来了。按他的说法,根基只是一种“隐喻”,既然在“祛魅时代”的“多元主义事实”下不再可能重建超验的根基,那就换上并不那么坚固的根基——人的理性及善良意志——吧。
刘教授说:“独占性人本主义的信奉者可能断然否定这种追问(关于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的正当性,人的理性与善良意志就是终极性的,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更为形而上的基础,而各种形而上的基础观念(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相’,儒家的‘天道’还是基督教的上帝)恰恰是人自己的发明或建构。也有人会采取不可知论的回答,理性与善良意志基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还有人倾向于接受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与生俱来(自然)的’或者‘上帝赋予的’。对基督教徒而言,上帝是始源的和超越的,而人的理性和善良意志是派生的和内在的,只有前者才能作为后者的基础。”
于是,“……我们只能立足于此岸,立足于人类自身以及周遭可见的大自然。这是我们全部价值的来源,虽然总是不够确定可靠,却是我们唯一可能的资源。由此,我们获得了另一种确定性——放弃幻想所带来的确定性,并以此与世界的不确定共存。”
于是,“我们也可以换一种隐喻的方式。思想史的考证表明,自由主义无疑是基督教的儿子,带有基督教文明的血脉(基因)。但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在大地上行走,甚至远渡重洋来到异乡,他受到的欢迎与诋毁一样多。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在各种关于自由主义的考察中,我们看到了他多种不同的形象,以及(同样多的)对他应该如何的告诫与期望:效忠虔敬的儿子,叛逆出走的儿子,特立独行的儿子,自作主张的儿子,绝情弑父的儿子,投靠近邻的儿子,也还有迷途知返回到父亲怀抱的儿子……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无论再魅化(re-enchantment)的风暴如何强劲,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会见证许许多多不同的儿子。……”
让我用通俗的话来转述一下刘教授的意思:房子既然已经是危房,地基既然已经松动,立柱既然已经朽坏了,按说应该重修房子;但人们已经住习惯了,再加固地基、再换钢筋混凝土柱子已经不可能了,那就换一根没有烂透的木头柱子凑合着用得了。他不知道,这根看起来没有烂透的木柱——人的理性及善良意志——已经烂透了。
以取消根基的方法试图打牢根基,以悖逆上帝的自主选择试图获得自由,以与不确定性共存的方式来获得确定性,这不是南辕北辙又是什么呢?所以我要说,刘教授对自由主义的辩护其苦心可悯,但其行为可悲。这种可悲行为的思想源头,正是自由主义高举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实质是人的骄傲,以为人自己可以定善恶的标准。人本主义的鼻祖是谁?就是亚当夏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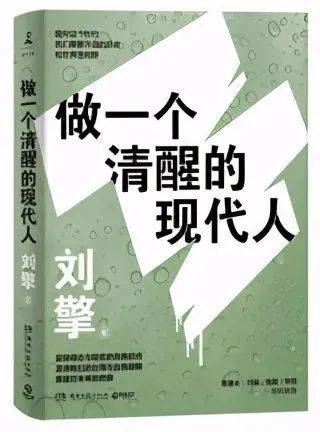
向我推荐刘教授大作的朋友问我:基督徒在政治领域应当如何对待非基督徒,或者说如何对待不同意见者?基督徒与自由主义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我答:基督徒应该爱人如己,当然不会强制别人信仰,也不会强制别人跟自己意见一致,这与自由主义并无不同。但基督徒与自由主义的不同是,前者认为信仰高于自由,信仰是自由的基础,信仰规制自由,后者认为存在没有上帝的自由,甚至主张没有上帝的自由。
朋友再问:其实刘擎老师说的很清楚,并非信仰和根基不重要,而是在事实上人们不存在共同信仰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共存的问题。就像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并非说人们对上帝的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而是说这种信仰已经无法成为社会的唯一权威和价值的尺度。这种多元主义是基本的社会现实,使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真实。
我答:上帝从来都没有死。如果全盘承认所谓社会现实,还谈什么改变呢?如果要改变,就不应该在祛魅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而应该复魅化。当然,这种复魅化不能依靠政治强力,只能依靠对人心的唤醒。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者不能唤醒“装睡”的人,他们恰恰就是“装睡”的人。
针对刘擎教授的《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杨鹏先生进行了很好的评论,现摘录金句如下:
1.“祛魅”,是想用“理性之魅”来取消“信仰之魅”,理性单脚跳的单脚舞蹈。启蒙运动-韦伯祛魅的单脚跳,跳出了什么?欧洲历史告诉了我们,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Fascism 和 Socialism。“祛魅”能“祛”出自由秩序?超越性信仰的真空,被民族和阶级填充。两希两希,信仰与理性,才是精神完整的健康人。
“祛魅”,岂是现代社会的事?中国精神史上,商鞅、荀子、韩非子早就“祛魅”了。他们“祛魅”了上帝、“祛魅”了上天,“祛魅”了“天命”,结果,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自我魅化,自称了”皇帝“。从”怯魅“上天到魅化皇帝,两者的密切关系,中国精神的舞台上早就表演过一大轮了。刘擎先生还在欣赏宇宙论上的“祛魅”,他不知道有可能是在大地上为秦始皇帝扫地?
2.跟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尼采的“上帝死了”-韦伯的“祛魅”而来的,是些什么东西?魅化的民族主义领袖和阶级主义领袖。从世界中“祛魅”绝对者,就是魅化人间领袖。
刘擎没有注意到的是,“理性主义”必导向对天才的崇拜。理性之本,就是发现数学关系,这是少数人。理性的竞争中,必无最终的平等可言。理性自主的自由主义,必导向理性的专制。信仰是大众的,理性是精英的。信仰有平等的聚合性,理性走向等级的撕裂性。美国民主的前提是平等,建立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凝聚力上。理性自由主义是等级,这就是理性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必然瓦解。
3.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有超越性依据的共同体自由主义,一种是无超越性依据的以自我理性为基础的个人化自由主义,后者没有共同体。
4.刘擎是自由的清晰的观察者,但当他的眼光越过“自由”,去寻视“自由的超越性依据”的时候,他就有些模糊了。从严复、胡适开始,中国式自由主义,就是唯物-科学式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以个人理性自主为基础的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自恋式自由主义。这种自恋式自由主义,表面上从西方而来,其实是中国佛道式以“自性”为中心,以己为佛为仙的自恋式自我主义。这种个人化自我主义基础上,根本建立不起共同体的自由秩序,而没有共同体的自由秩序,根本保护不了这种个人化自我主义。
5.理性的剪刀剪断信仰,就成了对信仰的“中立”。“中立”于上帝以后,还能“中立”于民族主义和阶级主义吗?
6. 不少自由主义朋友,不明白个人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关联,不明白共同体自由只能建立在超越性的共同体准则之上。他们总是把个人自由视为一切,不知道“共同体自由”这五个字。自由主义要继续生长,只有将根系扎进超越性依据的永恒之河流中,这样才能长出共同体自由秩序的果实。End
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可阅读刘擎教授的《被误解与被滥用的自由主义》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