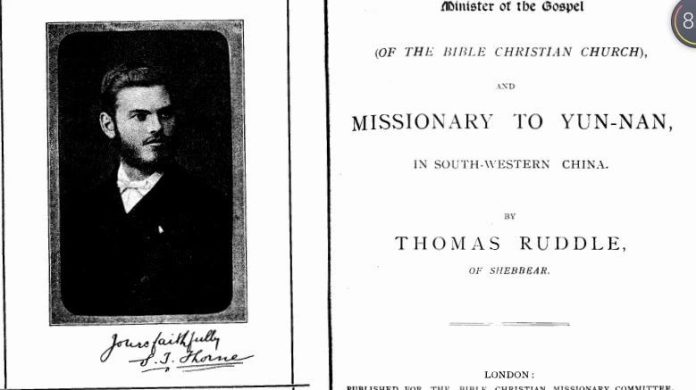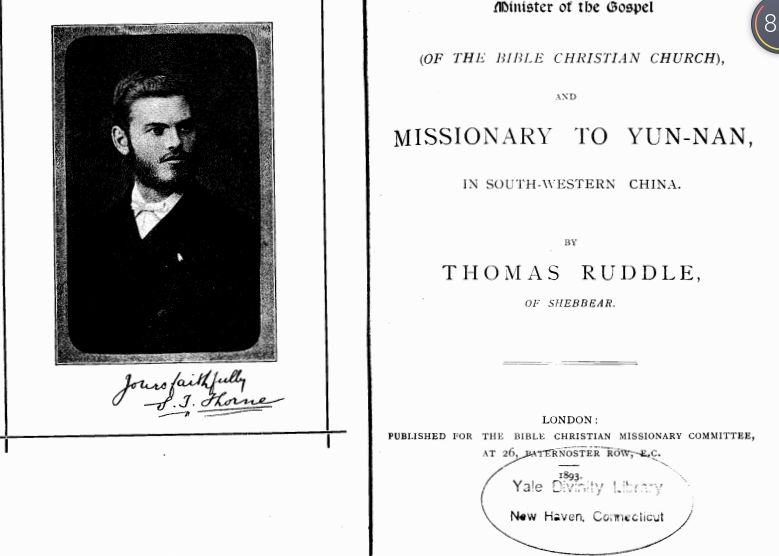
《云南的福音使者——多马·索恩传》
译者说明:
1891年9月,因为在昆明的柏格理牧师身体欠佳,教会决定让柏格理换个环境,来昭通事工。在昭通的多马·索恩夫妇决定开辟新的教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昭通东北部的彝良和镇雄一带。
1891年9月8日,索恩最后一次外出布道,中途疟疾发作。赶回昭通后于1891年9月22日离世归主。终年31岁。
索恩牧师离世13年之后,4个苗族人来到昭通找到柏格理牧师,从此开始石门坎传奇。13年前索恩用自己生命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
今天我在上海出差,利用休息时间翻译这章最后部分,才发现明天是多马·索恩牧师逝世127年。
该书由多马·索恩的老师多马·纳德写于1893年,安晓敏翻译、阿信校对。目前初校工作接近完成。
谨在微信公众号发出此文,纪念我们亲爱的多马·索恩牧师离世127年。荣耀归于上帝!
特别说明:如发现译文中有语句不通顺的地方请留言提醒。
节选:《云南的福音使者:多马·索恩传》第14章:“最后的巡回与归家”:
下面的叙述来自索恩夫人露易丝:
怀抱着扩展教区事工,让福音进入未得之地的激情,我亲爱的丈夫索恩决定前往昭通东部的镇雄(Chen-hsiong)巡回布道。这是一个从未有新教宣教士进入的地方。
他的计划是巡回走访,途经角奎(Ko-kuei)到奎香(Kuei-hsiang),在奎香与一周后从昭通出发,赶往那里的英国海外圣经公会(B&F.B.S.D)中国售书员藤先生(Mr. Teng)汇合,同赴镇雄。藤先生是重庆人,他计划取道镇雄回老家一趟。鉴于索恩渴望尽快地想去镇雄看看,我们认为有藤先生陪同真是天赐良机。
1891年9月8日,礼拜二,索恩、小马弟兄、杨开荣(Yang-kai-yung)三人一早出发。马弟兄是回族人,已经信了耶稣。稀罕的是,临行前的两三天,索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很平静,因为相信这是神的旨意,但和以前的出行前相比,总感觉这次提不起精神来。他好几次告诉我:“真想带着你一起走!”,“这次巡回,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哎,有你同行多好!”
9月7日,礼拜一,出发前的头一日。他忙了一整天,晚上给我说他感觉异常疲倦。礼拜二早上起来,他的身体还是没有恢复。我安慰自己说,以前每次身体不适,外出旅行总能让他好起来。我希望这次也会这样。
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回来。而且,会突然离我们而去!
9月8日,他们只走了25里路(8英里)。第二天他写了便笺给我:“这是我迄今为止住过的最糟糕的旅店。看到我这样说,你应该能猜想到它会是个什么样子。房子的三面墙壁由树枝凑成,光线从枝条间直透进来。这趟旅行我倍感孤独,但我们是为了最美好的事业。我已经给这些人讲了耶稣,并引导他们向天父祷告。周四晚我们赶到毛坪(Mao-ping),以便在礼拜五的赶场日街头布道。真希望你和我在一起,多为我们祷告!
9月12日,礼拜六。早上7点,他从角奎写信给我:“这次巡回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开心,我想着或许是因为我不得不和你分别很长一段时间。除非你来奎香和我汇合,要不我最好从那里就返回昭通。我估计滕先生礼拜一(9月15日)从昭通出发之前,你不大可能收到这封信。但如果你收到了的话,就不要把我准备好托他带的书再带过来。由于我们错过了角奎的集市,书还剩下很多。昨天我们很晚才从毛坪出发,到达角奎时天已全黑了。我们计划下个礼拜天返回毛坪,可是我太疲惫了,感觉不太可能。如果你到礼拜天你还没有收到此信,你最好不要来奎香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因为我本应该昨晚寄信出去,今天大多数赶集的人都走了。如果欧伯雷斯弟兄不需要你协助工作,你可以来镇雄和我汇合。如果这样,我们两人就可以彼此照应,在乡间慢慢巡回布道。杨开荣这小家伙一路很开心,和我们同行的老马人也很不错。”
下面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信的时间是1891年9月13日夜里,他刚开始发烧时写的,寄自角奎:
1891年9月13日,礼拜天。夜里,角奎:
“亲爱的露易丝,今天来赶场的有好几千人,角奎我们一定还会再来。明天我们出发赶140里路去奎香,当地人告诉我礼拜三是那里的赶集日……今天我感觉不是很好,头疼。今天老马在街头布道,他讲了很多。昨天他告诉一个人他是穆斯林,一会又对另一个人说他已改信基督教,而且家族里有几十个人信了基督教。我公开表示异议后,他告诉听众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连我他也没算在内!”我问:“你刚才说得几十个基督徒指的都是哪些人?”他回答说:“我们学校里所有的男孩,帮工,老师,还有南门姓马的一家。”我希望他说话诚实些,也看出来他的确想脱离他以前的宗教信仰。我们要多多为此恒切祷告。小伙子看上去很开心,让我们满怀信心。
深爱你的丈夫 索恩
我们待会再读索恩夫人的信,先看看索恩写给传教会秘书I. B 万斯英的最后一封信,一封没有写完的信:
1891年9月13日,礼拜天,下午
尊敬的万牧师:
我礼拜二离家,到闸上(Cha-Shang)传道,和当地老百姓交流很愉快。第二天,我们离开从昭通往英国(上海?)的主道,进入一条岔道往山上爬。为我们扛行李的苦力是一个回族,自称相信基督,我觉得他说得很真诚。同行的还有一个叫杨开荣的小伙子。往山上爬了15里后,我们在路边一个奇差的小客栈住下。房间的三面墙壁由树枝搭成,睡觉时光线从枝条的空隙透进来。房间既不暖和,也不安全。我们把马栓在我的床脚,因陋就简,除了杨开云,我和苦力都睡得很香。
9月10日,我们早早起床,爬到山顶。俯瞰山下,云遮雾绕,看不见一处村庄。我们沿着小径小山,一路大雾弥漫。吃过早餐后,我们前往毛坪,路径一个花苗(Hua-Miaotz)村寨。“花”是他们区别于其他苗族人的标志。几个妇人围在井边用脚踩洗衣服。她们很友善,送水给我们喝。我发现妇女都将头发盘在头顶成一个金字塔形状。我还看见一些小姑娘、小伙子,有些长得很俊俏。男孩子都留着长发,分成两缕留在背后。他们穿的裙子有点苏格兰民族风情。我还没弄明白这些人到底信仰什么,有人说敬拜上天,有人说他们拜菩萨;还有人说自己啥都不信。
终于抵达山下的洛泽河,摆渡的男孩要我们60铜板,最后我们以6个铜板成交。
9月11日,是毛坪赶集的日子。我们沿街四处宣讲,卖出去几本圣经。然后我们沿着峡谷而下30里,在天黑时分到达角奎。
我们要了两碗带猪肉的细面条,加上辣椒、醋、油等佐料吃(法国厨师也许能从这里学到东西。)我还为马匹买来些许新米和草料。这里正值农忙季节,人们忙着收割稻子。昭通虽然离这里不远,温差却很大,那里的稻田还一片碧绿。
天主教在这里信徒很多。我看见许多人家屋里醒目处贴着一纸条幅,上面写着“创造天、地、人及万物的主上帝”。他们不守安息日,不过也可能是我对他们了解不多。
走上街上,时不时碰到陌生人用称呼天主教牧师的方式喊我“神父”。很显然,我是来到这里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今天来赶集的人少说都有几千人,街上挤得水泄不通。
这么多人,这么多的灵魂,却没有人告诉他们救世主降世救人的好消息。所有人生活在毫无希望的黑暗之中,看不到被拯救的机会……
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让我现在回到索恩夫人的叙述:
听取杨开荣详细的讲述,并阅读丈夫留下的日记后,我得知:9月11日清晨,他就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全身突然打起了摆子。那天一整天他都感觉特别疲乏无力。由于担心疟疾这“老朋友”又来了,他吃了奎宁;后来身体明显发烧,他又服了几片乌头(aconite);又走了一程,他又吃了砷剂(arsenic)(砷剂是为顺势疗法做准备)。但是这些药都不管用,病情愈来愈严重。我丈夫决定到了奎香就返回昭通。他还希望在奎香为自己的返回租乘轿子。但不管他们出多高的价钱,终究没有找到轿夫。
1891年9月15日,礼拜二。天黑之后很久他们才抵达奎香。礼拜三他在床上躺了一天。那天晚上藤先生到了奎香,并见到我的丈夫。
9月17日,尽管发着高烧,我亲爱的丈夫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和杨开荣启程回家。他们多雇了一匹马,把三天的路程两天就走完了。他心里有一口气,觉得自己必须尽快回家,否则就来不及了。带着重病在高山峡谷间跋涉的两天里,只有靠神的帮助。
当他终于回到家时,已被病魔折磨的不成人样(very exhausted)。
我想,如果我当时在奎香,一定能帮助我亲爱的丈夫,减轻他的苦楚。
回到家之后,他详细告诉我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事,他如何发现自己生病,路上他尽量不吃干粮,还是被迫喝了两三回生水。要知道,这是我们在中国最小心翼翼避免的事啊!他感谢主带他回家,心里满是感恩。除了脉搏过速,其他症状已经平缓下来。
但很不幸,他的脉速每天升高,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9月21日,礼拜一。我亲爱的丈夫开始全身浮肿,什么东西都吃不下。我们用尽一切办法,从未放弃希望。但主更需要他。他在世间的工已经完成,要去主耶稣那里接受奖赏。但对于我们这些可怜而脆弱的人而言,当时难以理解到这些。我们向主恒切祷告,祈求祂为了中国事工的需要,赐福我丈夫身体康复,从而免去我们分离的苦痛。
在丈夫生命的最后五天里,在这极度悲伤的分分秒秒,我日夜守护着他。这是主赐给我们夫妇的恩典。我丈夫一直都很喜乐,他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地交给神,说:“主会做正确的事,神的心意都是最好的!”。
他对主矢志不渝!
除了担心我服侍他过度劳累,他心中没有一点焦虑。他很乐观,反倒来安慰我。当剧烈疼痛来袭,他表现得异常刚毅。他从未怀疑过神的旨意,不断地赞美神,归荣耀于神。
即使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汉语说话。只要他头脑清醒,他就不停地祷告,给旁边的人分享耶稣。为了帮助他节省体力,我尽量克制自己,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即使这样,我的丈夫还是难以安静下来。
从9月8日离开我们外出巡回,到他生命的最后两、三个小时,我亲爱的丈夫不停地宣讲基督,极尽全能让人信靠主。他把自己沉浸在救赎(Atonement)的欢乐里面,有好几次,在大声赞美神之后,他劝告帮助我照顾他的厨师要来信靠主。我们的厨师会时不时重复我丈夫讲给他的话。
9月22日,礼拜二。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全身疼痛加剧,头疼尤其剧烈。我发现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正在到来。在一次清醒的间隙,我请欧伯雷斯弟兄用祈祷代替我们常规的敬拜,请他为我丈夫向主献上特别的祷告。我跪在欧伯雷斯弟兄身边,嘴里说不出一句话来。
轮到我丈夫祷告时,一开始他语不成句(he began in a few broken sentences)。可是突然,他以极大的热情,为他正在遭受的一切感谢神(就在祷告的时刻,他呼吸急促,嘴唇又干又痛)。接下来,他为我们宣教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为传教委员会,为着主在中国的福音,为着家乡的亲友,还有他的妻子我,向神献上祷告。
祷告说到这里,他突然提高声音:“主啊,求你用油涂抹我们的双唇,使我们能口齿伶俐地歌颂你的美善,传讲你的话语。”(Lord, butter our lips; make us glib to preach Thy Word, and tell of Thy goodness)。’
这是他最后一次能清楚地用英语祷告。那天,他还做了好多次简短的中文祷告。
一位从贵州安顺专程赶来的传道员代先生(Mr. Tai), 是主亲自带领他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安慰我们的。代先生跪在床前,索恩将手放在他的头上,为这个弟兄向神求祝福。他还祈求上帝的荣光在这里彰显,祈求天国快快降临。
傍晚时分,索恩终于平静下来。我们的心中再次燃起希望。谈起即将召开的教区会议,他问我明年我们会被差派去哪里事工?我说,也许主会让我们承担更大的任务。他听后回答我:“我不知道,愿神的旨意成全。”
吃过晚茶,我去另一间屋子略微休息休息。我离开时,他口里叫着我们“养子”的名字,诚挚地劝勉他归向耶稣,告诉他:“我很快要到天堂去了。”
我走后,欧伯雷斯和代传道两人守护着他。他不停地呼喊:“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他们还拿起歌本,一起唱了一首中文赞美诗。
欧伯雷斯发现我丈夫的手脚开始变凉,赶紧叫我过来。我到达他身边后,发现“最后的时刻”正在到来。
我亲爱的丈夫深情地注视着我,挣扎着要对我说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刚才,他曾几次呼唤我,听说我在休息,他显然很得安慰。他使劲想说话,但吐出的声音我们完全听不清楚。
10点左右,死神开始在他身上动工,从那时起,我丈夫的身体陷入极度的痛苦,再也没有精力关注我们。
我们四人齐齐在他身旁跪下,将我心爱丈夫的灵魂交托给全能的上帝,愿神亲自带领他走过“边缘之地”(border-land)。我们也为自己祷告,求神赐我们全然顺服的心。
在这肃穆庄严的时刻,我们感到天国已经近了。我们的中国佣人也都来到床边。那时那刻,我们是多么的无助。
12点过后,他的呼吸明显微弱。12点30分,我亲爱的丈夫离别人世,归回天家。
我们又全部跪下来祷告。代先生将他的灵托付给上帝。
我们一直这样跪着,直到他的灵离我们而去。
露易丝 1891年9月23日,凌晨12:30分
感谢支持文字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