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所有这些停滞的文明社会共同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等级制和专业化分工,这两个特征都可以浓缩成一个单一的公式:这些社会包含的个体不完全是一种单一的类型,而是被分割成具有明显差别的两类或三类。爱斯基摩社会有两个等级:猎人和猎犬。游牧社会有三个:牧羊人,辅助动物和牧牛。在奥斯曼社会,我们可以找到与游牧社会对等的三个等级,只不过人类代替了动物。游牧民族复杂的社会躯体是由离开其同伴就无法在草原生存的人类和动物构成的单一社会聚合而成的,而奥斯曼帝国复杂社会躯体的构建正好与之相反,它把本性相同的人类划分成许多等级,似乎把他们视为不同种类的动物(就我们目前的研究目的而言,这些“动物”之间的差别是可以忽略的)。爱斯基摩人的猎犬和游牧民族的马、骆驼是半人性化的,可以视为人类的同伴。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莱亚(Raiyeh,意指“畜群”)和拉哥尼亚的希洛人却是半动物性的,被当作牲畜看待。在这样的社会里,其他的人类同伴则转变成了独特的“怪物”。完美的斯巴达人是一个火星人,完美的土耳其禁卫兵是一个教徒,完美的游牧人是一个人首马身的怪物,完美的爱斯基摩人则是一个人鱼。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辞》中,对雅典人和它的敌人作了对照,其要点就是雅典人是一个按神的模样造出来的人,斯巴达人却是一架战争机器。至于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所有的观察者都一致认为这些“专家们”已经把他们的技术完善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他们是把人和船以及把人和马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进行活动的。
这样,爱斯基摩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斯巴达人都通过尽可能地抛弃无限多样化的人性而坚持一种僵硬的动物性完成了他们所要完成的使命,由此他们就走上了倒退的道路。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使自身严格适应高度特殊环境的那类动物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在进化过程中是没有前途的,而这恰好是这些停滞文明的命运。P179-P180
匝评:不能说“等级制和专业化分工”是导致文明停滞的原因,任何社会都有等级,自然形成的等级是正义的。关键不是有无等级,而是如何形成等级,是不要用人为的政治权力形成等级。当然,作者这里批评的主要是人的异化。现代工业、大学、科学的日益专业化已经使人成了工具,丧失了人性的完整性,这对文明是巨大的挑战。思想源于综合,而不是分析。
12.在伯里克利死后,民主就和它曾经辉煌过的同伴——雅典文化分道扬镳了,民主发展成为一种疯狂的军国主义,几乎摧毁了曾经孕育出无比灿烂的雅典文化的整个世界,直到最后以苏格拉底的被审判谋杀结束了这场战争。
战后雅典的哲学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批判过去两个多世纪曾经使雅典无比繁荣伟大的一切事物。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把雅典的哲学和斯巴达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才能拯救希腊。P181
匝评:国内民主从来都不可能带来世界和平。千万不能迷信民主,法治下的自由高于民主。
13.真正最适度的挑战不仅能够刺激挑战的对象完成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能够刺激它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从一次成功到一个新的挑战,从解决一个问题到面临另一个问题,从阴到阳。如果文明不断生长,仅有一次从动荡到平衡的有限运动是不够的。要把这种运动转变成周而复始的节律,必须有一种“生命冲动”(柏格森的术语),以便将挑战的对象再度从平衡状态推入动荡之中,再次面对新的挑战,再度刺激它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结束动荡继而作出新的应战,如此交替,不断前进以至无穷。P187
匝评:自信才能不断直面问题,并想办法解决问题,开放才能真自信,才能有真活力。
14.在甘地的职业生涯中,也体现了这种模糊性,他对无处不在的西方化进程的不情愿推动,具有更强的讽刺意味。这位印度先知提出要切断使印度卷入西方世界大网中的棉线。他宣称:“用我们印度人的双手纺织我们印度的棉花”;“不要穿西方电动织布机的产品。我恳求你们,不要通过在印度的土地上的、按照西方模式新安装的电动织布机,来驱逐那些异族的产品”这种思想是甘地的真实思想,但并没有被他的同胞所接受。他们尊他为圣徒,但是听从他的只是他辞职后领导他们走西方化道路的主张。因此,今天我们看到甘地实际上推动了一个西方式的政治道路——印度转变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制主权国家——建立了各种会议、选举、辩论、报纸、宣传等西方式的政治机构。在这个运动中,这位先知最有效的——但不是最强大的——支持者正是那些极力破坏他的真实使命的真正的印度工业家,因为他们把西方的工业技术移植到了印度。P204
匝评:甘地代表了一个古老文明可笑的,但也无力的民族自尊心。甘地就是印度的倭仁,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就算是在印度,尼赫鲁也很快就改变了甘地的政策。
15.对连续挑战既定的一系列成功的应战,如果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推进,这种行为趋向于从外部环境——自然环境或者人为环境——转移到成长中的人格和文明内部,那么这一系列挑战和应战就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成长现象。就成长和持续生长而论,它面对的是越来越少的来自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对于外部战场的强制性应战,不得不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来自内部的自身挑战。生长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换句话说,文明衡量的标准是一个趋向自决的过程,尽管这个进步过程对于描述“生命”进入其王国的这个奇迹来说,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图式。P206-P207
匝评:文明体之间永远存在竞争,关键不在于文明体是否应该应对挑战,而在于要主动应对挑战,并在此过程中不仅更新文明的物质载体,而且更新文明的内核,即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各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华夏世界尚未在应对西方的挑战中获胜,因为华夏文明的内核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更新。
16.描述人类社会和个体关系的正确方式又是什么呢?真理似乎是:一种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关系系统,人类不仅是个体而且是社会动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脱离了与其余部分的关系是无法存在的。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就是个体之间关系的产物,他们的关系来源于个体行为场所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把个体场所结合成一个共同场所,这个共同场所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P211
匝评:关于社会和人的关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错的,应该是关系主义。集体主义压制个人,个人主义导致无力,只有关系主义才导致自由力量的兴盛。自由主义建基于个人主义,是一个迷梦。
17.正像人类天才不断打破人类智力界限一样……所以出现了一些异质的灵魂,它们感到与所有的灵魂都有关系,它们不会局限在所属群体的界限之内,不会局限在大自然建立的有限固定性之内,而是以一种爱的冲动致力于全体人类事业。这种灵魂的每次出现都是创造一个独特个体构成的新种类。
……在柏格森看来,只有神秘家才是完美的超人创造者,他能够在神秘经历的最重要的时刻发现创造性行为的本质:
……这个伟大的神秘家感到真理从其源头流进他的身体,涌出一股行动力量。神秘家的方向正是生命冲动力的方向。生命冲动本身与那些具备超常异质的人类紧密相连,他们渴望在全人类身上留下印记,渴望通过他们觉察到了的矛盾性,把一种本质上是被创造的事物改变成具有创造性的事物,准确地讲,是从确定为停滞的事物中制造出一种运动来。
这种矛盾性是社会动态关系无法解开的死结,它源自人类中间具备神秘灵感人格的出现本身。这种创造性的人格激励他的同伴转变成创造者,依据他的形象重塑这些同伴。发生在神秘家微观世界的创造性转变在其完成或巩固之前,需要宏观世界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但是依据这种假说,转变了的人格的宏观世界同样是未曾转变的同伴的宏观世界,当他努力改变宏观世界以期和自身的改变相一致的时候,将会遇到他们惰性的抵制,这种惰性趋向于保持宏观世界和未曾改变的自我相协调,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
这种社会状态代表了一种两难。如果创造性天才不能在他的周围实现他自身完成的转变,那么他的创造性对他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他将与他的行为场所不再协调,即使他以前的同伴没有把他折磨致死,在失去了行动动力后,他也将失去生命的意志,就像蜂群和兽群中的异类在群居的动物和昆虫社会生活中被通过排斥和隔离折磨致死一样。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天才的确成功地战胜了其周围的环境和以前同伴的敌意,的确胜利地把周围的社会环境改造成与他转变了的自我相协调的新秩序,那么他又因此制造了一种男男女女的普通肉体无法忍受的生活,除非他们能够成功地调整自我,使之适应新的胜利的天才主导性的创造意志强加的社会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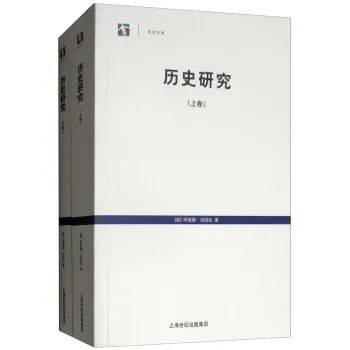
……当天才的破坏性爆发一旦打乱社会平衡的时候,社会平衡如何复原呢?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独立地完成统一爆发——力量统一,方向统一。……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创造性天才的感召作出百分之百的反应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毫无疑问,历史充满着这样的事实:当一种观念——宗教的或者科学的——处于未定之时,它只会单独地、几乎同时地在一些有灵感的人们的思想里酝酿而成。即使在极其异常的情况下,这些启示性的思想也只能被个别人注意,成千上万的人对此是反应迟钝的。事实似乎是这种内在的独特性和任何创造性的个性会受到某种趋向统一的倾向微不足道的抵制,因为这种统一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潜在的创造者,这些个体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之中,结果当这个创造者出现的时候,甚至当他有幸得到一些家族同伴的时候,他总会发现自己处于人数众多的毫无创造性的惰性群体的压制之下。所有社会的创造性行为或者是个别创造者的工作,或者至多是少数创造性群体的工作,在任何一个连续的进步过程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落在了后面。……
文明的成长是个别创造者或少数创造性群体的工作这样的一个事实暗示着没有创造性的大多数人将会落在后面,除非这些先驱能够设想出一些办法在他们的急切前进中带动这个反应迟缓的后卫部队和他们一道前进。……在每一个成长中的文明中,大多数参与个体都处在与静止的原始社会成员一样的停滞不前、沉寂无声的状态中。更多的情况是,成长文明中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具有原始人类似的热情的人,只不过添加了一个教育的外表而已。在这里我们发现真理的要素即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超常的人格、天才们、神秘家或者超人——无论你称呼他们什么——都仅仅是普通人面团中的一个酵母。
……事实上,要确保毫无创造性的大多数人跟随那些具有创造性的少数领导者显然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实践上的,另一个是观念上的:
一个是教化的方法……另一个是神秘主义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反复灌输一种不掺杂个人因素的习俗构成的道德;第二个方法劝诱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然后达到精神的结合,或多或少形成一种认同感。
创造能力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的直接传递无疑是理想的方法,但是完全依赖这种方法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空想。要想在整个社会规模上把那些没有创造能力的普通人提高到创造性的先驱者的水平上,依靠实践的方法是无法解决的,只有运用纯粹的模仿能力——这是人性的较低能力之一,其中教化要多于启发。P211-P216
匝评:先知引导群众不是靠群众机械、被动地模仿,更重要的是调动群众的情感和利益。后者或许理性不足,但往往情感有余。后者往往看不到意义,但在乎利益。先知之所以能引导群众,前提是先知敢于牺牲自己。先知一定是无私的,因为无私,所以勇敢。先知的神秘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无私。
18.柏拉图为这些哲学家铺就的道路与基督教神秘家所走的道路确实是一样的。
然而,尽管道路是一样的,但是希腊和基督教的灵魂所要跨越的精神是不一样的。柏拉图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得到启示的自由哲学家的个人兴趣和个人的欲望一定不会和仍然“处于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下……牢牢陷于痛苦和枷锁中的”大多数同类相同。在柏拉图看来,无论囚徒的兴趣是什么,哲学家都不会牺牲自己的幸福和理想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一旦他获得了启示,对他而言,最好的事情就是呆在洞外的光明中,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事实上希腊哲学的基本原则就是:生活的最佳状态是沉思状态(contemplation)——希腊语中的这个词已经变成英语中的“理论”(theory)一词,我们习惯性地把它当作“实践”(practice)的对立面来使用。毕达哥拉斯把冥想生活置于行动生活更高的层次上,这种观念贯穿于整个希腊哲学传统,一直持续到生活在希腊社会解体的最后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为止。柏拉图倾向于相信他的哲学家愿意参与世界性的工作,仅仅出于一种纯粹的责任感,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的拒绝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文明遇到的衰竭从来不能复苏,他们 “强烈地拒绝”的原因也是很清楚的。他们道德的局限性根源于信仰的错误。由于相信狂想而不是复出就是已经踏上的精神上的奥德赛(即长途跋涉)的全部和终点,因此他们只看到从狂想到复出这一痛苦旅程中的责任祭坛上的牺牲,而事实上这是他们所从事的运动的目的和顶点。他们神秘的经历缺乏基督教最重要的博爱美德,而正是这种博爱美德激励着基督教的神秘家直接从与上帝交流的最高处回到精神和肉体都不可救赎的世俗世界。P219
匝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没有力量,真正有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是圣徒。圣徒之“圣”,在于他们是先知;圣徒之“徒”,在于他们是门徒,是敢于牺牲的行动者。
19.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么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无费力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P232
匝评:所以中国历代大患在北方。
20.我们西方社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从一个农业贵族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一种工业民主生活方式而且不采用城邦体制。瑞士、荷兰、英国都遇到了这种挑战,最终采取了英国式的解决方式。这三个国家从欧洲的普通生活中归隐以后都得益于它们的地理环境:瑞士得益于高山,荷兰得益于堤坝,英国得益于海峡。瑞士成功地克服了中世纪晚期城邦统一政体的危机,建立了联邦政体,在先是抗击哈布斯堡王朝,后又抗击勃艮第强国以后,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荷兰在击退西班牙的进攻后获得了独立,建立了由七个统一行省组成的联邦国家。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被迫收敛了企图征服欧洲大陆的野心,像荷兰一样,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击败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从那以后直到1914—1918年战争,始终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陆事务的政策,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标之一。P234
匝评:为了长治久安,大国必须平衡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联邦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