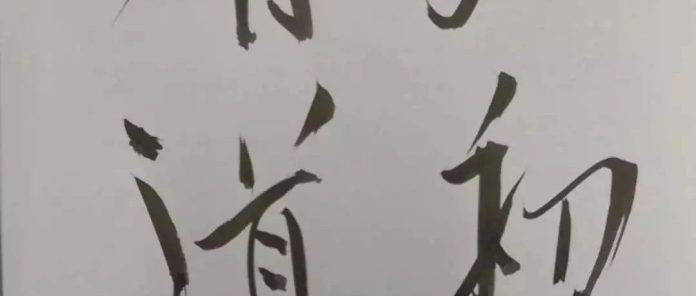第三十四讲 徐光启:苍天未死,黄天可立
这一讲我们讲徐光启。之所以讲徐光启,是为了讲中国思想史的另一种可能。
徐光启(公元1562年-1633年)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他的重要性不在于当过高官,而在于他是中国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与中国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他本是一个追求读书仕进的儒者,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改变了他的思想。34岁那一年,他在广东韶州遇到了耶稣会神父郭居静(Cattaneo),深受天主教吸引。41岁,他在南京接受罗如望(Jeande Rocha)的洗礼成为天主教徒,为此他还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了“保禄”二字,这表明他愿意亮出自己作为天主教徒的身份。他和传教士利玛窦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利玛窦教授他西方天文、地理、农业、水利等方面的知识。1604年-1607年,他与利玛窦共同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为中文,他还著有《农政全书》。他任礼部侍郎的时候,建议根据西洋历法修改我国历法,因为我国历法无法准确推测出日月食的时间。为此他被任命为钦天监。钦天监任内,他不仅任命了自己的友人、同时也是天主教徒的李之藻为副手,还大胆起用了耶稣会传教士龙幸民(Longobardi)和邓玉函(Terrenz)为副手。邓玉函去世后,他又请汤若望及罗雅谷(Jacgues Rho)接替邓的工作,这二人也是传教士。
徐光启的特色在于,他信仰西方宗教,推崇西方科学。在儒家思想深入骨髓的中国,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徐光启干的事,可以说是空前的。可以想象,他必然面临巨大阻力。
天主教在明末初进中国时,就遇到了士大夫普遍抵制,甚至有人向皇帝指控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go)等耶稣会教士败坏人心。这是相当严厉的指控。
在这个时候,徐光启站了出来为传教士辩护,他向皇帝上了一道《辨学章疏》。他说,这些西方传教士都是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知识渊博的人,他们的言行没任何问题,如果他们有问题,那么他愿意为他们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信奉天主教。
为了消除皇帝的顾虑,他说,天主教的教化与儒家思想其实毫不矛盾:“臣累年以来,因与(传教士)讲究考求,知此诸臣(传教士)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功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诫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罚善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衷故也。”
不仅如此,徐光启还站在皇帝治理天下的角度,指出了天主教的社会功用:“辅益王化”、“教化风俗”、“久安长治”。徐光启提出的建议是:“倘蒙圣明采纳,特赐表章,目今暂与僧徒道士一体容留,使辅宣劝化,窃意数年之后,人心世道,必暂次改观。乃至一德同风,翕然丕变,法立而必行,令出而不犯,中外皆勿欺之臣,比屋成可封之俗,圣躬延无疆之遐福,国祚永万世之太平矣!”
为了进一步消除朝廷顾虑,徐光启还提出了考察传教士的三种方法,大意是把传教士翻译的所有宗教、科学、政治、艺术书籍拿出来公开讨论,如果悖逆常经,言无可采,不能启人智慧,则可斥逐,他自己也甘愿与传教士同领罪罚。
最后,徐光启还提出了处置传教士的三种方法:一是由朝廷提供生活所需,停止传教士接受外来接济;二是允许传教士传教,并接受人们监督,看他们言行是否正当,若不当则驱逐出境;三是观察那些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的品行是否良善。
徐光启论述清晰,建议得当,万历皇帝看了这份奏疏,批了“知道了”三字,事实上就允许了传教士在中国传道、译书。
与徐光启一样,李之藻对天主教的认识也是从其与儒家精神不悖、有利于世道人心的角度立论,但他更强调主宰之天的价值。在为利玛窦《天主实义》所作序言中,李之藻讲了如下几层意思:一,天是修身之原。“昔吾夫子语修身也,先事亲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养事天之论,而义乃綦备。盖即知即事,事天事亲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二,上帝是天的主宰。“帝者,天之主宰。”三,利玛窦一本事天。“然则天主之义不自利先生创矣。……然则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谭天之所以为天甚晰。”四,《天主实义》写作宗旨是训善防恶。“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为大父母也。人知国家有正统,而不知惟帝统天之为大正统也。不事亲不可为子,不识正统不可为臣,不事天主不可为人。’而尤勤恳于善恶之辩、详殃之应。……大约使人悔过徙义,遏欲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监,绵顾畏而遄澡雪,以庶几无获戾于皇天上帝。”五,天学合于儒学宗旨。“……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于正,至其检身事心,严翼匪懈,则世所谓皋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厉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为了说服皇帝和读书人,徐光启和李之藻大多强调天主教与儒家的相同处,而故意淡化了二者的差异,也不凸显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应该说,这是很明智的策略。
说到二者的差异,我想顺带讲一个故事。御史杨廷筠也信仰天主教,打算受洗,但被教会拒绝,原因是天主教反对纳妾,而杨廷筠有侍妾。儒家不反对纳妾,教会的拒绝让杨廷筠左右为难。最后,在李之藻的说服下,杨廷筠放弃了侍妾,才如愿受洗。
下面我们来谈徐光启对西方科学的推崇。事实上,你已经发现,我谈徐光启不是为了谈徐光启个人,而是谈他同时期思想上的同道,其中自然也包括李之藻。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序言中说:
唐虞之世,羲和治历,暨司空、后稷、工虞、典乐五官者,非度数不为功。周官六艺,数与居一焉;而五艺者,不以度数从事,亦不得工也。襄、旷之于音,般、墨之于械,岂有他谬巧哉?精于用法而已。故尝谓三代而上,为业者,盛有元元本本,师傅、曹习之学,而毕丧于祖龙之焰。汉以来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依拟形状,如持萤烛象,得首失尾,至于今而此道尽废,有不得不废者矣。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利先生从少年时,论道之暇,留意艺学……因请其象数诸书,更以华文。独谓此书未译,则他书不可得论。遂共翻其要,约六卷。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虽实未竟,然以当他书,既可得而论矣。私心自谓:“不意古学废绝二千年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其裨益当世,定复不小。”……
这篇序言再次体现了徐光启的游说技巧,其大意是:上古时代,中国人本来就重视数学,只是秦汉之后,此学失传。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几何原本》是数学的祖宗,所以应该引进,以补充中国上古本已有之“阙典遗义”。徐光启还说;“下学工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能精此书者,无一书不可精。”他还说,此书有四不必、四不可得。四不必是: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四不可得是: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应该说,徐光启对数学的认识是深刻的。
与徐光启相似,李之藻也相当重视科学知识。他在认识利玛窦之前,曾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认识利玛窦以后,发现利玛窦也有一幅世界地图,而且对方的地图比他的科学、严密得多,他就放弃了自己的地图,成了利玛窦的弟子。他也与利玛窦一起翻译了两本数学书,一本是几何方面的《圜容较义》,一本是算术方面的《同文算指》。更值得提及的是,李之藻还与傅汎际(Francis Furtado)一起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现在的人们都知道,逻辑学是社会学科的基础。很显然,徐光启和李之藻之所以要翻译西方的数学和逻辑学名著,目的就是要培养中国思想传统中相当缺乏的科学思维。
我上面的判断并非武断,让我们来看看利玛窦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他在《几何原本》序言中说:
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物理渺隐,人才顽昏,不因既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吾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故审究物理之书极繁富也。彼士立论宗旨,惟尚理之所据,弗取人之所意。盖曰,理之审,乃令我知,若夫人之息,又令我意耳。知之谓,谓无疑焉,而意犹兼疑也。然虚理隐理之论,虽据有真指,而释疑不尽者,尚可以他理驳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信其无或非也。独实理者,明理者,剖散心疑,能强入不得不是之,不复有理以疵之,其所致之知,且深且固,则无有若几何一家者矣。
程朱陆王都谈致知,但所致的知都是德性之知,而非如今我们所说的科学之知——物理。中国人没有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也就谈不上有科学思维。利玛窦在这里虽然也用了中国“格物”、“致知”的老词汇,但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他把“格物”解释为对物理的探求,“致知”解释为对物理知识的获得,这不能不说简直就是发动了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自此以后,中国人才逐渐建立科学思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利玛窦长期共事,相互之间过从甚密,可以推测,利玛窦关于格物致知的新思想,也是徐、李二人的共识。也可以说,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试图实现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也正是他们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意义。
值得重视的是,明末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不仅仅只有上文提到的几位,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书籍、他们与中国人合译的书籍也不仅仅是上文提到的那些。统计数据显示,仅仅传教士金尼阁带到中国的西洋图书就多达7000余部。据学者张荫麟考证,“这样数量的书籍,是欧洲一个巨型图书馆的规模,几乎包括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各学科的所有知识”。传教士到中国来,虽然以传教为目的,但考虑到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实际情况,他们的着重点首先是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这样才不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中国人自古养成了实用理性的民族性格,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从帝王到士大夫并不排斥西学,最典型的例证是,康熙皇帝甚至是个西洋科学迷。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随着西方神学和科学思想的引进,人们逐渐发现,它们必然解构中国固有的意识形态。按葛兆光先生的说法,它们给中国带来了“天崩地裂”的结果。
先来看西方天文、地理知识传入中国给中国人的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天圆地方”,天围绕北极星为中心转动,地不动。中国处于这块方形的大地的中央。中国的皇帝是上天之子,稳居中央之国,是苍天之下无可争议的共主。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最新的天文学表明,地球绕着太阳转,天也不是圆的,而是无限的,也无所谓中心,地球是圆球,当然也无所谓中央。传教士带来的地理学也表明了这一点。它让中国人知道,世界由许多国家构成,这些国家都分布于地球之上。很多国家的名字,中国人闻所未闻。这就直接解构了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君权神授在古代为何必要?因为皇帝可以通过定义时间和空间来定义、训导、规制人们的思想。长此以往,人们就会把这套思想当成理所当然的公理,根本不需要论证。如今,中国的时间(历法)经测量误差很大,空间意识又被证实为纯属虚构,那么,皇帝统治的合法性何在?
这个问题,清初的那个著名的反动派杨光先就看到了,他之所以反对西法,根本无关于根据西洋天文学测算出来的天象是否准确,而是别有大用意在。“光先所以攻其西法,非其新法也,其言孟子之距杨墨,恐人至于无父无君。”到了清末,曾廉还认为:“西人言,日大不动,而八星绕之……窥其用心,止欲破我天地两大,日月并明,君臣父子夫妇三纲而已。”即便进步如梁启超,也说:“空间、时间二者,实吾感觉力中所固有之定理,所赖以综合一切,序次一切,皆此具也。苟其无之,则吾终无术以整顿诸感觉而使之就绪。”梁启超不仅看到了天地观念的变化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不能自洽,而且看到了由此导致人们无法思想的更大困局。
我在以前多次讲过,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天,是主宰之天、规律之天与自然之天的混杂,它们之间很难分开。如今,自然之天已经被西方的天文、地理学说解构,那么,中国原已稀薄的主宰之天的观念还能撑得住吗?要命的是,传教士带进中国的,不仅是关于自然之天的知识,而是整个西方的系统知识,这其中不可缺少的,也是与传教士身份密切相关的,是其关于主宰之天的信仰,那就是基督宗教的上帝信仰。虽然中国人找到了“上帝”一词来翻译基督宗教的神耶和华,但天主教教义与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在本质上其实是不同的。比如,基督宗教反对偶像崇拜,主张独一神,倡导原罪说、救恩说、契约论、自由平等说,如此等等都与儒家思想截然不同。因此,中西双方在思想上发生冲突是必然的。
这种冲突在初期并不会彰显出来,因为彼时人们对西学的认识还局限于术的层面,但随着西方的科学思想和基督信仰日渐扩散,人们认识到西学的术后面还有一个它们自己的道在支撑,冲突就会到来。事实上,虽然康熙与传教士曾经有过一段不短的蜜月期,但当传教士所传播的思想直接威胁到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时,康熙的反应也相当断然,那就是彻底驱除传教士出境。就历史事实而言,这一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是罗马教宗对中国传教士的严厉指责,他认为中国传教士纵容天主教徒祭拜祖先,违背了天主教义。在他的观念里,祭拜祖先的天主信徒根本是不合格的信徒。但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祭祖天经地义。更要命的是,在儒家思想里,家国同构,忠孝同理,祭祖体现了中国的孝道,如果切断这个孝道,臣民为什么还要忠于皇帝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康熙、雍正驱除传教士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对于这一历史事实,一般人认为,错误在罗马教宗一方,但我认为,找到一个偶然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没有意义的,更应该看到的是中西思想的确存在相当大的不同,而且其核心主张就是不同的,所以冲突是必然的。
徐光启等人的主张,大概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苍天未死,黄天可立。这基本上还是从实用理性出发考虑问题得出的结论。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看,他们或许还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人类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也就只能同戴一个天,不可能有两个天。这就需要把旧的天换成新的,而这一换天的过程,必然需要很长时间。同时,这个转换的过程会出现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前进和倒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都很难说这个过程已经完成。
中国古人总喜欢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明末以后出现的问题是,天已经在变了,那么,道呢?在王阳明那里,中国的天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心。到徐光启这里,就已经认为我们不妨换个天试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光启为中国思想史开启了另一种可能。也可以说,他启动了中国思想史进入近代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