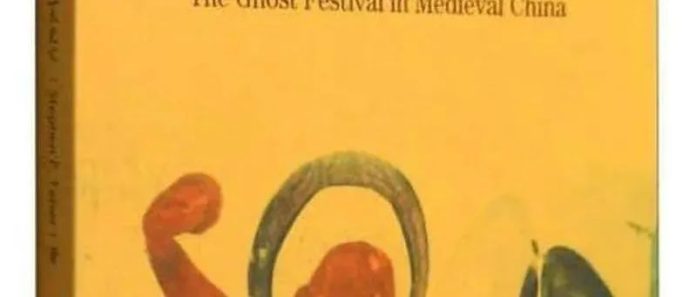著名作家周作人在《我的杂学:十四》里说:“中国人民的情感与思想集中于鬼……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周作人眼光之敏锐不在其兄鲁迅之下,可惜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周作人因附逆之事,其影响力远远被低估,再次显示出中国人敏于别人之罪,而黯昧自身罪过(自我称义极具欺骗性与捆绑性)的能力是何等强大。一方面,周作人这说法,敏锐地感受到与生死相连的“鬼”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另一方面礼俗之诞生与传承,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在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之前,都处于一种弥散性(社会学家杨庆堃语)状态,而佛教与道教的建制性使得宗教的规模性、礼仪性、活动性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但总体来说,由于一直匍伏在政权之下,在政教关系中被政权碾压,故建制性一直发育不良,因而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往往会“弥散性”地扩张到民众的生活中,而变成礼俗的一部分。
一
今天是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中元节——中元节是道教的称呼,佛教称为盂兰盆节,而民俗称七月半、鬼节、麻谷节等——虽然在建制性的形式上,七月半对今天中国很多地方以及不少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但其中作为宗教(或民俗)习俗依旧强旺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概略地说,其实影响中国民众的观念力量,除官方的意识形态外,有两股看上去很难区分,但确实有所不同的力量促成,亦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前者系书面语写成之专著(若儒家的四书五经、佛教之各种内典、道教之各种经籍等),影响知识阶层;而后者则是以说唱(书)、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官方宣讲(圣谕圣训等)以及众多节日之动态形式,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换言之,哪怕你没有读过一天书,你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那文化就是相对比较容易迁衍而动态的“文化传统”,而非需要一定阅读门槛的“传统文化”。
关于中元节的来历及其相关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多是散乱而不成系统的,不仅史料梳理与发展沿革欠奉,且用诸种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深度,也并不令人满意。单以张士闪、周星主编《节日文化.第六辑.鬼节专辑》(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为例,其中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大多炒冷饭,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令人措意的地方。倒是美国学者太史文(Stephen F.Teiser)所著《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侯旭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史料及剖析上都下了较多的功夫,基本上把鬼节怎么从一种零散而影响有限的民间活动,因佛教的楔入(盂兰盆经之译成汉语,再加上各种注疏如宗密等人)、道教的命名(中元节),最终成为影响波及面相当广的中国传统节日,给讲明白了。
简单地说,古代中国有各种祭祖传统,众所周知的春节、清明节先按下不表。其中就有一个秋尝的祭祖活动,即秋天作为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向祖先告成,荐新祭祖,求祖先继续保祐。与此同时,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一开始受阻,一方面将僧伽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三个月封闭之修行,与民间秋尝之祭祖连结起来;另一方面改变其经典汉译与注释策略,加进具有佛弟子目连,从而杜撰出一个于地狱救母的戏码,层累叠加,逐渐完成对民间零散的季节性祭祖活动,系统化成一个以孝道为中心的祭祖活动。传统印度佛教当然不仅与孝道无关,而且出家修行,还直接违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古训。但作为人创宗教的佛教施展十八般武艺,以求中国接纳,这便是中国佛教历史的重心。可惜的是,原始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对比,以及佛教如何中国化的过程,远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就在佛教楔入中国民间散乱的祭祖活动的同时,道教作为佛教的竞争势力也没有闲着。它在上元(农历正月十五),再添一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下元节(十月十五),形成其一系列的祭祀礼仪,分别对应其天官、地官、水官的诞辰。其对应功能是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而清虚大帝地官因主赦罪,地官自然掌管大地上鬼神幽明之事。而佛教的僧伽及僧团封闭修行(包括对他人罪过的揭发与自我揭发),也与这个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儒(民间祭祖)、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元节”。藉此儒家得其祭祖和血缘联络,佛教得影响力之扩大(包括经济上得到广泛的民众布施)、道教得冠名(中元节是道教所命名,与佛教分享死亡超度等仪式的分肥活动),从而造成了一个影响不下于春节的中国传统节日。
不特如此,太史文还认为鬼节如只是民间(佛、道广泛意义上讲亦可谓民间)的影响,而没有官方在这当中的助力,是不可能在中国的中世纪特别是唐朝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儒释道三教共“创”之“中元节”,其中“收益”最大的自然是佛教——虽然“盂兰盆节”之名似乎相对不彰,它通过目连救母的戏码,成功地迎合了中国旧有的传统,一定意义上比竞争对手道教占得先机,另一方面解除了本土精英势力亦即儒教抵抗的武装。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皇家祭祖需求,而且提倡祭祖特别是鬼节的祭祖,只单纯地在家里祭,而不到寺庙许愿,参与超度、祛祓活动,其果效存疑,从而在一定程度为僧团、寺产的扩大带来很大的助力。
鬼节主要重心是祭祖(家鬼),当然也拿点剩余的东西祭孤魂野鬼(故有些地方将鬼节名为“施孤”),两者的目的有同有不同。相同之处,都是为了满足活着的人之情感,希望祖先保祐自己及后代,说明自己还不算忘本;若不祭祀祖先,就是不肖子孙,祖先要“饿饭”,是大不孝,其实考虑的中心还是活着的人。祭祀野鬼,自然远不如祭祖先之施舍,但更多的是采取驱促野鬼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祭祀中的等级与亲疏之别,祭祖的重心还是其背后的血缘崇拜。其实这祭祀,完全是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真实反映,与其说传达的是幽明动向,不如更措意的是人间。
二
鬼节的崇拜性质是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即便在无神论被大规模灌输的今天也是如此。但2010年香港中元节(潮人盂兰胜会)被官方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是四九年后被官方批评的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传统之“返潮”。官方在这里展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行为,一个无神论政权,接纳一个边缘性(香港相对内地、中元节相对于无神)的“传统”节日,暗含着一种不自信的妥协——以保存中国文化为名来实施。我并不否认人死后灵魂不死(中国传统中也有灵魂不死的信仰),也不否认祖先值得追怀纪念,但不赞同祭拜祖先。因为祖先不过是人,祭拜非创造者之外的任何受造物,都是不折不扣的偶像崇拜。
学者张士闪写过一篇文章名为《“鬼节”与“鬼结”》,内容倒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但标题所体现了像周作人一样的敏锐,还是值得赞赏的。中国不少人一方面相信人死如灯灭,另一方面又相信有鬼,这二者的对立在逻辑学教育欠奉的中国,人们常常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之处。与其陷入“鬼结”之中,还不如真正直面死亡,因为人人必有一死。而不是常常以为自己不会死,对死亡毫无准备,一旦来了,就处于呼天抢地的失措状态。仿佛在哭诉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死亡为何临到自己的亲人?直到自己死时,亲人又重复以前恸哭者的状态。
为了研究死亡,我搜罗了大约近六百种文献,还有待编细目整理。其间我曾罗列过“关于死亡的儿童绘本”62种(关于死亡教育当然不只是涉及到儿童,所有人都应该思想死亡之事,死亡教育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死亡与信仰”的文献62种(涉及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各种宗教),其它分门别类的罗列,亦在进一步整理之中,以使有兴趣者知道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必然影响我们如何生活。一个不思想如何面对死亡,不思考死了到哪里去的人,其实可以直接地说,他活着的质量并没有他彰显出来的那么高,其人生意义也是存疑的。因为他连人生在本质上的虚空性,都缺乏必要的警醒与反思。
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诗人约翰.邓恩,因两位诺贝尔获奖者——诗人艾略特的赏识、作家海明威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的称引,其“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敲响”,逐渐为人所知。事实上,“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这段著名的话,是他作为牧师所写的布道词或者说传道讲章,名为《紧急时刻的祷告》(一译《在紧急际遇中的灵修》),其主要目的是安慰彼时在瘟疫流肆虐中生活的人们,其实也是他面临极大的病痛时,如何操练死亡(与希腊哲学家的操练死亡不同,它是公共事件,既鼓励自己,更安慰别人,也是传福音的机会与方法),并且通过自己预备死亡,使更多的人能听道而悔改归信主。
邓恩临死时的讲章,出版时被贯以《死亡对决》之名。这当然不像希腊哲学家操练死亡,靠自己来完成与“死亡对决”,在他看来那是荒谬不经的。他进而说,“我们不须要太担心引致死亡的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始终掌管着我们如何离开世界,也关注我们怎样离开,所以我们可以信靠祂”,最重要的是“在突然的死亡中有时间悔改,在迈向死亡的痛苦和艰难过程中,能有冷静与谦和的心去面对”(罗莫伯《死亡灵旅:无憾迎永生》P67,宣道出版社2017年版)。在清明节、中元节、十月半(亦有说十月一之送寒衣节,才是三大鬼之一)三大鬼节包围的文化处境下,让我们去掉偶像崇拜,直面死亡,得着悔改并真正认识造物主的机会。
2022年8月12日上午匆匆写就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