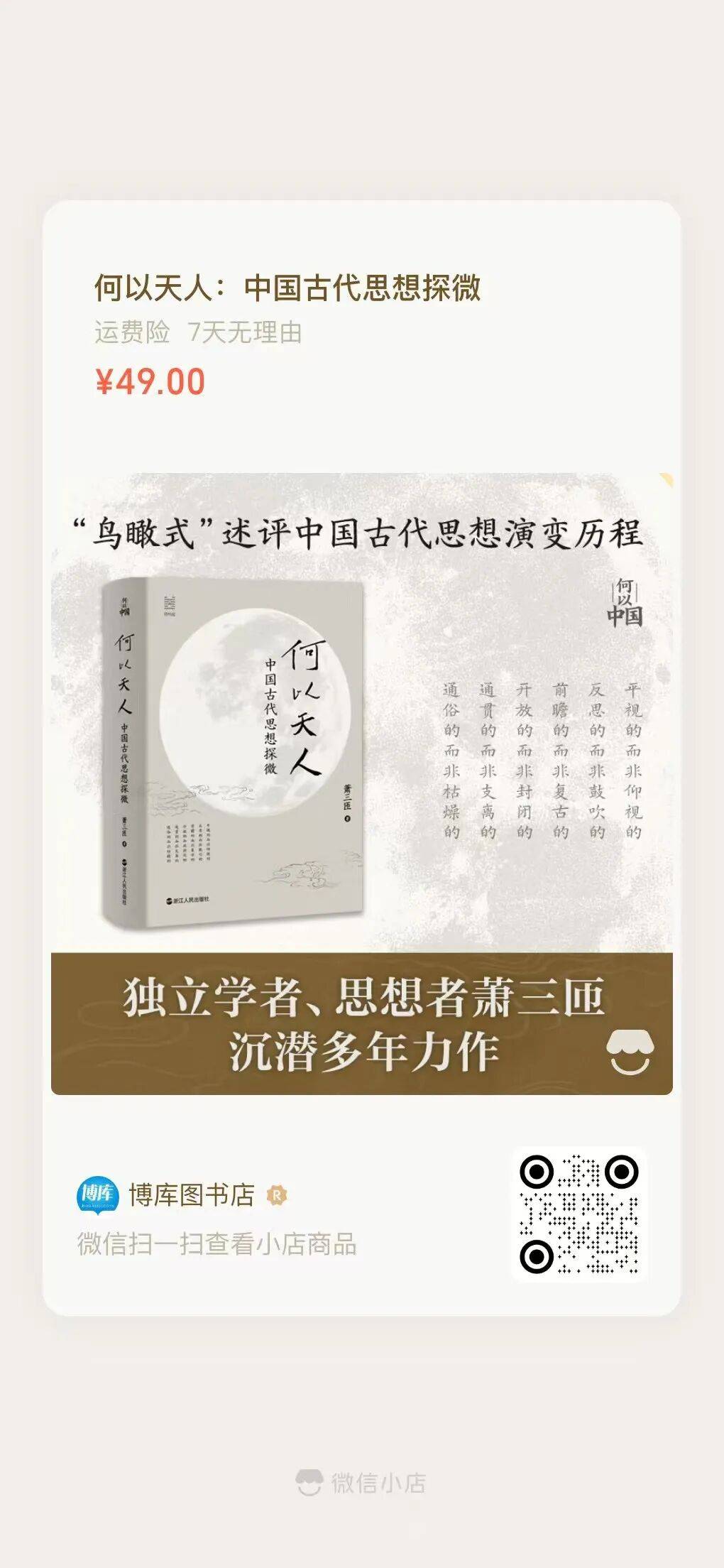中国古代思想,谈论或者讲授者,多如过江之鲫,能够提纲挈领者,却如凤毛麟角。
三匝此书,竭诚探究“天人之际”,切中古代思想要领,如得金线在手、串联散珠,故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当今之世,彷徨于“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者,应该不在少数;我想,至少就中国思想史的探索而言,此书或可让飞鸟得枝,此枝之下,树大根深!
窃以为书末两句结论,实为至理,作者却说此书或助人求真,拐杖而已。
我曾私改张载名句以自勉:“天地本有心,生民自有命,为今人求真道,为来者祈太平! ”
翻阅此书,自然会有“心有灵犀”之感,自然期盼读者亦有同感。
——何光沪
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著作。与坊间的同题作品相比,作者确立了不同于建立在同情与敬意上的、过去向度的中国思想史书写进路,力图向人们敞开思想史的未来面相;不同于经史关系为主线的叙史模式,作者将天人关系作为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主线,但不是将天人化或将天神化,主旨落在天何以成为“主宰”。
作者的论述,别开新面,新见迭出,论辩性强,主张鲜明,与其自陈成一保守主义面向的中国思想史著作相合,颇值一观。
——任剑涛
认识造物者是智慧的开始。萧三匝先生的目光,超越在人际的喧嚣之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自神者的幽暗与虚妄。
——杨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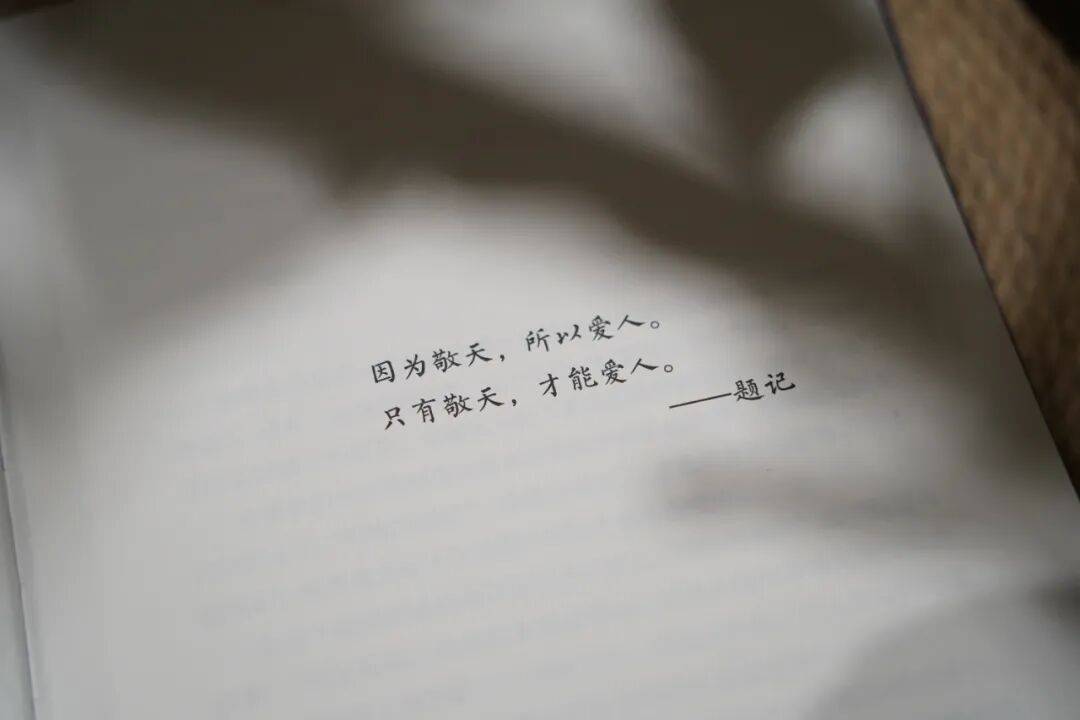
自序:阐旧邦以开新命
史家钱穆有一个核心史观,那就是对本国史应该抱以“同情地理解”,或者“温情与敬意”。此一史观,初看起来是很好的,它体现了后人对前人的尊重,也提示人们不要迷信各种牌号的进步史观。
可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史观在实践中带来的流弊,那就是对历史的认识止于“同情地理解”“温情与敬意”,于是处处为历史及历史人物辩护,结果就是让人们感到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
虽然不能说钱穆的著作只是止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但老实说,钱穆的大部分作品,留给人的印象确实是守旧有余,开新不足,辩护有余,建构不足;读他的作品,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古代中国尽善尽美,好一个金光灿灿的黄金世界!
“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体现的显然不是科学的精神,“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它至少是没有逻辑说服力的。历史是由不同阶段构成的,每个阶段出现的事物都有不同,历史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如果一切历史都是合理的,那么每个阶段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么历史中的新因素何以能够产生?新因素的合理性又何在?
钱穆尊孔,但他在史观上却是孔子的“叛徒”,因为孔子开创的《春秋》史观,坚守的是思想家著史的宗旨,他是用一套价值观来论断、书写历史。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寓褒贬于历史叙述之中,这就是所谓“春秋大义”。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重视历史的作用,为什么“历史是中国人的宪章”,为什么经与史无法截然分家。如果孔子止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他又何必下一字褒贬?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中国传统史观暗含的精神。为什么?由儒家开创的思想传统不是主张复古吗?诚然,历代儒家的确主张复古,但其复古的目的却常常是为了开新,复古的真确含义是:当现实政治、社会遇到巨大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希望阐发古代的政治、社会理想来批判现实,以促使现实朝新的方向行进。
复古能否开新是另一个问题,但任何思想家、史学家在思考维新何以可能的时候,总有一个如何调动思想资源的问题。思想资源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时间轴上的古代资源;二是空间轴上的异质文明资源。在一个封闭的文明体内,在长期封闭的时代,人们能调动的思想资源,当然主要是古代的。这并非中国特有的情形,西方也是如此,文艺复兴不就是对古希腊思想资源的“复古”吗?说到底,复古之所以可能开新,根本上是因为人们认为古典中蕴藏、体现了符合人性的精神内核。这一精神,在古中国是德性,在古希腊是理性。
史学应该指向维新,根本上是因为任何历史都是不同时代的“当代人”带着当代问题、当代困惑书写的,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时时刻刻都在互为影响、互为建构,人们总是依照想象的未来规划现在并研究过去。因其如此,梁启超才能在1902年发表《新史学》这一近代史学的开山之作。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批评了中国两千年来史学存在的四大病灶,比如“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等。试问,如果仅止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新史学”岂非毫无必要?
所以,衡评历史,不能止于“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过分强调“同情”“温情”“敬意”,就会造成自我封闭、孤芳自赏,甚至慢性自杀。
我之所以批评钱穆的史观,现实的原因是,如今的历史书籍大多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故事会”,等而下之的翻译、注释、陈述、复述甚至抄写史实、史料,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把一切历史往合理方面解释。我的问题是,读这样的史书有什么用呢?增加读者的谈资?梦想回到古代?哪个古代?这样的史书能塑造什么样的心灵?即便是对历史进行辩护,又有多大价值?
在我看来,任何缺乏思想穿透力和前瞻性、没有史识的历史类读物根本谈不上是史书。史书自然必须基于客观史实,但任何书写都必然是主观的,对史料的拣选、剪裁、论断无不体现了书写者的主体性。因此,史书必然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客观的史实只是书写的素材而已,过分强调客观的结果,就是书写者把自己异化成了复读机。如果读者在乎的只是客观史实,他们直接去读史料即可,又何须现代人喋喋不休地复读?中国历代还缺史料吗?
让我们回到思想史的主题。中国本有经史合一的传统,章学诚甚至认为“六经皆史”。按传统的看法,“思想”属于“经”的范围,思想史写的是思想的历史,自然更应该是经史合一的著作。但对中国而言,这里面存在一个大问题:对一个封闭的文明体而言,几千年来所奉行的“经”未必是真经。“经”意味着永恒、不变、绝对价值,但近代史告诉我们,儒家所崇奉的“经”并不能满足人们对永恒、不变、绝对价值的渴求,它早就遭遇到了严峻地挑战,中国思想界至今也尚未成功应对这一挑战。
那么,当代人写古代思想史,应该怎么写呢?我认为至少要坚持三大原则:一,既然是思想史,就应该勾勒出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成因和内在逻辑;二,既然是历史,就应该讲清楚中国思想传统的历史演变逻辑;三,既然史学应该指向维新,也即是指向未来,就不能满足于论证历史的合理性,不能迷信历史的必然性,而应该指出历史的可能性。而要指出可能性,就必须不能满足于对历史“同情地理解”或“温情与敬意”。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就必须有思想上的追求,就必须站在全人类的坐标系中、站在未来的时点审视、批判、扬弃中国(包括西方)的传统思想,因此作者的眼界必须开阔,心态必须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史的写作者应该具有“推倒百代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抱负。
这样的思想史写法必然被人质疑,一种典型的批评意见认为,批判先贤是脱离了历史语境的做法,是厚诬古人,让古人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体现了写作者的怯懦。
这样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书写思想史,不仅要着眼于思想家在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要着眼于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如果他的思想对后世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也不必写他。因此,我们可以“同情地理解”那个已经死去的作为个体的孔子,但我们不能止于对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的“同情地理解”,这样的书写其实反映的正是书写者对现实和未来的不负责任。
遗憾的是,已经出版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大多不符合我提出的几大原则,它们要不是只有历史没有思想,要不就是把历史论述得过于合理和必然,要不就只是对思想史素材简单、杂乱地罗列。不客气地说,不少思想史名家也犯了上述错误。
既然我们应该写着眼于未来的,指出存在某种可能性的思想史,就必然面临一个以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上的思想家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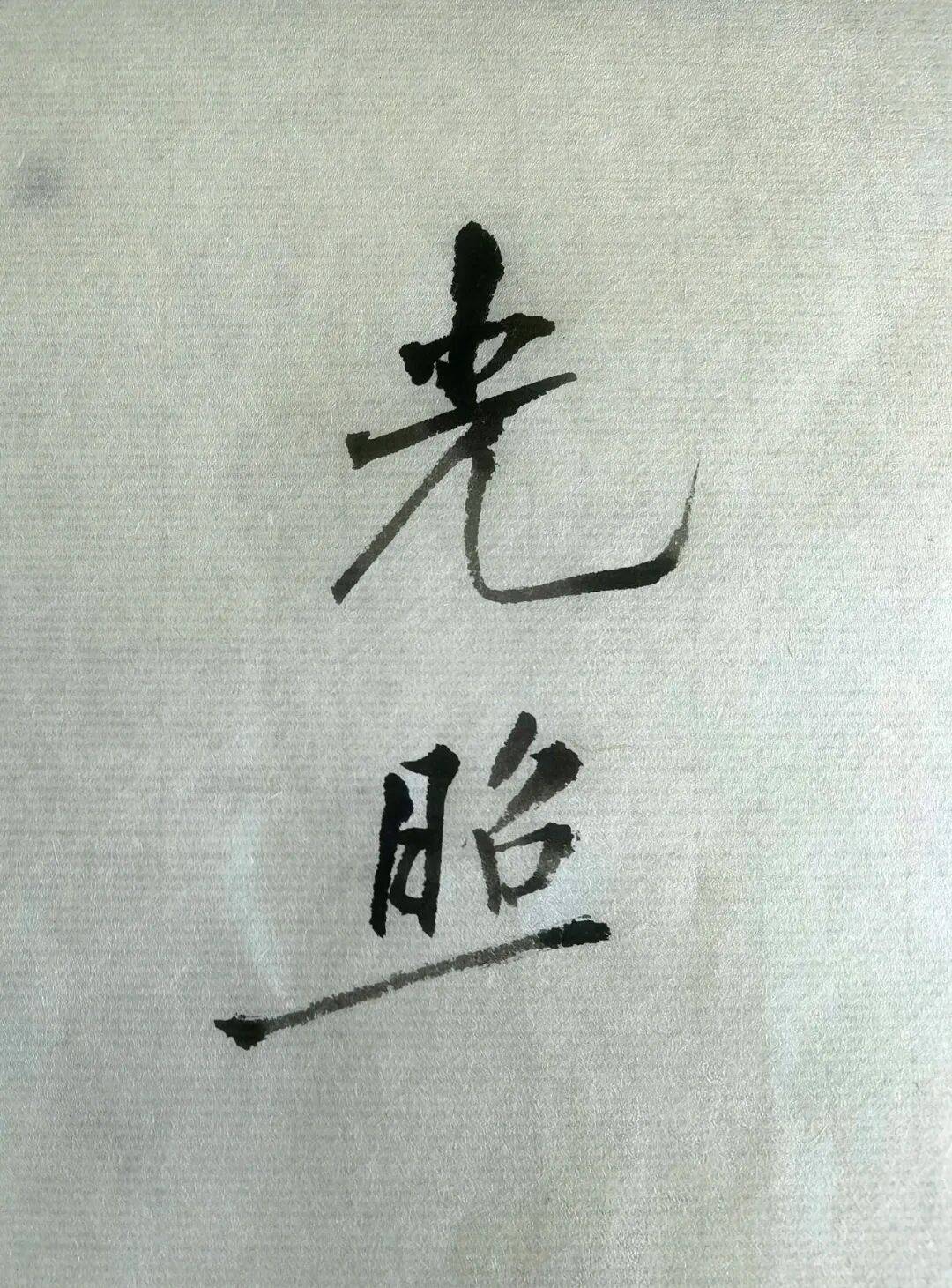
对我而言,要写思想史,就应该紧扣人类思想的核心问题,以此来论断思想史和思想家。那么,人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要言之,就是天人关系,它是一切思想产生的前提,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问题,没有之一。
在汉语中,“天”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人格化的主宰之天,相关词语如“天谴”“天助”;二是非人格化的规律之天,相关词语如“天理”“天道”;三是自然之天,相关词语如“天气”“天空”。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论之天,除非特殊说明,均为主宰之天,这也是天人关系意义上的天。
一般来说,我们所谓的“思想”,就是俗话所说的“三观”。按中国传统语汇的说法,天与人的关系解决的就是世界观问题,人与人的关系解决的就是价值观问题,人与自身的关系解决的就是人生观问题,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世界观——天人关系,人只有摆正天与人的关系,另外两种关系才能摆正,天人关系是宇宙人间一切关系的基石。当代中国的种种乱象、当代中国人的焦虑不安甚至抑郁也都能在天人关系中找到源头和解决办法。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论的主宰之天,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他是万物的创生者。万物因此本于他、源于他,按儒家的说法,就是“生生之谓至德”,因此他能解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二、他是万物的立法者。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只有他能制定绝对价值,人间的一切价值、规则都本于他、源于他,而非人为自己立法。人为自己立法的结果必然是谁都无法说服谁,由此必然产生大纷争,甚至大战争,此乃取死之道。法源自天,“人法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会有共同语言,就会协作共进。
三、他是赏善罚恶的司法者。因为赏善,他才让人敬爱;因为罚恶,他才让人畏惧。人无敬畏,必然放肆。这一特征也能解决“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四、他是亲切的交流者。《诗经·皇矣》说:“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天帝告知我周文王:“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不要看重疾言厉色,莫将刑具兵革依仗。你要做到不思不想,天帝意旨遵循莫忘。”天帝还对文王说道:“要与盟国咨询商量,联合同姓兄弟之邦。用你那些爬城钩援,和你那些攻城车辆,讨伐攻破崇国城墙。”)天如果不能与人交流,则人如何获知天意?天如果不能与人交流,人如何得知天的存在?
考诸中西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举凡一流的思想家,无不主动把对天人关系的论述当成其思想的重大课题或思想的背景、预设。对西方思想史而言,古代的苏格拉底、近代的康德、现代的维特根斯坦无不着意于对天的敬畏,西方思想史本质上就是“两希”(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信仰)思想传统内部张力的演进史。遗憾的是,中国学者,即便对西学有深入研究,大多也只是从希腊哲学这一条线着眼,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希伯来传统,很多人对希伯来传统的认识居然存在不少惊人的常识错误。这样的西学家,根本上是不合格的,其对西方的认识,至少存在巨大偏差。我甚至认为,抛开希伯来传统,根本无法正确认识西方事物的任何方面。比如,那些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如果对希伯来传统没有认识,也根本不能真正理解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史而言,先秦时代的天总体上已经具备上述主宰之天的特征,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如孔孟、董仲舒、程朱、陆王也无不关注天人关系,否则中国也不会有“天命”“天良”“天心”“天性”等词汇了。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伟大,首先是因为他看到了“究天人之际”才是宇宙人间第一要务。近代中国学者最大的缺失,是不知天人,嘴上高呼“三观要正”,心里实不知世界观为何物,更不知世界观是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基石。
因其如此,本书尝试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着眼,重新书写、论断中国思想史和其中重要的思想家。我将证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轨迹是一条不断下行的抛物线,而其之所以如此,根源就在于天塌了,人的思想无所附丽,于是只能自以为是,言辩滔滔却不知所云,飘飘荡荡如不系之舟。我将证明,文明是一个连续体,可以更新,但不能切断;文明的更新必将以思想文化的重生为前提,而思想文化重生的前提则是重新理顺天人关系。
至于具体写法,我希望自己做到以下几点:
一、平视的而非仰视的。因为只有平视一切人,才能产生创见。
二、反思的而非鼓吹的。因为思想史本身就是不断反思前人思想的历史,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没有反思的思想史也是不值得读的。
三、前瞻的而非复古的。因为人是被希望引领的,与其反顾,何若前瞻?
四、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因为开放才有生机,封闭只能消亡,不能认识世界,就不能认识一国。
五、通贯的而非支离的。因为只有通贯,才能帮助读者搭建认知框架;不能认识森林,也就不能认识一棵树。
六、通俗的而非枯燥的。因为通俗才能广传,枯燥实乃自绝;凡“大雅”,必“近俗”;凡通透,必平常。不过,通俗与否,不同的人感受不同,有人就认为《论语》相当通俗,有人却认为它相当难懂。对讲中国思想史来说,首先就会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古人的著作,都是文言写成的。我要证明自己的论点,就不得不引用一些古文,但当代中国人,大多数不具备阅读古文的能力,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我的选择是:尽量少引用古文,对于不得不引,且比较不容易读懂的古文,我会适当予以解释。
三千年思绪奔涌而来,我所能做的,“修辞立诚”而已。“知我罪我,其惟天乎?”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