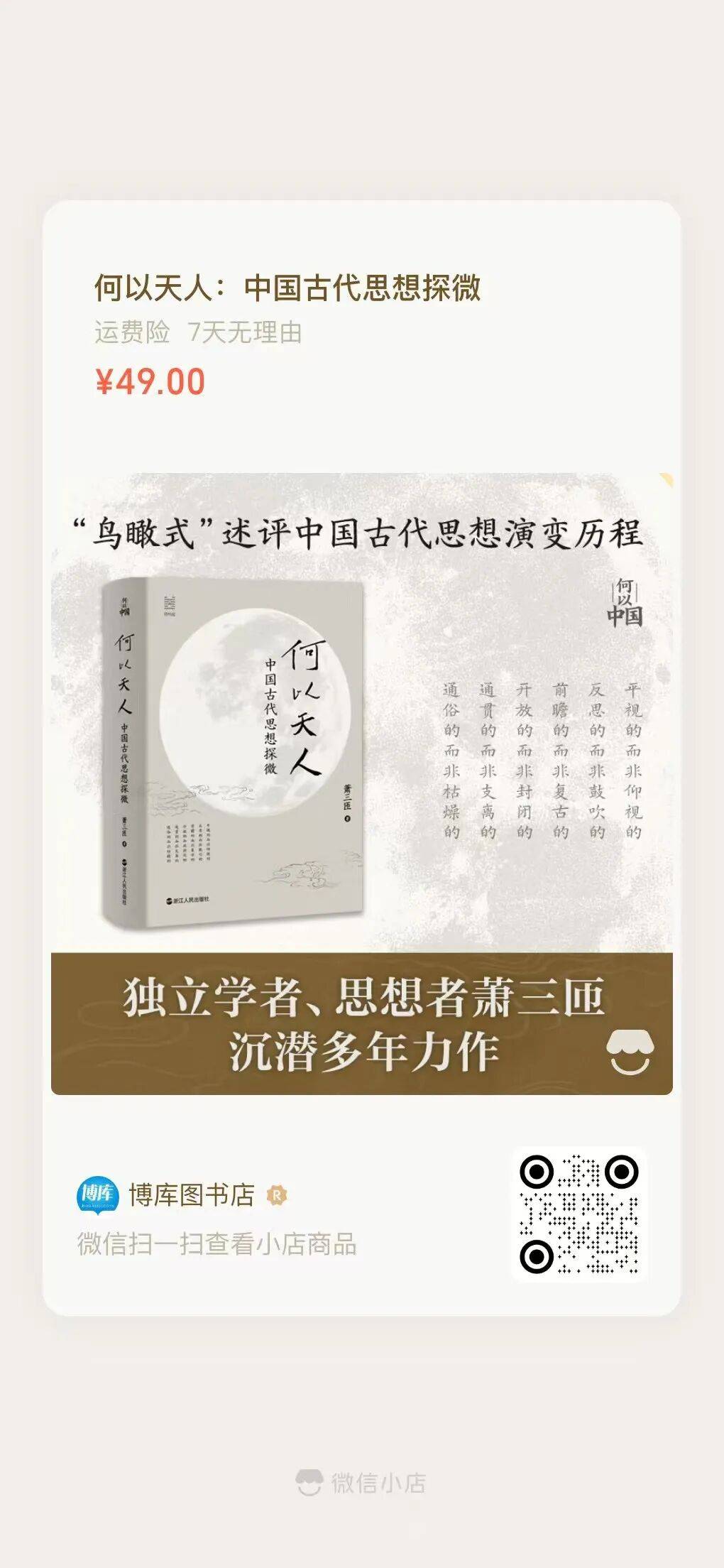在中文思想写作的繁密丛林里,萧三匝新书《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像一柄亮得扎眼的手术刀。它既不满足于“温情与敬意”的故事化叙述,也不躲在学术注脚里节外生枝,而是把“天—人”作为总钥匙,重写一部以价值判断为引擎的思想史。作者在序言中直截了当地宣布:历史不是用来自我安慰的,史书若只剩“同情地理解”,就会滑向保守的合理化。于是他回到《春秋》“寓褒贬于史”的古法,用“应然”与“或然”的标尺丈量“实然”,试图在传统与未来之间,重新校准中国思想的地基。
全书的最大胆处,不在于材料的铺陈,而在于立场的锚定。作者把“天人关系”的历史,解释为一条“不断下行的抛物线”:从殷商的“上帝/天帝”到周公“以德配天”的制度化,再到战国以来对“主宰之天”的抽空,汉代“道德之天”与“天人感应”的并置,宋明理学对“天”的道德化乃至心学的“良知自作主宰”,最后落入清代“舍天求生”的人间计学。其命题之锋利,在于把当代的“无法无天”与古典的“失其所天”连为一线:当外在的“超越尺度”被消解,人的道德努力便容易抽空为修辞,政治权力则天然有理由自我神化。把这条线索勾亮之后,本书就不再是知识史的编目,而是文明自救的辩论书。
这样的写法为何值得今日读者思考?一则,它有勇气把“价值中枢”摆回思想史,拒绝把思想史当器物志来编。我们确实需要一本能解释“何以此时此地”的书,而不是只告诉我们“彼时彼地说过什么”。二则,它用“敬畏的来源”追问伦理与秩序的最后根据。这对一个高度技术化、风险持续叠加的社会尤其切要:当“有效性”成为第一美德,关于“应该如何”的讨论往往被裹挟进效率话语而悄然失声。三则,它逼迫我们在“可用的传统资源”与“必要的价值奠基”之间作艰难的选择,不再把“复古”“西化”的二分当作思想的终点站。
当然,传统并非只有“可诉诸超越”的部分。本书虽然持续揭示“天”的人格性被稀释的后果,却同样提醒我们:周公制礼之妙,在于把“敬天”的纵向维度翻译进“礼治”的横向秩序;法度与德性的张力,正构成古代政治的现实主义面目。今日我们从传统里可汲取的精华,正在这种转译术之中:其一是“春秋大义”的史家之责——敢于立场之明与褒贬之当,反对价值虚无化的“无害史学”;其二是“礼以节民”的制度智慧——把敬畏从玄虚的崇拜变为可操作的边界意识与程序约束;其三是“以德配天”的品格政治——把权力的正当性与品行责任紧紧缝合,而非将德行当作粉饰性的个人修身。若说“借古以开今”,古典之可学,正在于此。
有人问:“当代中国是从古代寻找思想资源,还是从‘两希’寻找资源?”《何以天人》并不鼓励在两端中作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以“主宰之天”为支点重铸平衡。若我们把“两希”简化为“希腊之理性、希伯来之信仰”,再把“中国之天”理解为“自然—法则—德性的综合”,那么最可行的路径不是单向移植,而是“对读式再锚定”:让中国古典提供生活世界与常识的厚土,让希腊提供论证与批判的逻辑工具,让希伯来提供终极价值的超越地平线。三者会通,不是混搭,而是在“可争论的公共理性”之下,保留“可自由选择的信仰超越”。这既避免了把政治神学化的危险,又防止公共伦理在纯工具理性里被消解得无影无踪。
中国古代的“天”与希伯来之上帝,异同在处处细节里显影。其同者,一是两者皆声称对人间秩序拥有最后裁判权,二是“天命/约”的语言都曾被用来约束权力并滋养伦理。其异者,则更具结构性:古典中国的“天”常在自然—秩序—德性之间游移,倾向于无位格、可体认、可感应的“法则之天”,由此培植出“修己安人”“以德配天”的道德政治;希伯来上帝则是位格化、启示性的“自有永有者”,通过线性历史展开“约的伦理”,将“爱—公义—怜悯”绑定为不可拆分的三位一体。前者强调内在修养的渐进、与万物同构的和谐;后者强调应许与审判、历史中的呼召与悔改。两种形上风景各有伟力,然而在现代公共生活里相遇时,若不能清楚地区分“形上之根”与“制度之形”,就容易把“敬畏”误读为“神权”,或把“理性”误读为“价值中立”。《何以天人》之所以重要,正在它迫使我们一边厘清“根”,一边反思“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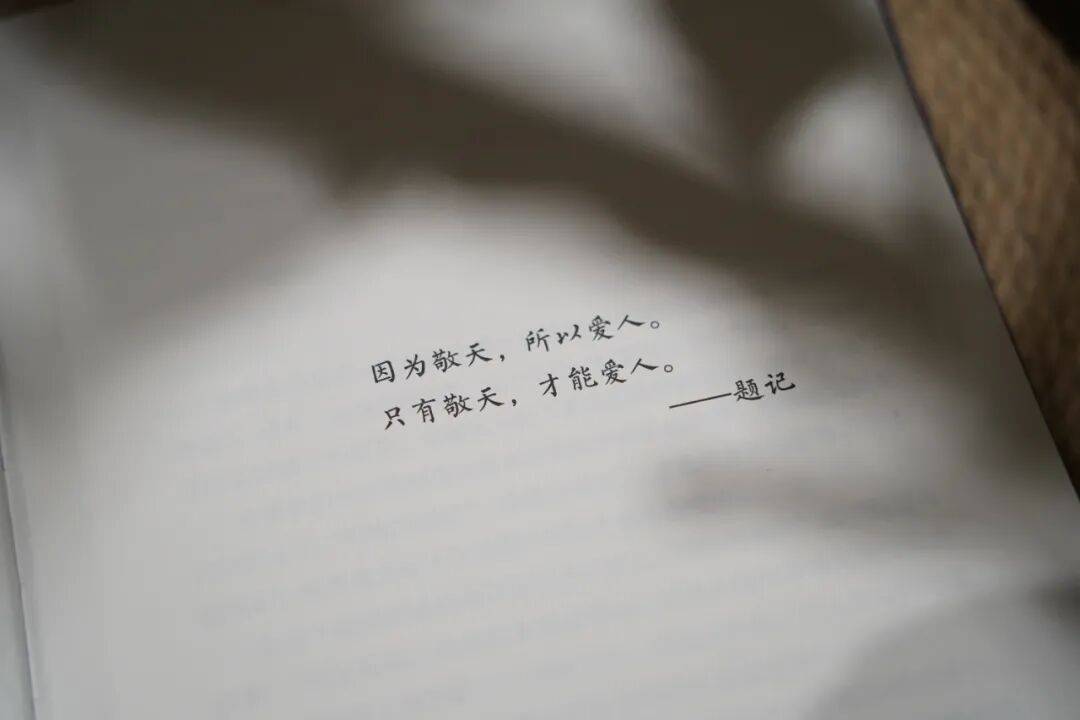
重铸思想的地基,是建立在超自然的超验之神之上,还是“天”之上?若把这问题理解为“择一排他”,我们会掉进历史的死胡同。更稳妥的回答也许是“双层奠基”:在公共层面,以自然法与人性论为共识底座,辅以可验证的制度安排与权力分立,使秩序无需诉诸某一宗教的绝对化语言;在个体与社群层面,用超超验世界引领人类,向超越敞开——允许并保护人以启示性信仰来赋义人生、校准良知,并反哺公共德性。前者提供最低限度的可治理性,后者提供最高可能的道德张力;两层之间以“自由—宽容—责任”作桥梁。这不是折衷,而是把“敬畏”从形上资源转译为可共享的德性谱系,把“信仰分歧”转化为“公共合作”的动力结构。作者所主张的“主宰之天”,在这样的双层机制中并不被排斥;它成为许多人愿意选择的终极锚,且在不强制他人的前提下,发挥其净化良知的作用。
《何以天人》最能启发今日心智的,是作者对“绝对价值”的再申辩。萧三匝提出:如果没有“主宰之天”,人类的道德将缺乏不随境遇摇摆的标尺;如果只靠内在良知自为主宰,便难以避免多元良知之间的相互抵消。此论不必被理解为某种神学预设的硬性推销,而可以作为对现代伦理困境的经验观察:公共生活中,我们的确频频见到“价值冲突—程序仲裁—裁决不被承认—信任进一步崩解”的链条。作者的激进之处在于:他不把药方寄望于更多的技巧性调停,而是要求重建一个能让“善恶之别”获得最后背书的超越来源。对于习惯把道德奠基交给历史、民族精神或社会共识的我们,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甚至是一封挑战书。
当然,本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叙述纲要偶有“单线退潮”的倾向:把多中心的思想演化压扁为“去人格化—失天—人主化”的决定论,可能低估了汉学、佛学、道学在不同时期对“天”的再发明与再社会化能力;其二,对心学的评议略显“以果责因”:心学的社会效果并不止于“主宰内置”,它也产生了强烈的“良知公共化”冲动与实践伦理;其三,将当代道德困境尽数归咎“失其所天”,有助于警醒,但若忽略市场化、城镇化与数智化带来的结构性重排,就会让药方失衡。正因如此,我更愿把本书看作“开吵”的书——它提供一种必要的极端,让别的极端显形,从而促成更诚实的对话。
从写作本身看,《何以天人》的可贵,在于“刀口向内”的勇气与“不怕得罪人”的明白。它以史家之笔做思想家的事:不怕立标准,也不怕冒风险。它的论断未必每条都能服众,但它逼人的诚意足以让人把书合上后继续思考。更重要的是,它把“中国思想史”从“学术对象”抬回“公共议题”,让“该以何为善、何为恶、何为可敬、何为可憎”重新进入讨论场。这本书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答案,而是提纲。若能在读者心里点燃“敬畏、自由、诚实”的三重火焰,它就不虚此名。
我认为读者可以从《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获得三种具体的“可操作性收获”。第一,重学“褒贬之术”:在史、经、政的交界面,训练用公开的理由、透明的证据和可辩的价值来做判断,抵制在情绪与立场之间走捷径。第二,重建“边界的敬畏”:将“敬畏之心”落实在制度与日常的最低线——契约不可戏弄,程序不可任性,权力不可越界,言论不可诬陷。第三,重启“对读之法”:把《尚书》《论语》《中庸》与《圣经》《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并置,把“礼—法—德—信”的四条线互证互校,在差异中寻找最大可共享部分。做到这三点,我们就既不必在传统与“二希”之间二选一,也不必把信仰与理性对立成你死我活。
用一句话结束这篇文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取决于它如何安放“看不见的东西”。《何以天人》所做的,正是把那些看不见、但又决定我们看得见的一切的根,重新拎到阳光下。善良需要尺度,正义需要根基,自由需要边界;而尺度、根基与边界,不会天然长成,必须被一代一代人自觉地重建、守护与更新。
【本文原载 Substack “中国思想快递”(China Thought Express)中英文平台,欢迎转载,欢迎登陆阅读其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