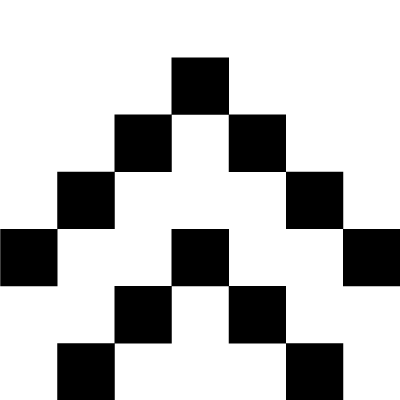在地生长,不仅是在人的身上,还有在神的身上
前天写了 后,很多读者后台留言香港人相比北方就很有主体性。今天想结合这个话题,最后再说说香港。 主体性从香港电影就能看出来,我小时候的香港电影自主创作的激情从镜头里都能感受到。它不是像好莱坞那样模式化,善恶二元对立。香港电影更有一种末日感,和虚空一切的能量。 从太平山上看香港,就很有香港电影的即时感,就像从天上看人间。占据C位的是贝律铭设计的中银大厦。设计灵感来自竹子节节攀升的节奏感。仔细一看,果然,香港岛不仅高楼鳞次栉比,连地形也是上下起伏。这一切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像竹子一样是在香港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20世纪上半叶,作为远东重要转口港,香港的建筑以殖民地风格的港督府和银行大楼为代表,它们象征着传统贸易与英资的稳固秩序,经济完全依赖地理中转。
20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化起飞,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大厦在九龙新界涌现,但港岛的核心仍由老汇丰银行大厦等建筑把持,代表着战后制造业繁荣所积累的金融资本。
真正的剧变始于1980年代。香港金融和房地产高速增长。由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破土而出。它那突破传统的三角造型与节节攀升的凌厉姿态,不仅挑战了由旧汇丰大厦界定的天际线,更像一柄“破局之剑”,刺穿了不确定性的迷雾。它的修建,向全球市场宣告:它与几乎同期兴建的新汇丰大厦隔街对望,一场关于资本权力与信心的无声竞赛在天空展开,恰恰印证了当时香港作为国际资本汇聚地的空前繁荣和地位。
因此,中银大厦远不止是一座建筑。它是香港百年经济演进的关键地标:它标志着香港经济动力从港口贸易、本土制造,最终转向了国际金融。 它的玻璃幕墙,像是后现代的阁楼,天地风云都在个人的世界里。
这一切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随着生活生产需要,在地生长的。
人字大写的时代,就此走向高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具有主体性的原因。自己决策,行动,对结果负责。这是一种公·民精神。
在另一个角落里,兰桂坊等酒吧业态也在生长。开始是在港老外聚集的地方,去兰桂坊逛逛,基本大多数都是老外,慢慢的,本地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兰桂坊后来在成都开分店时我去了,你霓虹闪烁,比香港总店还要绚烂,大多数是本地的潮男潮妹们,这是他们挥洒青春的地方。感觉像是空降的欲望城。 相比起来,香港兰桂坊有点像英国的乡村酒吧。村味足,不city。如同路边的野花,野蛮生长。
香港也有空降,比如迪斯尼,还有故宫。这东西文化的两种场所,同时出现在香港,通常被解读为香港的包容。但在今天,它们两不管降落在哪座中国城市都不违和。而不同在于,里面的游客,总感觉参观迪斯尼和故宫的本地人总是充满惊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那种好奇少了些许浮躁,多了许多童年。都说香港人是三分钟热度,就像小孩子面对外面世界,频繁切换着惊喜。 当然,能坚持下来的人总是少数,全世界都一样。之前 说过香港的交响乐团,话剧社都是世界一流水平。好似童心的孕育,像竹子一样破土而出,长成高楼,生长的力量是巨大的。
香港的大屿山等富人区,当然不会像新界港岛那样拥挤。但很少有香港的Y行S威是因为贫富差距大。我在香港参加过几次Y行,五花八门,但基本都是对权的不满,未有对富的。李嘉诚霍英东等富豪是抓住了香港腾飞的历史机遇,地产金融影视这几个行业出了大鳄。但他们并非有权 之背景,而是从土壤里搏杀出来的,可以羡慕其运气好,可以仰慕其努力拼搏,却极少有人不满。
在地生长,不仅是在人的身上,还有在神的身上。
在香港,天后妈祖,土地庙,黄大仙,佛祖,安利······各路神仙走不到两处就能遇到一个。记得弥敦道上,有家很小的基督教会,斜对面就是香港最大的清真寺,走几步就是道教什么仙人的牌位。
人在地面竞争,神在天上打架。
真正的福·音,超越宗教,在这样的充满神人张力的土壤里播种。 就看你是什么种子。
只是这几年香港电影没有以前《英雄本色》那么狂,没有《国产零零七》《大话西游》那么随意无厘头,没有《古惑仔》那么野路子。这些电影也不是说多好,但感觉像是从香港人的文艺细菌里长出来的,现在的香港电影,感觉像正能量的模型里制造出来,镶了金边。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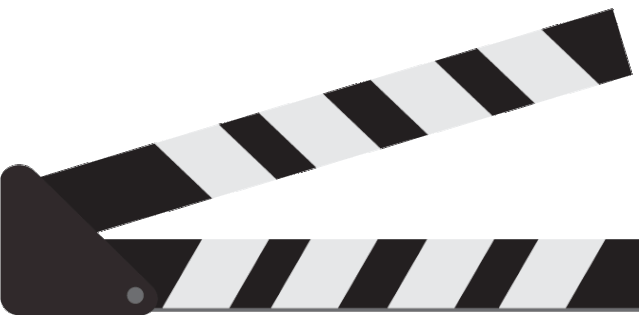
欢迎转发本文给你关心的他/她 传递真光⭐